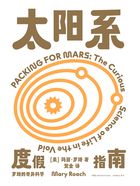
倒计时
在火箭科学家眼中,你是个大问题。你是他或她这辈子经手的所有机械装置里最恼人的一个——你、你起伏不定的新陈代谢、你那些琐碎的记忆,还有你千奇百怪的身体结构。你难以捉摸,你千变万化,你要花上好几周才能安装到位。工程师不得不操心你在太空里需要的水、食物和氧气;操心要把你的鲜虾沙拉和你那有光泽的牛肉墨西哥薄饼卷发射升空需要多少额外的燃料。像太阳能电池或者推进器喷管就不一样。它们总是表现稳定,并且无欲无求;它们不排泄,不抓狂,更不会爱上任务指挥官;它们没有自我;它们的结构即使没有重力也不会崩坏;另外,它们不用睡觉也可以工作得很好。
在我眼中,你却是火箭科学中最好的一环。如果人类也是一种机械装置,那么它正是让其他机器都跟着充满无穷魅力的那一个。试想一个有机体,它的每一项特征都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好让它在这个有着氧气、重力和水的世界里能够存活并且茁壮成长。把这么个有机体丢到太空这个不毛之地,让它在那里飘上一个月甚至一年,这简直就是一项荒唐得令人着迷的事业。一个人在地球上习以为常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被重新思考,重新学习,还要反复演练——要训练一群成年男女怎么上厕所;还要给一只黑猩猩穿上宇航服,把它发射到轨道上去。在地球上,一个诡异的世界已经形成。而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在模拟外太空。在这里,一个个太空舱永不会发射升空;病房里躺着的都是健康人,而且一躺就是几个月,模拟零重力的样子;撞击实验室里的人则在拿着尸体往地上扔,模拟宇宙飞船在海洋上溅落的情况。
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勒内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他工作的地方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的9号楼。这幢楼就是航天中心的模拟大楼,里面有50多种模拟太空环境的东西——压差隔离室啦、气密舱啦、舱口啦、航天舱什么的。那时,勒内连续好几天都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去调查了一下。“原来是某个可怜的家伙穿着宇航服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跑步机吊在一大套复杂的模拟火星重力的机械装置上,周围环绕着写字板、计时器、耳麦和众人关切的目光。”就在读他这封邮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即便不离开地球,我们也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进入太空的。或者至少是进入某种有如超现实的闹剧一般的虚幻世界里。而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可以说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月的文件和报告数不胜数,然而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篇比一份11页纸的报告更有意义。这份报告是在北美洲旗帜学协会第二十六届年会上发布的。旗帜学是一门研究旗帜的学科,不是研究气质的 。不过我要讲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既不是关于旗帜研究,也不是关于气质研究。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前无古旗:关于在月球上安放一面旗帜的政治及技术层面问题研究”。
。不过我要讲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既不是关于旗帜研究,也不是关于气质研究。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前无古旗:关于在月球上安放一面旗帜的政治及技术层面问题研究”。
要完成这份报告,首先要开会。在阿波罗11号发射升空前5个月,当时新成立的“首次登月仪式性活动委员会”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就将一面旗帜插上月球的得体性问题展开辩论。
《外层空间条约》规定,禁止对天体宣誓主权。而美国是这一条约的签约国之一。那么,怎样才能将一面国旗插在月球上,而看上去又不像是想要——用一位委员的话说——“占领月球”呢?有人提出了一条很难上镜的计划,就是把一套装有各国微型国旗的盒子放在月球上。委员会考虑了这个计划,又否定了它,旗帜必须要飘扬。
这样一来,就该美国航空航天局技术服务部大显身手了。因为如果没有风,旗子是没办法飘起来的。而月球上连大气层也没有,更不要说风了。另外,虽然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重力的六分之一,但是这点重力要想把一面旗子扯成软趴趴的下垂状还是绰绰有余。于是,人们在旗杆上又装了一根与旗杆垂直的横梁,然后在旗子上缘缝出了一个卷边。这样,星条旗看上去就会像是在一阵猛烈的风中飞扬了——这一画面还挺可信的,几十年人们对这个弥天大谎津津乐道——虽然实际上那面星条旗不是飘着的,而是挂着的;所以与其说它是一面旗帜,还不如说它是一块充满爱国主义气息的小窗帘。
然而挑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你想,怎样才能把一个旗杆塞进一个狭窄的,已然拥挤到了极限的登月舱里呢?于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又派出了一批工程师来设计折叠式旗杆和折叠式横梁。可即使如此,舱内的空间还是不够。于是这套“月球国旗套装”——这面国旗、它的旗杆还有横梁是注定要举世闻名了——只能装在着陆舱的外面了。但是如果装在外面,它就必须要能承受旁边降落引擎产生的华氏2000度(约为1093摄氏度)的高温。于是工程师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旗子在华氏300度(约为149摄氏度)的时候就融化了。结构与力学部又赶来救急,他们设计了一个保护罩,由一层层的铝、钢和特莫弗莱克斯二元电阻合金隔热层制成。
现在看上去这面旗子总算是准备好了吧。可是就在这时有人提出来,宇航员们在穿着耐压服的情况下,握力和活动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他们能把国旗套装从它的绝缘保护套里抽出来吗?还是他们只能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徒劳地站在那里,对着保护套望洋兴叹呢?他们能把旗杆和横梁的伸缩杆拉到所需的长度吗?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知道答案:人们又生产了一批“月球国旗套装”原型,然后召集全体宇航员进行了一系列的国旗套装展开模拟训练。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首席质量保证官的监督下,国旗打包完成(一共4个步骤),然后装上了登月舱(11个步骤),最后它就飞向月球了。到了月球之后,那个伸缩横梁没办法完全打开;另外月球土壤也太硬了,尼尔·阿姆斯特朗最多也就能把国旗插个6英寸(1英寸=2.54厘米)或者8英寸深 。结果,国旗看起来就像是被上升舱引擎鼓出的风吹倒了似的。
。结果,国旗看起来就像是被上升舱引擎鼓出的风吹倒了似的。
欢迎来到太空。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部分,那些荣耀与悲怆;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那些小小的,喜剧性的片段和每天的小胜利。将我吸引到宇宙探索问题上来的,既不是英雄事迹,也不是探险故事,而是它们背后那些最具人性化的,甚至是荒谬的挣扎。一位阿波罗宇航员在太空行走的那天早上吐了,于是担心他个人会害美国输掉这场登月之争,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暂缓登月计划的讨论。还有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太空人,尤里·加加林,始终记得当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以及成千上万欢呼雀跃的民众面前走红地毯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鞋带没系,于是自始至终脑子里就只有这一件事了。
在阿波罗计划结束的时候,宇航员们就一系列问题接受了采访,以取得反馈意见。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宇航员在航天器外做太空行走的时候死去了,你们应该做些什么?“摆脱他。”这是其中的一个回答。而所有人都同意:任何试图追回尸体的尝试都可能使其他成员的生命陷入危险。只有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些绝非无足轻重的挣扎,最终穿上宇航服,进入宇宙飞船座舱的人,才能如此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样的话。只有一个曾在浩淼无垠的宇宙中飘浮过的人才能明白,被埋葬在太空里,就像海员的海葬一样,对死者来说绝无任何失礼,反而是一种荣耀。在太空中,任何事情都与地球迥异:流星从脚下划过,而太阳在午夜升起。宇宙探索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人类存在意义的一种探索。人们能在多么反常的状况下生存?能活多久?这种生活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
在我研究生涯的早期曾有那么一个时刻,那是长达88个小时的双子星七号任务中的第132分钟;正是这个时刻,在我看来,总结了宇航员经历的意义,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如此吸引我。当时,一位叫吉姆·洛维尔的宇航员正在对地面指挥中心描述他用胶片记录下来的一幕,任务记录单上写着:“漆黑的天空上悬着一轮满月,下面是麻红色的地球云层。”沉默了一会儿后,洛维尔的队友弗兰克·伯尔曼按下了对讲键:“博尔曼在小便,大概有一分钟之久。”
然后隔了两行,我们看到洛维尔说:“多么引人注目的一幕啊!”我们不大清楚他所指的到底是哪一幕,但很有可能不是有月亮的那一幕。从不止一位宇航员的回忆录看来,太空中最美丽的画面之一就是:一束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的速冻尿液滴。太空并不只是高尚与荒诞。太空消除了二者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