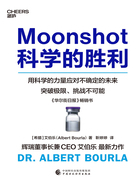
主动创造,奇迹之旅开始的地方
这辉煌的产生,离不开2020年的那场奇迹之旅,那长达9个月令人焦灼的日日夜夜。但是,这段故事要从至少两年半以前说起。2018年1月1日,我被任命为辉瑞首席运营官,这个职位给了我一年的时间,为最终升任最高负责人做准备。我的关注点是增长,将“增长绝非机缘巧合,而需主动创造”奉为座右铭。在制药行业,推动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患者的生活做出积极的改变。为此,我们必须将辉瑞转型为一家以患者为本的公司,一家坚持科学与创新的公司。我是乐观主义者,这或许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期间,我的母亲在即将被纳粹行刑队执行枪决之前,表现得非常勇敢和镇定,几分钟后她非常幸运地死里逃生。这让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对即将由我领军的辉瑞持乐观态度。对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在我之前担任辉瑞首席执行官的伊恩·里德(Ian Read)信念坚定,令我获益良多,在我上任前的9年中,他将辉瑞这台“研发引擎”从一家生产力平平的公司转型为行业翘楚。这为我注入了信心,让我能够“心怀远大”地思考辉瑞的转型举措,并雷厉风行地执行我的计划。
在成为首席执行官前的这12个月里,我制定了战略,对公司进行了布局,并选出了即将与我一起踏上转型之旅的执行团队。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一天,我已对想要实施的举措胸有成竹。那天,辉瑞董事会把我叫到加州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宣布了对我的任命。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微笑着大声说:“这种事在美国更有可能发生!”在美国,一个有着浓重口音的希腊移民晋升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才更有可能。
掌舵之后,我立即启动了公司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改革。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了重组。另外,我们还在公司外为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和辉瑞普强(Pfizer Upjohn)的专利到期药(3)业务找到了更合适的容身之地。这两项业务的体量都很可观。2018年,二者的营业收入(以下简称营收)总和占公司总营收的25%以上,但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的市场份额较低,普强的营收则正在下降。对于这两项业务而言,与继续留在辉瑞相比,新东家能够为它们带来更稳健且光明的前景。辉瑞的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与葛兰素史克的相同业务合并,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该公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成就最为卓著的非处方药公司。辉瑞普强则与迈蓝制药公司(Mylan)合并成全球仿制药巨头晖致公司(Viatris)。业务拆分的过程并不容易。
一想到辉瑞放弃了如此多的营收,我的一些团队成员不禁担忧起来。有人说:“辉瑞可能要把‘全球最大生物制药公司’的头衔弄丢了。”而我的回答是:“我们的目标不该是成为最大,而是成为最好。”我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优秀的园丁需要在初春时节就开始为树木修剪枝叶,而辉瑞正处于万物疯长的春天。”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放弃这两项稳定但增长缓慢的业务,将全部资源都投入公司的创新型核心业务,不仅让辉瑞在两年后推出了抵御全球流行病的疫苗,同时也让辉瑞重回全球最大生物制药公司的宝座。
除了对“规模”的担忧,我的团队成员还受到了许多情感上的烦扰。让辉瑞名声大噪的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品牌,都属于这两项业务,包括布洛芬(Advil)、善存、立普妥、络活喜(Norvasc)、万艾可等。这种感觉,仿佛在与自己最大的成就切割开来。但我知道,要想让一家优秀公司跻身伟大公司之列,就要依靠对自身成功业务进行优化的能力,以及开启新篇章和拓展更新、更广前景的魄力。
在缩小公司规模的同时,辉瑞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以提振科学实力和待开发资产。几个月内,辉瑞收购了四家生物科技公司。Array生物制药就是其中之一,这家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化“无成药性为成药性”(4)而闻名。虽然这些公司的成本高于营收,但有助于辉瑞巩固自身科技实力。此外,我们也开始构建新的业务能力。例如,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一天,我就任命莉迪亚·丰塞卡(Lidia Fonseca)为辉瑞第一任首席数字官,直接向我汇报工作。
莉迪亚出生在墨西哥,幼年时移民美国,在荷兰获得硕士学位,致力于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改善卫生工作成果。她离开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后入职辉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变革推动者。我为她布置的一项首要任务,是对研发实施数字化,从而实现合作的加深、透明度的增加和速度的提升。然而,这些举措花费不菲,为了支持这个新方向,我们必须对资本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配置。由此,研发和数字化方面的预算得到了大幅提高。作为平衡,我们采取严格的措施,缩减了营销和管理费用。在我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的6个月后,辉瑞已经从一家企业集团转型为一家专注于科技创新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