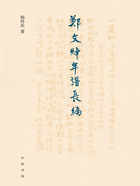
传略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霞(遐)东客、瘦碧、冷红词客、大鹤山人、鹤道人、樵风墅主、樵风逸民、樵风遗老等,室名紫薇玉尺精舍、石芝西堪、齐玉像盦、半雨楼、瓶知室、瘦碧盦、樵风庼、藕翘小榭、威喜芝宧、冷红阁、琴西老屋、红可簃、大鹤山房、沤园、明玕廊、清瑶溆、竹醉寮、书带草堂等。因生于河南开封,小名豫格。隶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旗姓文,故又称文叔问、文小坡。奉天(今辽宁)铁岭人,又署山东高密人。其婿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云:“先生祖籍汉北海郡高密县通德里,为郑康成之裔。”于此龙榆生曾云:“其自称高密郑氏者,文焯自诡托于康成之后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全集》第三卷,第77页)实则言文焯“诡托”,失之武断,远绍“高密郑氏”并非始自文焯,其《得家兄幼兰书却寄》诗云:“通德家风不可忘,敝庐犹是郑公乡”,注云:“昔五世祖抚山东时,祭扫先康成公墓,并绘《郑公乡图》。”(《补梅书屋存稿·扁舟集》)可知其五世祖山东巡抚禅宝即视自己为郑玄之后,以山东高密郑公乡通德里为祖籍。文焯光绪乙亥(1875年)举人。后报请恢复汉姓,称郑文焯。而其兄弟文焕、文炳仍循旗俗。郑文焯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有词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樵风乐府》《苕雅》《苕雅余集》,诗集《补梅书屋存稿》《瘦碧庵诗稿》《大鹤山人诗集》。著有《扬雄说故》《高丽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医故》《古玉图考补正》《金史·补艺文志》《词源斠律》《绝妙好词校释》《梦窗词校议》《大鹤山人词话》等,杂著有《瘦碧庵丛载》《半雨楼杂钞》《石芝西堪札记》《双铁堪杂记》《鹤翁异撰》《樵风杂纂》,批校之古籍有《论语》《谢康乐集》《陶渊明集》《燕翼贻谋录》《花间集》《乐章集》《东坡乐府》《清真集》《白石道人歌曲》《梦窗甲乙丙丁稿》等等,另存留有丰富的书画、篆刻作品。郑文焯虽出身官宦之家,然一生仕途偃蹇,以巡抚幕客终老,晚年又遭辛亥国变,最终在窘困潦倒中离世。下面依据其人生履历及心态变动的轨迹将其一生分为才俊少年、干进举子、江南退士、困顿遗老四个阶段,对其生平略加勾勒。
一
文焯出身内务府世家,祖上虽以军功得官,但历数代之后,这个官僚家庭的文化学术氛围已经非常浓厚。特别是其父瑛棨,更是一位文人气十足的地方重臣。《清画家诗史》称瑛棨“有‘郑虔三绝’之称”(李濬之编辑《清画家诗史》[壬上],第438页)。戴正诚曾云:“郑氏世代簪缨,及兰坡先生,绩学淹雅,金石书画,鉴藏甚富。”(戴《谱》)桥川时雄也说:
郑氏世代簪缨,及兰坡公,名尤显著。以从政之暇,治诗书画,神趣天然,颇极笔墨之妙。(神趣二语,俞曲园评语,见曲园题兰坡画文。)又金石书收藏甚富。(桥川时雄《大鹤山人郑文焯传》)
对于家富收藏这一点,郑文焯在《两汉文评跋》中也云:“余家旧藏书籍精抄本甚夥。”(《国朝著述未刊书目》)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熏陶以及父亲诗歌、书法、绘画的直接影响,为日后文焯的博学多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桥川时雄所云:“先生学藻,盖渊源有自矣。”(《大鹤山人郑文焯传》)
同治元年(1862),文焯入学读书。次年,父瑛棨为文焯兄弟聘请江宁廪贡顾晓帆设帐课读,文焯子郑复培记云:
次年聘顾晓帆先生设帐课读,先府君每授课,文字即能颖悟,且劬学善问,异于诸伯叔,先王父深爱之。十余龄即倜傥见志节,为文奇杰,课余且喜作绘事。(《行述》)
可见,文焯少时即聪慧颖异,勤学善问,深得瑛棨喜爱。十余岁即有潇洒卓荦之风采与高远之志向,并且作文出众,更能继承父亲工于绘事之优长。戴正诚记云:
先生六岁时,见壁悬画轴,即知捉笔临摹。十二三岁,辄以指头代笔,凡花鸟山水人物,著手立就。兰坡先生雅善丹青,至是酬应诸作,多命先生代笔。(戴《谱》)
由此可知,文焯少时于绘画一艺着实有天分,其早年于书画、金石等方面的积淀也为其客居苏州时迅速融入吴中文人群体奠定了基础。
光绪元年(1875),文焯二十岁,本年秋天,他参加了顺天乡试恩科,中式第二百六十六名,保和殿覆试,钦定一等第十三名。房考陈宝琛判其文曰:“朴实说理,风骨清遒,斯为大家。举止有次,有典有则,不蔓不支,抑扬顿挫,灵气往来,是水到渠成之候。”评其诗曰:“芊绵秀丽,雅韵欲流。”(戴《谱》)考官对其诗文的高度评价,让得中举人的文焯“益工学业”(《行述》),他对未来的科举仕途也充满信心。不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里等待他的只有落第的悲苦。
二
光绪三年(1877),文焯参加了在京举行的会试,遗憾的是他落榜了。本年冬,文焯在京师娶热河正总管毓泰之长女张宜人为妻。宜人,字眉君,工绘事,善琴操,才茂德懿,与文焯伉俪甚笃。
光绪四年(1878)春,文焯父瑛棨以病告归,行至平定州逝世。文焯闻此噩耗,“哭不成声,咯血升余”(《行述》),大恸之下,扶柩回京。光绪五年(1879)春,葬瑛棨于京西门头沟大裕村。先是同治元年(1862),瑛棨以剿匪不力,被朝廷褫职,前后十余年携眷四方奔走,故家道衰敝,至其病逝,则彻底败落。戴正诚记云:
兰坡先生在官三十年,去官十五年,家赤贫,丐贷无路,每事阻及节迫,往往使老妇驵携书画折阅,初未尝计及子姓。(戴《谱》)
因此,瑛棨去世后,文焯兄弟为了生计不得不出京谋食。五年(1879)冬十月,文焯本欲赴上谷(现属张家口怀来县)谋职,卒未成。次年(1880)春,江苏巡抚吴元炳请李鸿藻、毛昶熙介绍,聘请文焯入幕为僚。故文焯携张宜人自京师至苏州,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幕宾生活。
文焯至苏州后,首先拜谒了居于苏州的俞樾,并请其为父瑛棨所作画题辞。俞樾曾与瑛棨同在开封共事,文焯晋谒俞氏的目的自然也是希望得到其帮助。本年秋,文焯携妻泛舟西湖,俞樾为其导谒彭玉麟,又为其寓所题写“诗窝”横额相赠。初至苏州的文焯,尽情地在秀美的江南山水中徜徉,结交了如傅怀祖、安山眠高上人、瑞莲庵鉴中长老、虎丘云闲禅师、寓苏日本本愿寺僧小雨长老等一干吴中名士。光绪七年(1881)秋,文焯梦游石芝崦作《记梦》诗,诗序云:
光绪辛巳秋七月十三日癸酉夜,梦游一山,洞西向,榜曰石芝崦。山虚水深,乱石林立,石上生如紫藤者,异香发越,坚不可采。屐步里许,闻水声潺潺出丛竹间,容裔滉漾,一碧溶溶,世罕津逮。时见白鹤横涧东来,迹其所至,有石屋数间,题曰瘦碧。
诗中有句云:“欲踏藓石寻幽蹊,元湣出入无町畦;忽从老鹤迹所至,曲房眑眑非尘栖。”此后,文焯即以“瘦碧”名庵名集,其号鹤道人、大鹤山人,皆源于此梦境所见。为记这一奇梦,文焯请名画家顾若波绘制《石芝西梦图》,俞樾、王闿运、沈秉成、吴昌硕等均为其题辞。
光绪九年(1883)春,文焯第二次晋京会试,落第南归。此间,与沈秉成结为忘年好友,流连于沈氏耦园,饮酒唱酬。又与洪钧、彭翰孙、陈寿昌等吴中名流或游山泛水,或园中集会,唱和相乐。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文焯移居庙堂巷汪氏壶园。三月,招潘钟瑞、吴昌硕、金心兰、姚觐元诸人集于壶园饯春。冬大雪中,又招龚易图等于壶园作东坡生日之会。似乎文焯并没有将仕途功名的得失放在心间,实则并非如此,游乐的表象并不能掩盖其积极干进之心。居于壶园之时,文焯致其妻弟叔璱信札有云:
北闱有何新闻,偕生之二子,果能假手必捷,亦不须买赋金矣。复丰(新简苏织造)是海李三弟否?与吾家有无渊源?乞示及。并乞吾弟速托豫丈,为兄谋一干馆,如世锡之按季致送之例,想弟必能善为说辞也。兄前有需托豫丈及仲华相国,切存旧馆,想当上达,务祈向豫丈切询,并转询荣相师更妙。兄有机械火炉,及精画纨扇物,本托子年由津径送豫丈,聊效一芹之献。于得子年信云,伊须先赴岭南,此二物已托黄公,到京交弟转致,必不致延误。兄随即上书求从者先容,因机器炉甚新,京师尚未有也。(略盦[桥川时雄]抄《郑大鹤手札》)
可见,文焯首先对科考新闻非常关注,并托人送礼请荣禄(仲华相国)等人帮忙为其谋取职位。然而,文焯的愿望并未实现。
光绪十二年(1886),文焯第三次晋京应会试,仍然荐卷不第,南归。十三年(1887)春,蜀中词人张祥龄(子苾)、蒋文鸿(次湘)与湘人易顺鼎(实甫)及其弟易顺豫(叔由)游吴,与文焯相交。此四子与文焯常聚于壶园,酬唱相和,因五人俱嗜白石词,故共结壶园词社,自春迄秋,联句遍和白石词,结成《吴波鸥语》一集。
光绪十五年(1889),文焯第四次入京会试,落第。取道沽上南归,适逢王闿运至津,文焯与于式枚、汤纪尚相约拜访,“相见即置酒论文,扬榷今故,意气相得甚欢,每慨然时事,悲悯之诚,切切满口”(戴《谱》)。这一时期,文焯与王闿运结下深厚友谊。本年秋,王闿运又至苏州,二人共校《墨经》,文酒雅宴、欢言晨夕。
光绪十六年(1890),文焯晋京应恩科会试,仍荐举不第。本年有诏开秘馆,广延通儒,因文焯精于音律,当道欲举文焯以正乐纪,不就。光绪十七年(1891)冬至次年春,况周颐在苏州,期间与文焯及张祥龄、易顺鼎等游览山水,联句唱和。为实现考中进士的梦想,文焯于光绪十八年(1892)第六次进京应会试,仍然落第归来。光绪十九年(1893),纳吴姬张小红(红冰)为妾,别居庙堂巷龚氏修园,以“冷红阁”贮之。文焯以“冷红”命名词集,并在此期创作艳词,都与纳红冰为妾相关。
光绪二十年(1894),文焯第七次会试不第。本年秋天,应两淮盐运使江人镜邀请,他与张祥龄赴扬州修盐志。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猖狂挺进,清军节节败退。文焯与张祥龄在赴扬途中,感慨战事,联句和梦窗词《莺啼序》,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已四十的文焯第八次参加会试,又一次落第。本年七月,文焯与刘炳照、夏孙桐、张上龢等在苏州成立了鸥隐词社,至次年春结束。秋,恰逢文焯四秩正寿,诸人结集为郑氏贺寿。文焯所作《念奴娇》自寿词云“沧海尘飞,故园秋澹。梦断挐云想。江关词赋,倦怀自任疏放。”“卧看青门锁旧辙,世外樵风相况。哀乐中年,登临残泪,付与玲珑唱。”可见其此时对四十尚无功名充满了悲哀,并道出了隐于世外的无奈。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文焯第九次进京应会试,仍落第。此次入京,尽管未得功名,但于郑氏的而言非常重要,他结识日后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两位友人王鹏运、朱祖谋。本年王鹏运在京师举咫村词社,邀请文焯入社。咫村词社期间,他多次与王鹏运、张仲炘、夏孙桐、朱祖谋等分题唱和。离京后,文焯在津沽一带游历,孤旅期间,多有感怀,所作词装成《鹤道人沽上词卷》。这些词作包含了落第之痛、飘零之苦以及对朝政腐败的不满。结束津沽之旅后,文焯又返回了京师,在京期间,恰逢戊戌政变,文焯以词笔记录这一政变惨剧,对维新同志被杀,光绪帝被囚禁表达了同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西逃西安,此即“庚子国变”。国难之际,居于苏州的文焯怅望觚棱,与困于京城的好友王鹏运、朱祖谋心灵相通,以词笔书写悲愤心情,创作了令人泣下的“词史”之作。
三
自光绪三年(1877)至二十六年(1900),文焯共参加了九次会试,均名落孙山。“遂决计弃仕进,仍回吴下卜居孝义坊,以束修之余,筑室以避世。每值春季,必驾扁舟往邓尉观梅,勾留数日始归。”(《行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廷补行辛丑会试,郑文焯因九试不中卒生绝意仕进之心。文焯放弃科考实是无奈之举,屡考不第的打击自会让其灰心失意,清廷的腐败和不可逆挽之颓势也让他感到前景灰暗。在这一时期,归隐山林成了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光绪三十年(1905)文焯在苏州孝义坊购地五亩,筑造房室,营建新居,并自榜其门曰“通德里”,又购置花卉草木,栽入园中。戴正诚记云:
先生于孝义坊购地五亩,建筑新居,秋初落成,即迁居其中,张筵庆五秩焉。从邓尉购嘉木名卉,杂莳屋之四周,颇擅林园之美。其东高冈迤逦,即吴小城故址,复作亭于城之高处,榜曰吴东亭,绕以竹篱,凭眺甚佳。城下有一水潆洄,即子城濠,所谓锦帆泾也。先生自谓以五亩之居,刻意林谷,即拥小城,聊当一丘,泾之水又资园挽,可以钓游不出户庭,而山泽之性以适者此也。(戴《谱》)
文焯精心设计园林,经营园中山水,其目的在于幽居其中,不出户庭即可日赏山水之美,与山水为伴,满足其“山泽”之性。
光绪三十四年(1908),文焯又一次扩建樵风别墅,其自制《樵风补筑上梁文》云:
光绪旃蒙大荒落之年,余既于吴小城粗营五亩之居,灌园著书,寂寞人外。……其词曰:桂丛之幽,聊可佳留。诛茅西隘,善草是谋。巢移一枝,书堆两头。蝉翳自簌,计惟周周。(戴《谱》)
从文焯所记可知其沉浸在山水园林之中,著书度日,不问世间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光绪丙午(1906),朱祖谋以病免礼部右侍郎,卜居吴门。文焯亲为相阴阳,拣时日,营新居,并作词坚定朱氏隐逸林下的志向,鼓励朱祖谋与自己共同消受林下真趣。其《惜红衣》词小序云:
彊村翁早退遗荣,旧有吴皋卜邻之约,朅来沪江,皇皇未暇,近将移家小市桥吴氏听枫园,先以书来,商略新营,作苍烟寂寞之友,却寄此以坚其志,再和白石。
宣统元年(1909)春,新君登极,起用旧臣,朱祖谋以特征不起。文焯置酒邀之,赋《木兰花慢》(闭门春不管)词,再次鼓励朱祖谋莫管尘事,不要响应朝廷的征召。词中“甚长安、花事等闲催”“胜看人、调鼎费羹材”二句,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失望。
光绪庚子(1900)后,保存国粹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自朝廷至民间,都有人员广泛参与,文焯也不例外。邓实在上海创办了《国粹学报》,欲于新学驰骛之际,借之保存绝学。文焯作为邓实之友,对其举动自是大力支持,时常将所撰文章及词作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粹学报》举行三周年庆祝时,文焯以所藏晋砖研拓作报端图画,并赋《浣溪沙》词相寄。郑氏还实际参与到保存国粹的运动中去,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苏巡抚陈启泰在苏州创办存古学堂,聘请文焯校艺。文焯在致夏敬观的信中说:
去春长沙抚部广张文襄保存国粹之议,奏设存古学校,以简易矩,则志在雄成。当时乡绅蒋翰林犹抵书讦诘,目为迂阔。幸赖臞老,毅然任之。剋期蒇役,群彦观成,蔚为美迹。以下走敝通籍,谬延禄及,忝预总校之末。……自是流风渐沫,玉振声希,节端固未暇及此,诸生瞻忽,兴感莫繇。至定章应行学期考试,今岁春余,会臞老病革,遂未举行,不日年例休假,兹役竟将缺焉。下走向于院校校课总其成,而一枝栖息,窃有未安,推原故府主提倡之盛心,能无冥冥之负?(《夏剑丞友朋书札》)
在这封信中文焯以存古学堂总校艺的身份对保存国粹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他也意识到保存国粹走向了衰弱,其为辜负巡抚之聘感到不安。保存国粹是文焯作为“江南退士”时参与的最重要活动,对他这一时期的金石、书画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四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天下风靡。文焯兄文炳、妹贞仪、弟少兰皆集于文焯寓所避难。本年末,宣统退位,共和局定。文焯伤怀鼎革,满腔孤愤,一于词发之。他以“苕雅”名集,抒发黍离之悲,哀悼清室之亡。
辛亥后,郑氏自称“樵风佚叟”“樵风真逸”“樵风逸民”“樵风遗老”“北海遗黎樵风叟”,明确点出自己的遗民身份。他又以陶渊明自比,辛勤批校陶集,寻觅与陶渊明的心灵共通。他说:
辛亥后,绝景穷居,无日不以陶诗自随,遂得其逸趣。偶有感触,辄题数行于简端,聊以寄慨云尔。八表同昏,人间何世,悲夫!
余居恒慕晋人风致,其高节美行,又独以靖节先生自况,尝论其《读史感述》之首章曰:“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其时当宋武改元,永初受禅之年,而先生行年五十有六已。自后有作,但题甲子,不著元号,旧国之感,异代同悲。患难余生,纪亦合昔以风致自况者,今不幸而身世更共之,恨无刘遗民辈,相从于苍烟穷漠中,琴酒流连,以送余齿,一醉不知人间何世。吁,可哀也已。(桥川时雄整理《陶集郑批录》)
郑文焯认为自己与陶渊明一样,都是五十六岁之时身遭亡国之变,虽是“异代”,但同悲“旧国之感”是一样的。因此他以陶渊明的“高洁美行”自况,同时也以自己之情感设想陶渊明,为没有志同道合之人而感到遗憾。
袁世凯当政时,开清史馆,曾延请文焯为纂修,但“他对袁印象极坏,坚不应聘”(高拜石《词人贵公子——大鹤山人郑叔问》,《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七],第21页)。民国六年(1917),文焯致书友人程淯云:
昔潘文勤公尝谓三十年来,真能淡于荣利,著书自娱,终身不士者,惟南北两举人,盖谓湘绮翁及下走耳。今湘绮既殁,而晚节为世诟病,迄今犹申申詈之,能无愁然。(程淯辑《鹤语——大鹤山人郑文焯手札》)
信中提及的“湘绮翁”指王闿运。民国三年(1914),王闿运接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文焯所言“晚节为世诟病”即指此事。在文焯看来,王闿运担任国史馆馆长,就是丧失气节的行为。
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请罗惇曧聘文焯至京,担任金石学科主任及校医,也被其回绝。其次年一月致罗书云:
昨承寄示孑民先生函订大学主任金石学教科兼校医一席,月廪约四百番钱,礼遇诚优且渥。第念故国野遗,落南垂四十年,倦旅北还,既苦应接,且闻京师仆赁薪米之费什倍于南,居大不易。蒿目世变,何意皋比,颓放久甘,敢忝为国学大教授邪?业医卖画,老而食贫,固其素也。辱附契末,聊贡区区,未尽愿言,但有荒哽。(戴《谱》)
他在致程淯书中也提及拒绝征召之事:
辛壬以来,一拒公府之聘,再却史馆之征,匪敢遗世鸣高,诚以穷老气尽。古之达士,苟全乱世,皆藉一艺以自存,史迁所谓贤者不危身以治生也。(程淯辑《鹤语——大鹤山人郑文焯手札》)
又致书康有为,告知拒绝北京大学之事。康氏记云:
戊午一月,君以书来曰:“大学之聘已却之,昔者清史馆之聘,忍饿而不就,岂至今而复改节哉?(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91页)
可见,文焯甘当“故国野遗”,不愿改变自己的“节操”以治生,也正因此,其家境陷入极度窘困。只能“出其余技,鬻画行医,聊以赡家。时往还淞苏间,劳劳于渊明所谓倾身营一饱也”(戴《谱》)。最终平生收藏金石、书画名迹,也尽鬻去。
民国六年(1917)冬,妻张宜人卒,文焯已落到无法安葬亡妻的地步。“典质既无长物,鬻书卖画,又非济急之具。”(1917年十一月廿五日致程淯书,《鹤语——大鹤山人郑文焯手札》)不得已托程淯帮忙,请求在京师的罗惇曧向梁启超求救。得梁启超等人“颁逮三百金,周急救凶”(戴《谱》),方才完结营奠之事。
生活的极度窘迫,加之张宜人的离世,让文焯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民国七年(1918)二月二十二日早起,文焯痰涌舌蹇,汗流不止,医治无效,于二十六日逝世,行年六十三岁。文焯临终前,将身后之事全部委托给康有为。本年十月,在康有为、朱祖谋等人的帮助下,将文焯与张宜人合葬于邓尉山中。故人朱祖谋、梁启超、夏敬观、吴昌绶、易顺鼎等函请内务总长钱能训,请其致函江苏省长转行吴县知事,将其住宅、坟茔分别立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