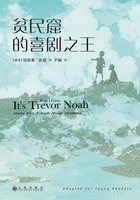
第3章 跑
妈妈把我从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里扔出去的时候,我9岁。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周日。我之所以记得那天是周日,是因为我们当时正行驶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我童年的每个周日都要去教堂。我们从来没有错过教堂活动。我的妈妈一直笃信宗教。她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与世界上其他原住民一样,南非黑人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了宗教信仰。我说的“继承”是指强加于我们。
童年时,我每周至少有4个晚上要参加教会活动。周二晚上是祈祷会。周三晚上是《圣经》学习。周四晚上是青年教会活动。周五和周六休息。周日则要去教堂。确切地说是去三座教堂。我们之所以要去三座教堂,是因为妈妈说每座教堂赐予她不同的东西。第一座教堂给予她对上帝的喜悦的赞美。第二座教堂会对经文进行深入解析,她十分喜欢这一点。第三座教堂则让她感受到激情和净化,那里能让人真正感受到圣灵附体。而在我们奔波于这三座教堂的时候,我意外发现,每座教堂都有其独特的种族构成:洋溢着喜悦之情的教堂是多种族混合教堂,擅长解析的教堂是白人教堂,而激情澎湃的教堂则是黑人教堂。
混合教堂名为雷玛圣经教堂。这座教堂是规模宏大的超现代郊区大教堂中的一员。牧师雷·麦考利曾是健美运动员,时常笑容满面,拥有啦啦队员般的性格。雷牧师曾参加1974年的环球先生健美大赛。他获得了第三名。那一年奥林匹亚先生健美大赛的冠军是阿诺德·施瓦辛格。每周,雷都会站在台上,竭尽全力让耶稣看起来很酷。教堂里有舞台风格的座席和摇滚乐队,会演奏最新的基督教当代流行乐。所有人都随之歌唱,你不知道歌词也没关系,因为它们都在超大屏幕电视机上为你准备着。这基本上就是基督教卡拉OK。我在混合教堂总是兴高采烈。
白人教堂是桑顿的罗斯班克联盟教堂,那一片就是约翰内斯堡典型的白人富人区。我爱白人教堂,因为我不用参加主日祷告。我的妈妈会参加,而我会去青少年参加的主日学校。在主日学校,我们会读很酷的故事。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故事当然是我的挚爱,我的名字跟它有密切关系嘛。但我也喜欢摩西分开红海、大卫斩杀歌利亚巨人和耶稣在圣殿驱逐货币兑换商的故事。
我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流行文化。我的妈妈不想我的精神被性和暴力污染。我唯一真正知道的音乐来自教堂:赞美耶稣的令人振奋的高亢之歌。我对电影的了解也一样。《圣经》就是我的动作电影。参孙就是我的超级英雄。一个人用驴的下颚骨打死了一千个人?真是太带劲了。最后读到保罗给以弗所人写信的那部分时,就少了一些情节性。《旧约》和福音书呢?这部分无论哪一页、哪一章、哪一节的内容,我都能张口就来。每周在白人教堂还有《圣经》游戏和知识竞赛,我总能轻松战胜所有人。
然后就是黑人教堂。黑人教堂总有一些黑人教堂礼拜仪式在进行,而我们都会去参加。在只有黑人聚居的镇上,这种教堂一般是指“帐篷复兴式”户外教堂。我们通常会去外婆的教堂,那是一座传统卫理公会教堂,五百名身穿蓝白相间衬衫的非洲老奶奶,紧握《圣经》,耐心地经受非洲烈日的炙烤。黑人教堂很简陋。没有空调。大屏幕播放歌词。礼拜仪式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每次至少要进行三四个小时,这让我很困惑,因为白人教堂的礼拜仪式好像只有一小时,整个过程似乎就是大家进场、退场,以及牧师感谢大家的到来。可是在黑人教堂,一坐下就好像要坐一辈子,其间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我最后得出结论,黑人需要更多时间跟耶稣待在一起,因为我们遭受了更多苦难。
黑人教堂有一个可取之处。如果我能坚持到第三或第四小时,就能看到牧师驱魔。被恶魔附身的人会像疯子一样在过道里跑来跑去,操着一口方言惊声尖叫。而教堂的引座员会像夜店保安那样对付他们,压制住他们。牧师则会抓住他们的头,用力地前后摇晃,同时嘴里大叫着:“我奉耶稣之名,驱赶恶灵!”有些牧师更为粗暴,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直到恶魔消失,教友瘫软无力地倒在台上后,才会停手。接受驱魔的人必须倒地不起。因为如果他不倒地,就意味恶魔很强大,牧师需要向他发起更猛烈的攻势。你也许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中后卫,那也没关系,这里的牧师会把你放倒。上帝啊,这可太有趣了。
基督教卡拉OK、激烈的动作故事和暴力信仰治疗师——天哪,我爱教堂。我不喜欢的是去教堂的那段长长的路程。那可真是一段艰难的长途跋涉。我们住在伊甸公园附近,那是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个小社区。我们要花一小时才能到白人教堂,再花45分钟才能到混合教堂,接着再开45分钟的车才能到位于索韦托的黑人教堂。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还有更糟的,某些周日,我们还会开车回到白人教堂参加特别的晚间祷告活动。等到我们终于在夜里回到家的时候,我会一头栽倒在床上。
这个特别的周日,也就是我从一辆行驶的车里被扔下来的那个周日,一开始跟其他周日一样。妈妈叫醒我,给我准备好早餐喝的粥。我去洗澡,她给9个月大的弟弟安德鲁穿衣服。然后我们出门来到车道上,可是当我们都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的时候,车却发动不起来。妈妈的这辆亮橙色大众甲壳虫又旧又破,她没花几个钱就把它买了回来,而它总是坏。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讨厌二手车。我每次都买有保修服务的新车。虽然我爱教堂,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意味着要走两倍的路程,以及承担两倍的痛苦。大众汽车拒绝启动的时候,我一直在祈祷:请说我们就待在家吧,请说我们就待在家吧。然后我瞥见妈妈脸上坚定的表情,她的下巴绷得紧紧的,我就知道,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快点,”她说道,“我们去搭小巴。”
我妈妈有多虔诚,就有多固执。一旦她拿定主意,就没法改变了。
“是魔鬼,”她这样解释汽车无法发动的原因,“魔鬼不想让我们去教堂。所以我们必须搭小巴去。”
每当我想反驳一下妈妈这种基于信仰的固执己见时,都会尽量以非常尊敬的口吻提出相反的意见。
“也许,”我说道,“上帝知道今天我们不应该去教堂,所以才让车发动不起来,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待在家里,休息一天,因为今天连上帝也休息。”
“啊,你那是魔鬼的话,特雷弗。”
“不,因为耶稣掌控着一切,如果耶稣掌控着一切,我们向他祈祷,他就会让车发动,但他没有,所以——”
“不,特雷弗!有时候耶稣会设置障碍,看看你是否能克服。就好像给你出点难题。这可能就是个测试。”
“啊!是的,妈妈。可这次测试可能是想看看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因此待在家里,赞颂耶稣的智慧。”
“不。魔鬼的话。”
“可是,妈妈!”
“特雷弗!Sun'qhela!”
“Sun'qhela”有很多含义。它可以表示“别唱反调”“别小看我”以及“试试看”。它既是一种命令,也是一种威胁,两者兼而有之。科萨族家长经常对孩子说这个词。一听到它,我就知道这意味着对话结束了,而如果我再多说一个字,就会被揍一顿。
那时,我就读于一所名为玛丽韦尔学院的私立天主教学校。我年年都是玛丽韦尔运动会的冠军,而我妈妈则年年都拿回属于妈妈的奖杯。为什么?因为她总是追着要揍我,而我总是逃跑不让她揍到我。没人能像我和我妈妈跑得那么快。
我们的关系就像猫和老鼠。她纪律严明,我则调皮捣蛋。她让我出去买东西,我一般不会买完就回家,而是会用买牛奶和面包剩下的零钱在超市玩街机。我爱电子游戏。我是玩《街头霸王》的高手。一盘游戏我可以玩很久。投下一枚游戏币,时间就嗖嗖地飞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身后会出现一个拿着皮带的女人。这就是一场赛跑。我会夺门而出,穿过尘土飞扬的伊甸公园附近的街道,翻过围墙,溜进别人家的后院。这种事在我们这片很常见。大家都知道:那个叫特雷弗的孩子会横冲直撞跑过来,而他的妈妈则会在后面紧追不舍。她能踩着高跟鞋全速奔跑,但如果她真的想追上我,就会以奇异的姿势扭动脚踝踢飞高跟鞋,而这一过程中她甚至不会踏空任何一步。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明白,好吧,她进入加速模式了。
我还小的时候,她总是能抓住我,可是随着我年龄渐长,跑得也更快了,她的速度再也跟不上时,她就开始动用智慧。如果我准备逃跑,她会大叫:“站住!小偷!”她知道这样附近的人都会来对付我。会有陌生人应声来抓我,想把我摁住,我不得不左躲右闪,同时放声大喊:“我不是小偷!我是她儿子!”
那个周日的早晨,我最不想做的就是爬上拥挤的小巴,可是,当我听见妈妈说“Sun'qhela”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一锤定音。她抱着安德鲁,我们从那辆大众车里下来,走出门去搭车。
纳尔逊·曼德拉出狱那年,我5岁,就快6岁了。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大事件,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但大家就是这么高兴。我当时才意识到,有个东西叫种族隔离,而它要结束了,这是个大事件,但我并不理解其中错综复杂之处。
让我牢牢记住、始终无法忘怀的是随之而来的暴乱。民主战胜种族隔离的过程有时候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白人没怎么流血。但黑人的血却洒满街头。
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我们知道现在黑人要开始治理这个国家了。问题是,该由哪个黑人掌权呢?因卡塔自由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权力争夺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冲突。这两个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复杂,但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法就是把双方的斗争看成是祖鲁人和科萨人之间的战争。因卡塔自由党主要由祖鲁人组成,非常激进,坚持民族主义。非洲人国民大会则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但当时领导层主要是科萨人。他们非但没有联合起来谋求和平,反而针锋相对,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行为。大规模骚乱爆发。每天晚上,我和妈妈都会打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收看新闻。12个人被杀。50个人被杀。上百人被杀。最后,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伊甸公园距离东兰德、托卡扎和卡塔翁3个镇子都不远,而这几个地方是因卡塔自由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会看到附近街区燃起熊熊大火。数以百计的暴徒聚集在街头。这时妈妈会慢慢地开车从人群边缘蹭过去,绕过由燃烧的轮胎设置的路障。没什么能像轮胎那样燃烧,你无法想象那种怒焰冲天的景象。
无论何时爆发骚乱,所有邻居都会明智地关紧门,躲在家里。但我妈妈不这样。她还是正常出门,在我们小心翼翼穿过路障的时候,她会给骚乱者们一个这样的表情:让我过去,我跟这场混乱没关系——她就是这样临危不惧。我一直对此惊叹不已。哪怕我们的家门口正在打仗也影响不了她。她有事要做,有地方要去。正是这种固执,让她在汽车抛锚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去教堂。
那个周日,我们在几座教堂之间辗转奔波,最后来到了白人教堂。当我们走出罗斯班克联盟教堂时,天已经黑下来,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经过一整天无休止的小巴之旅,我已经筋疲力尽。当时至少已经9点。那时候四处暴乱不断,没人那么晚还待在外面。我们站在杰里科大道和牛津路的交叉路口,那是约翰内斯堡富有白人郊区的中心地带,没有小巴。街上空空荡荡。
我真想对我妈妈说:“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上帝想让我们待在家的原因。”但我瞥了一眼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最好还是闭嘴。
我们等了又等,期待会有一辆小巴经过。种族隔离时期,政府不给黑人提供公共交通工具,但白人仍然需要我们去帮他们擦地板、打扫浴室。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发明,黑人发明出了自己的交通系统,一条条由私人组织非法运营的非正式公共汽车线路,完全游走于法律之外。不同组织运营着不同线路,彼此之间会为争夺控制权而发生冲突。相关贿赂和暗中交易的事情时有发生,暴力事件屡见不鲜,还有人需要支付大笔保护费以避免施暴行为。你绝不能偷偷跑竞争对手的线路。偷跑线路的司机会被杀死。由于无人监管,这种小巴也很不可靠。车子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站在罗斯班克联盟教堂外,我几乎就要趴在地上睡着了。一辆小巴的影子都没见到。我妈妈终于开口道:“我们搭便车吧。”我们走啊走,好像走了一辈子那么久,终于有一辆车开过来,停了下来。司机愿意载我们一程,于是我们爬上车。车还没开出三米远,一辆小巴突然拐到我们面前,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一个祖鲁族司机拿着一根“iwisa”走下小巴,那是一种巨大的传统祖鲁族武器,简单来说就是一根打仗用的木棒。它的用途就是敲碎别人的脑袋。另一个人——他的跟班——则从副驾驶座走了出来。他们径直走到我们乘坐的汽车的驾驶座旁,一把抓住那个愿意载我们一程的男人,把他拖出驾驶座,用木棒朝着他的脸一顿乱揍。“你为什么要偷走我们的客人?你为什么搭人?”
他们看起来好像要把他打死一样。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时,我妈妈开口说道:“嘿,听着,他只是在帮我。放开他。我们去坐你们的车。我们一开始就是想搭你们的车。”于是我们走出第一辆车,爬上小巴。
我们是小巴上唯一的乘客。除了顶着暴力黑帮分子的名头,南非小巴司机还因开车时爱发牢骚和教训乘客而臭名远扬。而这个司机正好是特别暴躁的那种。发车后,他就开始教育我妈妈,说她竟然去搭丈夫以外的男人开的车。我妈妈并没有老实接受陌生男人的教育。她让他少管闲事,而当他听到她说科萨语时,着实被激怒了。大家对祖鲁族女人和科萨族女人的成见,与对这两个种族的男人的成见一样根深蒂固。祖鲁族女人行为端正又守本分。科萨族女人则行为有失检点又不忠实。而我的妈妈就是他的民族敌人,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科萨族女人,其中一个还是混血儿,正好验证了人们的成见。“噢,你是科萨人,”他说道,“这就说明了一切。让人恶心的女人。今天晚上就要让你尝点教训。”
他开始加速。他开得很快,一路都没有停,只有在十字路口稍微减速查看一下交通状况,然后又加速通过。死亡从未离我们如此之近。我妈妈可能受到伤害。我们可能被杀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并不是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究竟有多危险,我太困了,一心只想睡觉。而且,我妈妈表现得十分冷静。她没有惊慌失措,所以我也不知道害怕。她只是一直在跟他理论。
“如果我们惹恼了你,我道歉,老兄。你可以让我们就在这里下车——”
“不。”
“真的可以,没关系的。我们可以走——”
“不。”
他沿着牛津路疾驰,路上空空荡荡,没有一辆其他的车。我坐在离小巴推拉门最近的地方。我妈妈就抱着小安德鲁坐在我旁边。她看向窗外飞逝而去的街道,然后靠近我,低声说道:“特雷弗,等他在下个十字路口减速的时候,我会打开车门,我们就要跳下去。”
她说的我一个字都没听见,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打盹。当我们来到下一个红绿灯前时,司机松了油门,四处张望,查看路况。我妈妈伸手拉开车门,一把抓起我,使劲把我往远处扔。然后,她抱着安德鲁,紧跟着我跳下了车。
一开始我还像在做梦,直到感到一阵疼痛。砰!我狠狠地摔在人行道上。我妈妈就落在我身旁,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连翻带滚。现在我彻底清醒过来。最后,我终于停了下来,支起身子,彻底晕头转向了。我看了看四周,看到了妈妈,她已经站了起来。她转头看向我,尖叫起来。
“快跑!”
我应声狂奔起来,她也跑起来,没人能像我和我妈妈这样跑。
这一切很难说清楚,我只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一种动物本能,当你生活在暴力无处不在、随时可能爆发的世界时,就会习得这种本能。在镇子上,当警察携带防暴装备,开着装甲车和直升机发动突袭的时候,我就知道:跑去找掩护。跑去躲起来。虽然我才5岁,但我知道要怎么做。就像瞪羚跑着躲避狮子,我也跑起来。
那两个男人停下小巴,下车想要追我们,但他们根本追不上。我们让他们领教了什么叫望尘莫及。我想他们一定惊呆了。我仍然记得当时回头看的那一眼,我看见他们停了下来,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不知道正在追的是玛丽韦尔学院运动会的卫冕冠军。我们一直跑到一家24小时加油站才停下来,打电话报了警。而那些人早就走了。
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是一直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狂奔。一停下来,我就感觉浑身疼得不行。我低下头,发现手臂擦破了皮,伤口还裂开来。我身上到处是伤口,到处都在流血。我妈妈也一样。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弟弟却毫发无伤。妈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他因此安然无恙。我惊讶地看向她。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跑?”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跑’是什么意思?那些人要杀了我们。”
“你根本没告诉我这些!你只是把我扔出了汽车!”
“我告诉你了。你为什么没跳车?”
“跳车?我正在睡觉!”
“这么说,我应该把你留在车上,让他们杀了你?”
“至少他们会先叫醒我,再杀我。”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斗着嘴。我实在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扔下车,也实在是很生气,完全没有意识到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妈刚救了我一命。
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等警察来把我们带回家,她说道:“好吧,至少我们安全了,感谢上帝。”
这次我没有保持沉默。
“嘿,妈妈,”我说道,“我知道你爱耶稣,但也许下周你可以请他到我们家来看我们。因为今晚发生的事可不好玩。”
她突然咧嘴大笑起来。我也开始哈哈大笑。深夜路边的加油站里,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就这样站在加油站的灯光下,一起哈哈大笑,两人的手臂和腿上还淌着血,沾着泥。
***
种族隔离制度是种族主义的完美表现形式。它历经数百年发展成形,早在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好望角登陆,并建立了贸易殖民地卡普斯塔德,也就是后来的开普敦,这里成为往来于欧洲和印度之间的船只的休息站点。为了实行白人统治,荷兰殖民者与当地人开战,最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压制和奴役他们。当英国人接管开普敦殖民地后,原荷兰殖民者的后代就长途跋涉来到内陆地区,在那里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最终自成一族:阿非利卡人——非洲白人。
英国人名义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实际上却仍在使用奴隶。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19世纪中期,在这个被看作是通往远东的旅途中几乎毫无价值的中转站的地方,一些幸运的资本家偶然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和钻石储备,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可以牺牲的劳动力深入地下,把黄金和钻石挖出来。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阿非利卡人一跃而起,宣称南非是其合法继承物。面对日益壮大且蠢蠢欲动的黑人多数群体,政府意识到,想要巩固权力,就需要一套更新颖、更有力的手段。他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派人走出南非,研究世界各地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他们去了澳大利亚。他们去了荷兰。他们还去了美国。他们看到了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无效。然后,他们回到南非,发表了一份报告,政府则利用这些知识,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种族压迫体制。
种族隔离制度代表着一个警察国家,一个监视系统,一系列旨在使黑人处于绝对控制之下的法律。如果要将这些法律条文完整汇编在一起,将是一本超过3000页的大部头,重量大约为4.5千克,但任何一个美国人应该很容易就能理解其主旨。在美国,当地土著被迫迁移到保留区,随之而来的还有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想象一下,这三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群人身上。这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