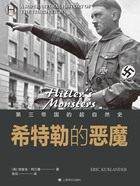
第二章 从修黎社到纳粹党
纳粹超自然想象的形成,1912—1924
“如果说有什么是非种族的[unvölkisch],那就是对旧日耳曼的表达折腾来折腾去,而那些表达既适应不了当今时代,也不代表任何明确的东西……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那些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他们]对古老的日耳曼英雄主义,对晦暗的史前时期、石斧、长矛和盾牌都是在胡说八道。”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24)(1)
“希特勒最初找的是修黎社的人;是修黎社的人最先和希特勒联合了起来。”
——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193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一名26岁的学艺术的学生因在西线负了伤而从德国军队除役。这名野心勃勃的年轻艺术家出生在德意志帝国之外,对泛德意志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凡是有关条顿人历史和神话的文学作品,他都会找来阅读。1917年底来到慕尼黑之后,他与人合作成立了一个团体,想要创建德意志第三帝国。该团体采纳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神秘学想法,如雅利安智慧学的种族主义,以及万字符之类的秘术符号。(3)不到几个星期,年轻艺术家讨论圈内的两名成员便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党(DAP),后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14年后,该党便上台掌权了。(4)
这些生平细节近乎完美地描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轨迹。只是这个所谓的年轻艺术家并非希特勒,而是瓦尔特·瑙豪斯,他是日耳曼圣杯骑士团的领袖,并与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合作创建了亲纳粹的修黎社。(5)玄学家瑙豪斯的早期意识形态和创建组织的轨迹与希特勒几乎重叠,如此便引出了一个老问题:奥-德的超自然环境和初创的纳粹党究竟有什么关联?
雅利安智慧学家和其他种族论-秘术团体都意识到,他们在战前的学说和1919年之后的民族社会主义具有相似性。兰茨·冯·利本费尔斯和他战后的出版人赫伯特·莱希施坦都坚持认为,纳粹的意识形态清晰地体现了战前奥-德的玄学环境。正如塞博滕道夫在上述的引文中暗示的那样,他认为纳粹党就是他的雅利安智慧学的修黎社的直接产物。(6)大量种族论-秘术领袖和种族论-宗教领袖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都认为第三帝国实现了他们的“新异教”信仰。(7)
而过去30年来,历史学家却一直在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微弱。有些人以从前面所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话为证,认为纳粹对玄学和异教并不感兴趣。另一些人则指出,修黎社的领导人对第三帝国从未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8)
本章将会从三个方面探讨修黎社在塑造纳粹党方面所起的作用。首先,会对威廉时代后期如日耳曼骑士团之类的雅利安智慧学团体和纳粹党从中脱胎而出的修黎社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其次,考察上述引文中塞博滕道夫的话,追溯修黎社对纳粹党早期的创建产生的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本章会对希特勒关于雅利安-日耳曼、神秘学、边缘科学思想的讲话对早期纳粹党的影响进行考察。本章认为,威廉时代种族论-秘术环境、修黎社和早期德意志工人党之间的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关联,比许多学者所认识到的更丰富、更具实质性,以至于超自然思维深深地烙在了纳粹运动的核心之中。
一、从日耳曼骑士团到修黎社
为避免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军队中服役,希特勒于1913年5月逃离了他深爱的维也纳,去了慕尼黑。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内,种族论-秘术的重心也随希特勒一道迁移。圭多·冯·李斯特和约尔格·兰茨·冯·利本费尔斯、弗朗茨·哈特曼和鲁道夫·施泰纳、汉斯·霍尔比格和卡尔·马利亚·威利古特都是奥地利人,但他们的理念都是在德国得到了最大化的政治上和知识上的表达。
从威廉帝国的最后几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后的最初几年,数以百计的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西里西亚人创建了多如牛毛的雅利安智慧学分支团体。阿尔萨斯-洛林人鲁道夫·冯·高斯雷本创立了埃达学会(Edda Society),继续李斯特对古日耳曼卢恩文字的研究。西里西亚玄学家赫伯特·莱希施坦战后成为兰茨的出版人,替他在柏林找到了受众。萨克森的雅利安智慧学家和占星师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搬去了慕尼黑,与人合作创建了修黎社。(9)
这些雅利安智慧学分支团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特奥多尔·弗里奇在萨克森创建的日耳曼骑士团。这是个典型的雅利安智慧学社团,充满了玄学仪式和有关“根种族”的奇奇怪怪的边缘科学理论。在创建日耳曼骑士团的时候,弗里奇还决定同时创建一个政治团体,将他的种族论-秘术规划传播给广大的民众,那就是“帝国铁锤协会”(Reichshammerbund)。(10)这个名字取自他那家声名狼藉的反犹出版社——“锤子”(Der Hammer),这家出版社的目的是以“日耳曼人比‘低等种族’优越”和“对犹太人的无情仇恨”为基础,使“雅利安-日耳曼”宗教得以复兴。(11)
和其他出现在德意志帝国最后20年间的种族论团体一样,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铁锤协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无政治权力或影响力。但在威廉时代后期的种族论环境和纳粹党早期之间,默默无闻的日耳曼骑士团变成了战时一个重要的中继站。在瑙豪斯和塞博滕道夫的领导下,脱离了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的慕尼黑分支将会找到新的生命,并以一个新名字示人:修黎社。
日耳曼骑士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特奥多尔·弗里奇并非种族论政治的新手。他是德国最早也是叫嚣得最凶的反犹的种族主义者之一,出版了德国最老的反犹报纸《反犹通讯》(Anti-Semitic Correspondence)。1890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代表持激进的种族论和反犹的德国社会主义党,后来在社会改良派右翼发挥了重要作用。(12)弗里奇对种族-秘术论充满了热情,跟他想要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消灭掉的心情一样急切,他以“弗利茨·托尔”这个笔名发表文章,还加入了圭多·冯·李斯特学会和兰茨的新圣殿骑士团(ONT)。(13)
不过,弗里奇想要在日耳曼骑士团/铁锤协会中将种族-秘术论和大众政治结合起来的做法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乍一看,这两个组织似乎和在它之前的新圣殿骑士团或德国社会主义党没多大区别。日耳曼骑士团和铁锤协会的共同创建者菲利普·施陶夫与赫尔曼·波尔都是有名的雅利安智慧学家。施陶夫还是李斯特学会、阿尔玛恩骑士团的高级成员,波尔则是萨克森当地的“沃坦小组”的领导人。(14)
和新圣殿骑士团一样,日耳曼骑士团也要求成员遵守含糊不清的种族标准,如“雅利安条款”规定的不得有犹太人血统。日耳曼骑士团还以共济会为榜样进行秘密仪式,并出版了一本名为《卢恩文字》(Runen)的雅利安智慧学杂志,封面上印着万字符。铁锤协会也有自己的玄学色彩。它由一个类似于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阿尔玛恩委员会”(Armanen-Rat)领导,委员会的12个人全部是从李斯特那儿借来的。弗里奇使用“低等人种”一词来指代犹太人和低等种族,这样的表达也透露出它和李斯特及兰茨的边缘科学中的种族论颇有渊源。(15)
然而,在日耳曼骑士团/铁锤协会同早期种族论政党之间存在重大差别。铁锤协会的目标是超越威廉时代反犹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之前,铁锤协会就已经在德国全境开花,分支遍布奥地利和德国。它还想要将所有的“种族主义改良团体”与“民族”的和“社会”的价值观整合到一起,将信奉种族论的商人和民族主义工人、军官和教授、农民和店员团结起来。(16)为了超越德国根深蒂固的阶级和告解氛围,弗里奇敦促“和天主教徒合作,向工人、农民、教师、官员、军官大力宣传,并在大学开展特定的活动”。(17)最终,日耳曼骑士团的个别分支还发展出了自己的青年运动,再次为纳粹党做了准备。(18)
弗里奇和波尔还设法建立了一个由志趣相投的职业政客及知识分子组成的非常广泛的联盟。其中就包括诸如李斯特、兰茨、伯恩哈德·克尔纳这些常见的人,伯恩哈德·克尔纳在签名时用的就是卢恩符文(后来,他在党卫军里扮演了重要角色)。(19)塞博滕道夫也是其中一员,还饶有兴味地回忆起了日耳曼骑士团在奎德林堡附近举行的一次会议,奎德林堡在哈尔茨山脉“布罗肯山”脚下,那儿是歌德的《浮士德》里“瓦尔普吉斯之夜”的所在地(后来纳粹还在那儿进行了考古)。(20)除了这些彻头彻尾的种族-秘术家,这份名单上还得加上一些著名的同行者,比如国防军元帅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德国保守派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以及泛德意志联盟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21)
考虑到铁锤协会意识形态上的前身以及它在政治上的支持者,它的规划里充斥着种族主义的歇斯底里,认为雅利安-日耳曼人和人数少些的“低等人种”之间必有一场末世之战也就不足为奇了。(22)在弗里奇和波尔的意识形态核心中,“病态的反犹主义和对日耳曼或北欧种族固有优越性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23)第三帝国成立之前的20年间,他们主张驱逐“寄生虫似的整天想着革命的暴民种族(犹太人、无政府主义混血儿,以及吉卜赛人[原文如此])”。(24)在1939年1月希特勒臭名昭著的预言之前,波尔就已宣称如果犹太人“准备发动战争或革命”,就会通过“神圣的菲默法庭”将他们消灭,菲默法庭将让“这群罪犯尝到他们自己的武器的苦果”。(25)
在此,我们看到了生物学上的神秘论种族主义和对政治暴力进行的类似末世论的合理化,这为以后纳粹的超自然想象铺平了道路。波尔不仅主张屠戮犹太人,还不带一丝嘲讽地提及了中世纪在威斯特法伦杀害“罪犯”的半神秘的秘密法庭,以此使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谋杀具有合法性。
在经济和政治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铁锤协会吸引支持者有一定难度。其精英主义的构架、种族主义的严格要求、令人望而却步的会费,也限制了入会。此外,铁锤协会的内部纷争乃是家常便饭,这也导致1912年之前的30年里,各种持种族论的反犹政党都没什么起色。(26)因此,铁锤协会就相当于介于玄学骑士团和现代种族论政治组织之间的过渡团体,将秘密仪式和怪异的种族理论与野心勃勃的社会政治议程以及地域来源多样的民族主义组织糅合在了一起。(27)
等到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时候,铁锤协会和日耳曼骑士团都陷入了混乱。这主要是因为近半数成员被征召入伍了。但是,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精英主义架构以及战争期间举办花费不菲的宴会,都在继续让许多潜在的支持者望而却步。正如波尔在1914年11月写给一名成员的信中所说,“战争太早地落到了我们身上,日耳曼骑士团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如果战争持续得太久,它就会分崩离析”。(28)
即便这场战争挑战了日耳曼骑士团的资产阶级基础,但它也为群体政治开辟了道路。它击碎了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德国人开始“落入最古老、最原始的人类幻想的怀抱,期望愿望能够达成,有更美好的未来……魔法世界观和迷信的领域”。(29)以前不过问政治的玄学家现在也都认为,战争“从宇宙层面来看有其必要性……在‘精神世界的存在’中体现了宇宙的进程……当各个国家打来打去的时候,恶魔和精灵的世界透过人类发挥着作用”。(30)战争的最后两年,随着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德意志民族主义右翼的种族乌托邦幻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31)
弗里奇和波尔试图借战时易于激进化,创建一个更为广泛的种族-民族主义联合体。但铁锤协会最终被并入了德意志民族主义保护和防卫组织(Schutz-und Trutzbund),它是魏玛共和国早期影响力颇大的民族主义社团之一。(32)由于日耳曼骑士团的大多数分部要么解散,要么并入更大的民族主义团体之中,由波尔领导的慕尼黑分部也分裂出去,成了圣杯骑士团的瓦尔法特(Walvater)分部。(33)
加入波尔的瓦尔法特分部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塞博滕道夫出生于萨克森的一个中等偏下的中产阶级家庭,原名亚当·阿尔弗雷德·鲁道夫·格劳厄,1890年代初短暂攻读过工程学。(34)后来,塞博滕道夫放弃了学业,先后去了埃及和土耳其。他全神贯注于神智学、伊斯兰教苏菲派和占星术,在研究占星术的时候,与一个希腊犹太人合作,后者引荐他加入了共济会。为了收支平衡,塞博滕道夫在基辅的一个犹太社区当家庭教师,甚至还成了土耳其公民。(35)尽管(或许是因为)塞博滕道夫一直浸淫于东方宗教和共济会之中,但他还是更倾向于雅利安智慧学,认为影响他的人主要还是李斯特、兰茨、弗里奇。(36)
如果从更广泛的奥-德超自然想象的背景来看塞博滕道夫的话,那他从一个看似普世主义的知识分子转变为种族-秘术师就说得通了。(37)塞博滕道夫对影响了拉加德、施泰纳、兰茨的“东方”神秘主义和东方宗教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痴迷。作为种族-秘术师的典型代表,塞博滕道夫并没觉得将激进的种族主义和反犹观同社会进步观、选择性的世界主义观(从东方灵性论和印度-雅利安种族超民族的兄弟情谊中汲取了养分)相结合有什么矛盾之处。日耳曼骑士团、修黎社和后来的纳粹运动都将保留这种极端的种族民族主义和印度-雅利安主义的结合。(38)
在经历了土耳其的插曲之后,塞博滕道夫返回了德国。他很快就加入了柏林的一个围绕一份名叫《魔页》(The Magic Pages)的报纸活动的玄学团体,在那里,塞博滕道夫撰写了一份关于魔法护身符的手稿。(39)他还成了占星术专家,1920年代初还被任命为卡尔-布兰德勒-普拉希特的《占星术评论》的编辑。(40)在柏林,作为一个不完全被社会接受的人待了几年之后,已加入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的塞博滕道夫去了慕尼黑。(41)1917年,他在圣杯骑士团的瓦尔法特分部参加了一场由波尔主持的会议。波尔对塞博滕道夫的种族-秘术信仰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邀请这位巡回占星师加入骑士团,并委托他重启巴伐利亚分部。(42)
从许多方面来看,塞博滕道夫去的瓦尔法特分部和之前的日耳曼骑士团并无多大区别。他把该分部设想为一个“社会-民族组织”,将“病态的反犹主义和对日耳曼或北欧种族固有的优越性的观念”结合了起来。和日耳曼骑士团一样,他也是按照共济会的宗旨组织起来的。(43)因此,该社团仍然是“秘密的”,几乎不产生书面文件。即便会有政治通讯,那也经常是用日耳曼卢恩文字来写的,而这对群体政治而言绝对不是什么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塞博滕道夫还决定让瓦尔法特分部来资助一份名为《卢恩符文》(Runes)的玄学杂志,并继续就摆锤探测术和占星术举办讲座。(44)
这些决定似乎并没有使日耳曼骑士团摆脱一年前波尔和弗里奇一拍两散后对组织造成的不利局面。但是,战争的重创甚至开始让骑士团最顽固、最不关心政治的成员都变得激进起来。到1918年夏,随着德国获胜的前景愈来愈暗淡,塞博滕道夫决定是时候进入政坛了。(45)
修黎社
塞博滕道夫在为日耳曼骑士团的瓦尔法特分部招募成员时,遇到了与他“臭味相投”的瓦尔特·瑙豪斯。瑙豪斯受过雕塑训练,和许多种族论知识分子一样,对“卡巴拉的秘法”以及埃及与印度的宗教信仰相当痴迷。瑙豪斯和他的朋友瓦尔特·戴克已经在1918年新年那天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来讨论这些想法。他们将称之为修黎社。
那时候,瑙豪斯的讨论小组完全不过问政治,和日耳曼骑士团也没任何关系。(46)等到塞博滕道夫任命瑙豪斯为瓦尔法特分部的副招募官之后,这种情况就逐渐发生了改变。到1918年夏,塞博滕道夫和瑙豪斯经常在慕尼黑的四季酒店召开日耳曼骑士团的会议。由于骑士团变得日益政治化,瑙豪斯便提出了一个想法,即用听上去人畜无害的“修黎社”来代替瓦尔法特分部名,为活动打掩护。1918年8月17日,当鲁登道夫在西线的最后一场攻势消退时,塞博滕道夫将日耳曼骑士团的巴伐利亚瓦尔法特分部同瑙豪斯刚开始启动的“修黎社”合并了。(47)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失落的许珀耳玻瑞亚或修黎的文明这一概念来自神智学家对亚特兰蒂斯的想象。然后,他们找到了一种方式,以更具种族化的形式将其融进雅利安智慧学,瑙豪斯和塞博滕道夫所信奉的那些原则都成了他们这个组织的基础。(48)因此,修黎社保留了其雅利安智慧学前身组织的各种行头,宣扬“将玄学-神秘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独一无二地糅合起来”,并承诺在末世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会实现乌托邦式的未来。(49)
还没输掉战争这一事实对于决定该组织的初始轨迹至关重要。在组织成立两个星期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塞博滕道夫仍然花时间对“摆锤”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讲,说那是“射线探测实验或所谓的医学诊断的工具”。新加入修黎社的男性成员表现出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秘术的风格,他们戴上了镶有万字符和两根长矛的青铜胸针,而女性成员得到的是一枚金色的万字符。(50)这里的重点不是塞博滕道夫将学会的时间浪费在入会的胸针或探测棒对健康的好处上。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他也会到德国总理府里到处探测致癌的“死亡射线”,希姆莱则会让他的首席玄学顾问威利古特开发各种各样的种族-秘术符文和徽标。
塞博滕道夫之所以把他的演讲和入会仪式弄得有趣,是因为他想吸引女性成员,这倒是和沙文主义性质极其明显的利本费尔斯的新圣殿骑士团、李斯特的阿尔玛恩骑士团以及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有很大的不同。(51)修黎社关注玄学和边缘科学思想这一点,也和他们比前人更想从事群体政治密不可分。最后,塞博滕道夫在柏林残余的日耳曼骑士团那儿获得了支持,而且他还打进了德国北部,在这方面,弗里奇和他的那些前辈都没他做得好。(52)
从许多方面来看,修黎社的规划和种族-秘术论的先辈是一样的。修黎社员想要一个没有犹太人、共济会员和共产主义者的大德意志,还提议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以帮助将劳动力和资本力量统一起来。(53)从其他方面来看,“社会-民族”因素在修黎社中表现得比日耳曼骑士团更强烈。塞博滕道夫对资本主义的明显敌意和对工人的同情,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他说这是典型的“日耳曼”性质。他想要消灭“犹太”资本主义,以便诚实的德国工人和小生意人能够兴旺起来。这样的论点事实上和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早期版本一脉相承。(54)考虑到修黎社早期成员的资产阶级特性,这种社会与经济改良的规划尤为有趣。(55)
创建修黎社之后,塞博滕道夫及其同事在1918年初秋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首先,塞博滕道夫买下了《慕尼黑观察报》(Munich Observer)(其报头印的是“一份民族和种族政治的独立报纸”)。塞博滕道夫认为该报假装是一份体育报(Sportblatt),这样就不会受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注意,因为“犹太人只会对盈利的体育感兴趣”。(56)不到一年时间,该报便更名为《种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简称VB),成为纳粹党的主要媒体。
其次,《慕尼黑观察报》的首席体育撰稿人、新来的政治编辑卡尔·哈雷尔于1918年10月与修黎社的同道安东·德莱克斯勒合作创立了“政治工作者圈”(Politische Arbeiter-Zirkel)。几星期后,德莱克斯勒建议将该组织从“圈”改为德意志工人党。(57)
塞博滕道夫本人并没有带头提出这一“工人阶级”倡议。但他的同僚们记得,他早已开始在资产阶级的修黎社框架之外接触日耳曼骑士团的年轻成员了。他和哈雷尔都认识到修黎社需要获得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才能获得政治影响力。(58)
塞博滕道夫在坚称修黎社不会过问政治的时候,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特奥多尔·弗里奇战前创办的日耳曼骑士团的玄学活动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塞博滕道夫的声明证明了以玄学为基础的修黎社和以政治为导向的纳粹党之间是有区别的。然而,从之前的内容来看,德意志帝国末期和魏玛政府初期都在严密监控极端主义政治组织,这也就是为什么瑙豪斯和塞博滕道夫会创办修黎社作为掩护,并把《慕尼黑观察报》说成“体育报”。(59)这样他们就可以相对不受监控,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其他右翼团体受到打压的时候,具有政治革命性质的修黎社却能公开在四季酒店集会,吸引来了如此多的泛德意志人士、种族论知识分子以及未来的纳粹分子。(60)
不过,如果不是由于爆发左翼革命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修黎社很有可能仍然只是一个没什么危害性的小型种族论团体。从1918年10月末开始,联合了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左翼政府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工人罢工,士兵哗变。工人提出的要求很快就被新出现的更为激进的独立社会主义者(USDP)和初创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KPD)所接受,他们希望立刻结束战争,废除君主制。这些左翼革命分子在巴伐利亚州最先取得成功,库尔特·艾斯纳的独立社会主义者设法推翻了维特尔斯巴赫君主制,并于1918年11月8日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天正好是宣布停战前一天。
对像塞博滕道夫之类“相信种族末世论”的人来说,艾斯纳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之后的停战、战败和德意志帝国的解体,都是灾难性的。1914年之前在种族-秘术圈内很流行的末世论,如今成了“文化主题和宗教演讲的主题,更不用说德国的战争宣传了”。面对战败和左翼革命,“具有末世论倾向的”德国人,如塞博滕道夫及其种族-民族主义同道,“都坚信他们将面对末日”。(61)有个士兵在魏玛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周是这么看的:
犹太人和……投机分子变得富有,吸取民脂民膏,犹如置身“应许之地”……德国似乎成了迷途的羔羊。除役的前线士兵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家人免受饥饿困顿之苦……各个地区都在罢工、暴乱,德国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世界天翻地覆!……前线士兵和部分体面的民众领导了一场几乎毫无希望的抗击这股风潮的斗争。庆祝议会制就像是在狂欢。出现了差不多35个党派和派别,让人民无所适从。巫师的手法可真高明!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德国人民,踉踉跄跄地朝着各式各样的鬼火走去,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病得不轻。(62)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印象在1914年之前的种族论圈子内挺盛行的。但反对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犹太人的末世种族斗争的想法“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并不怎么明显,直到战争、革命、慕尼黑苏维埃、屠杀人质提供了不断恶化的土壤使其成长”。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紧随而来的左翼革命使“暴力的反犹种族主义”在巴伐利亚“流行开来”之后,慕尼黑才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逻辑中心。(63)
1918年11月8日,也就是艾斯纳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那天,塞博滕道夫召开了修黎社的会议。他说:“昨天我们经历了我们熟悉、珍视的一切的崩塌。取代日耳曼血统的领袖统治我们的是我们的死敌:犹大。这样的混乱状况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猜测。斗争将要来临,那是一种极其痛苦的需要,是危险的时代……只要我还握着铁锤[指的是他主人的锤子],我就会让修黎社参与这场斗争。”(64)
如果说1918年11月8日之前修黎社的政治目标还有怀疑,那它未来的道路现在已经清晰可辨。修黎社再也不会在四季酒店里闲坐,讨论日耳曼符文和探测棒了。为了扭转德国战败的后果,恢复一个种族纯净的德意志帝国,修黎社需要拿起武器反抗“犹大”。(65)他们很快会在一名年轻的奥地利下士的陪同下完成这个使命,这名下士在塞博滕道夫宣战两周之后回到了收养他的慕尼黑家庭,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二、从修黎社到纳粹党
1918年11月底,由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中间派和自由民主党人组成的新中左翼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棘手的局面。他们遭到了极左和极右的极端主义反对派的围攻。摆在他们眼前的还有饿殍遍地,数十万人丧生于肆虐的流感,数百万退役的士兵正在源源不断地返回德国看到自己家园被毁、家人不再、生计无着。魏玛临时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保卫共和国,做出了两个贻害无穷的决定。第一个导致修黎社最终演变成了初始的德意志工人党。第二个促使希特勒在几个月之后和该党取得了联系。
第一个决定是由担任军事事务部部长的社会党人古斯塔夫·诺斯克做出的,他于1919年1月创建了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自由军团招募了许多退役士兵,代表共和国与极左翼势力作战。那些积极加入诺斯克的准军事组织的人,都是狂热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些人还很年轻,没怎么见过打仗。(66)以诺斯克为代表的自由军团中就有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的“斗争联盟”(Kampfbund),后来更名为“自由军团高地”(Freikorps Oberland),它将是未来纳粹的孵化地。(67)
第二个致命的决定是在几个星期后做出的,当时,德国防卫军(Reichswehr)任命希特勒为其所在连队的政府联络员(Vertrauensleute)。防卫军让希特勒“将教育资料传达到部队”,并担任“反布尔什维克”的线人,负责渗透进巴伐利亚的激进党派,这等于是给缺乏政治经验的希特勒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敲门砖。(68)就像塞博滕道夫说的,“即便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尤其是巴伐利亚分部,也能看到许多幡然醒悟的迹象,大家终于渐渐意识到[犹太人]这个非我族类要对眼下‘猪圈’般的混乱景象负最大的责任”。(69)正是在这种政治激进化、军事化、民族主义高涨的环境中,希特勒第一次接触到了德意志工人党。
德意志工人党的兴起
从1918年11月开始,塞博滕道夫及其修黎社同事开始密谋反对巴伐利亚共和国。12月,修黎社制订了绑架艾斯纳的计划。最后以惨败收场。渗入民兵队伍执行反革命任务的计划也失败了。后者导致多名修黎社成员被捕,并在地区议会中遭到公开谴责。(70)到1919年3月,修黎社一直受到监视。为了不被逮捕,塞博滕道夫不得不伪装起来,从自己在巴伐利亚警局的联系人那里接受指示。(71)
有一件事可以让人一窥修黎社采取政治行动的路数。当时,巴伐利亚警局的社会党专员造访修黎社,看看有没有“反犹宣传”。塞博滕道夫在前一天晚上得到同情他们的警员的通知,于是要求所有女性成员次日上午集合,表演“合唱”。警局专员到的时候,受到了修黎社的秘书海拉·冯·韦斯塔普伯爵夫人的迎接,她带领一群女性唱起了民族主义赞歌。照塞博滕道夫的说法,专员大惑不解,问“这是个什么类型的协会?”塞博滕道夫的回答:“这是日耳曼种族精英繁育(Höherzüchtung)协会”。专员感到惊讶,又问:“哦,那你们准备怎么做呢?”塞博滕道夫的回答:“你听得出来,我们都是歌手。”(72)
警局专员对塞博滕道夫的掩饰感到无奈,坚持要对房子进行搜查,看有没有反犹宣传资料。塞博滕道夫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你……逮捕我或我这儿的人……那我的人就会抓犹太人,随便抓来一个,再拖着那人游街,一口咬定那人偷了[基督教的]圣饼。然后,警察大人,你的手头就会有一场大屠杀要处理,这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73)
确实,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塞博滕道夫在《慕尼黑观察报》上连续发表了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的宣传文章,意在破坏艾斯纳的共和国。该报上刊登的几十篇文章都在讲“犹太人艾斯纳”和“以色列在德国的”代表正在如何设法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教育”来摧毁日耳曼种族。不消说,这些文章引起了当地的共和国当局的严密关注,并于1919年4月初对该报下了临时禁令。(74)
塞博滕道夫的关注点并不是建立党组织、夺取权力,而是通过暴力反革命的方式推翻社会主义政府,四年后,希特勒也在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1923年11月9日)中采取了这个模式。在这些阴谋中,最耸人听闻的当属塞博滕道夫在政府取缔《慕尼黑观察报》后没几天策划的针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变。诡异的是,这次的计划和结果与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惊人地相似。塞博滕道夫认为自己能在慕尼黑召集起所有的民族主义力量来反对艾斯纳,于是去接触当地的民兵组织,试图集结一支6000人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夺取慕尼黑,逮捕共产党当局,所有行动都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75)
还没等塞博滕道夫草率计划的政变开始启动,巴伐利亚“红军”就发现了这场阴谋。7名阴谋分子,包括瑙豪斯和韦斯塔普伯爵夫人,都被逮捕并被快速处死。这7名“人质”的被杀导致修黎社的名声在激进民族主义圈内一跃而起,就像啤酒馆暴动也提升了纳粹党的知名度一样。但不同于希特勒把对他的审判当作一个对全国演说的讲台,塞博滕道夫发现自己在种族论圈子里名誉扫地,有人指责他把同谋者的名字泄漏了出去。(76)
在发生了这些战略上的失误,而且错失了机会之后,塞博滕道夫在修黎社和联盟高地(77)内的地位也一落千丈。(78)在把战前日耳曼骑士团的种族-秘术理念转换成群体政治运动方面,他显然不是一个合适人选。资产阶级的靠阴谋起家的修黎社,也不是这项运动的合适载体。
在塞博滕道夫的同道中,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组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政治上与修黎社分庭抗礼的人是卡尔·哈雷尔。正如我们所知,1918年10月,哈雷尔和铁路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共同创建了“政治工作者圈”。该组织的目标是吸引劳动阶级的民族主义分子加入种族论运动。两个月后,即1919年1月5日,德莱克斯勒和哈雷尔、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以及右翼诗人迪特里希·埃克哈特一道组建了德意志工人党。(79)
从一开始,受玄学影响的修黎社和初创的德意志工人党之间就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修黎社和日耳曼骑士团类似,支持者大多都是资产阶级,他们有钱有闲,可以在下午听关于日耳曼符文、占星术、探测棒之类的讲座。而德意志工人党则是由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构成的。他们不会在高档的四季酒店见面,而是会去当地的酒馆里碰面。用政治战略的术语来说,德意志工人党关注的是建立政党,而非煽动革命,所以要比修黎社更务实。(80)
尽管有这些差异,但若是没有修黎社为基础,德意志工人党初期的发展便是无法想象的。德意志工人党的智囊,如哈雷尔、德莱克斯勒、埃克哈特、费德尔、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汉斯·弗兰克以及鲁道夫·赫斯,都是修黎社的成员或同事。哈雷尔还是《慕尼黑观察报》的编辑。修黎社成员弗里德里希·克罗恩将会为希特勒设计纳粹的万字符旗帜。(81)
当然,《慕尼黑观察报》起初是同情德国社会主义党(Deutschsozialistische Partei,简称DSP)的,该党由塞博滕道夫创建于1919年5月,是德意志工人党的替代品。(82)但1919年8月(如上所述),报纸更名为《种族观察报》,将办公室搬到了弗朗茨·埃尔出版社(Franz Eher Verlag),后者是纳粹的官方出版社。(83)不到几个星期(希特勒正好加入该党),《种族观察报》便开始定期报道德意志工人党了。
因此,照理查德·伊文思的说法,“修黎社将被证明是后来的许多纳粹活动家在投靠希特勒和他发起的运动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补给站”。(84)正如塞博滕道夫略加美化的回忆所说,“除了修黎社自身之外,未来元首的武器库还包括卡尔·哈雷尔兄弟在修黎社内部创建的德国工人联合会(Deutsche Arbeiter Verein,DAV),由汉斯·格奥尔格·格拉辛格领导的德国社会主义党,其机关报就是《种族观察报》”。(85)若是没有塞博滕道夫的修黎社,没有哈雷尔的“政治工作者圈”,没有他们为推广其世界观而买下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报纸,纳粹党几乎肯定诞生不了。(86)
德意志工人党还继承了修黎社狂热的反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对民主的恨之入骨以及推翻共和国的决心。加入德意志工人党的都是“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和负伤的老兵”,这些人对“平民社会不屑一顾,认为那里的人活在流于表面的琐事中,体会不了士兵那种近乎宗教般的超越和永恒的感受”。(87)在这种种族-秘术宇宙学之中出现了“一个幻想出来的救世主形象……[他]就是人们心理上的一个统摄之物,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性格盔甲都结合在了一起”。(88)在出现了许多虚假的弥赛亚——从李斯特到弗里奇再到塞博滕道夫——之后,德意志工人党现在成了人们的“救世主”。
希特勒掌权
德意志工人党和修黎社之间并没有一刀两断。受时时变化的政治环境左右,该党从修黎社演化出来的过程,一如修黎社之前从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演化出来,都是逐渐的。(89)“专业”占星师、摆锤探测师塞博滕道夫也许已经出局了。但业余占星师、摆锤探测师威廉·古特贝莱特如今入了局。在慕尼黑当医生的古特贝莱特持有《种族观察报》8.5%的股份,也是德意志工人党最重要的金主之一。1919年9月,希特勒参加第一届德意志工人党会议的时候,他也在场。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古特贝莱特在纳粹党内仍旧活跃,受纳粹情报头子瓦尔特·舍伦贝格的邀请,接受了他关于战时情报部门使用占星术和预测术是否可行的咨询。(90)
问题是,瑙豪斯和塞博滕道夫对雅利安-日耳曼宗教、神秘学以及边缘科学的兴趣持续的时间,远比修黎社和德意志工人党联合的时间要长。(91)况且,几乎所有的德意志工人党早期领导人,如德莱克斯勒、哈雷尔、埃克哈特、赫斯、罗森贝格和弗兰克,都表现出了对雅利安-日耳曼宗教、神秘主义和/或边缘科学的兴趣。(92)塞博滕道夫被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德意志工人党对修黎社的超自然倾向感到难堪,而是他在从政方面的业余行为和他1919年5月决定创建与之抗衡的德国社会主义党导致的(后者事实上有一个相同的规划,所以几年后与希特勒的纳粹党合并了)。(93)
但眼下,在几十个种族论组织里,德意志工人党只是一个小党。它还需要一样东西才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那就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1919年9月12日,埃克哈特原定要在德意志工人党的会议上讲话。但他病了,在最后一刻由修黎社的另一成员,也是德意志工人党的共同创建者戈特弗里德·费德尔顶替上阵,费德尔喜欢用生动的反犹言论抨击“拜金主义”和“利益奴役”(94),这让他在种族论的圈子里极受欢迎。
碰巧,当时希特勒决定以防卫军督察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他对费德尔的演讲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等到另一名德意志工人党党员要求让巴伐利亚脱离德国的时候,他差点离场。作为一个年轻的一辈子都在幻想如何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对这话火冒三丈。他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讲话,支持泛德意志种族的统一,他的这次讲话很受欢迎。德莱克斯勒对希特勒的即兴演讲印象深刻,向他提供了一些政治读物,邀请他入党。(95)
没过多久,《种族观察报》首次对德意志工人党的这次会议作了报道,里面还提到了一位“希特勒先生”发表了攻击犹太人的讲话。到1920年代初,《种族观察报》明显日益关注起了新创建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及其初露头角的新星阿道夫·希特勒。(96)
考虑到希特勒对“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的鄙视态度,人们自然会以为纳粹党接下来的变化肯定和清除党内的玄学因素有关。然而,希特勒掌权后党内出现的冲突相对来说和玄学或异教几乎没什么关系。它们和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看法有关,即德意志工人党吸引的都是有精英背景的人,喜欢讨论深奥晦涩的问题,要夺权会很困难。(97)
德意志工人党从修黎社分离出来之后,秘术讨论团体和创建群体政治的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成了种族论运动中的痼疾。(98)这是威廉时代的反犹党派失败的内在原因,也是阿尔玛恩、李斯特学会、日耳曼骑士团/铁锤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的原因。塞博滕道夫在决定创建一个政治组织来接替日耳曼骑士团的瓦尔法特分部时,就说到过其中的紧张关系。无论是德莱克斯勒、哈雷尔,还是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只能唉声叹气,却无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而正是各种族论群体之间的小内讧阻止了德国人团结起来反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99)
这种政治和战略上的紧张关系,在《种族观察报》的字里行间及编辑会议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整八个月时间,该报在哈雷尔的编辑下,试图避免一面倒地支持德意志工人党压过德国社会主义党。(100)但在1920年春,希特勒逼走了哈雷尔,坚决要求该报将注意力放在纳粹党身上。(101)1920年底,希特勒寻求买下《种族观察报》,使之成为纳粹党的专用报纸。希特勒的朋友、准军事组织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本人就是占星术爱好者。罗姆坚信希特勒就是做这事的合适人选,便鼓励手下的指挥官里特·冯·艾普买下该报,使之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工具。(102)
埃克哈特和罗森贝格两人都是修黎社成员,都喜欢钻研秘术,他们接管了《种族观察报》以及该党的宣传事务。(103)从相对务实的哈雷尔转到异教的半吊子爱好者罗森贝格及种族神秘论者埃克哈特的手上,并不能认为是和超自然思维的分道扬镳。这是德意志工人党持续政治演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希特勒在更广泛的种族论运动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104)
到1922年,纳粹党已经将塞博滕道夫的德国社会主义党和修黎社底下的准军事组织“联盟高地”吸收了进来。(105)一同吸收进来的还有许多“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其中就有威廉时代反犹主义的领导人恩斯特·冯·雷文特洛夫和特奥多尔·弗里奇,前者会在1933年之后帮忙领导德意志异教信仰运动,后者犹如偶像,将在第三帝国的无数党校和街道的名称中永垂不朽。(106)放弃德国社会主义党,投身纳粹党的还有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他声称自己拥有罕见的“力量”,能从很远的地方嗅出谁是犹太人。纳粹党还吸引了阿尔图尔·丁特尔的加入,他写过一本极端反犹、充满各种迷信的奇幻小说《破坏血统之罪》(The Sin Against the Blood,1917),卖出了好几十万本。(107)除了这些有名的种族论领导人之外,还必须提到异教论者雨果·克里斯托弗·海因里希·迈耶、恩斯特·亨克尔、恩斯特·弗莱黑尔·冯·沃尔措根,以及约翰·丁菲尔德、弗朗茨·施伦哈默-海姆达尔、赫尔曼·威尔特,弗伦佐夫·施米特等著名的雅利安智慧学家。(108)
鉴于种族-秘术论者的稳定增长,《种族观察报》在哈雷尔离开之后继续发表由雅利安-日耳曼异教论者和雅利安智慧学者写的特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文章充斥着诸如“低等人种”、“圣地”(Halgadome)、“沃坦或阿尔玛恩教会”、“种族灵魂”以及“雅利安光明宗教”之类的概念。(109)1920年12月1日,纳粹党与人共同出资举办了一个异教冬至日庆祝活动,“公开宣称这和圭多·冯·李斯特的种族论相关”。据《种族观察报》报道,共和国早年的这场可怕的危机在“埃达和阿尔玛恩的教诲”中已经“预言过了”。这篇报道的结论是,“雅利安人总有一天会过上更幸福的日子,在一片崭新的埃达之地”。(110)1921年夏,纳粹党又资助了一场夏至日庆典,以此向“太阳神巴尔杜”和“太阳英雄和齐格弗里德神的儿子”致意。(111)1922年,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纳粹异教者的圣诞节庆典(Yule festival),罗森贝格还写了文章以示赞许。(112)
正如塞缪尔·科纳(Samuel Koehne)提醒我们的那样,1923年11月9日啤酒馆暴动之前的纳粹战斗口号“来自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概念,得到了特奥多尔·弗里奇的推广”。该党的出版物说,如果纳粹革命成功,“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插曲,塔木德的精神和唯物主义的荒唐杂交的产物”,将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世界观只要稍微一动,黑暗统治下铸造的锁链就会轰然断裂”。文章继续写道:“欧马兹特(113)和阿里曼之间,即光明神和黑暗神之间的永恒斗争已再次开始,并再次以太阳的胜利告终,而太阳的象征就是古代雅利安人获救的标志:万字符!”(114)1923年11月,政变自然是以惨败收场。但许多党员的超自然情感和期望却是清晰可见的。
希特勒鄙视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后来任命施特莱彻担任下萨克森大区长官(Gauleiter),任命丁特尔担任图林根大区长官。(115)施特莱彻将继续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直到战争结束。丁特尔则在1928年被开除出党。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不愿遵从希特勒的“领导人原则”(Führerprinzip),包括寻求与独立政党联盟,并宣传他特定的种族-秘术信仰。(116)
希特勒对独立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不怎么容忍,这点和弗里奇、塞博滕道夫以及其他种族-秘术论者没有区别。所有的种族论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将他们的运动统一到某个领导人麾下。(117)正如塞博滕道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希特勒将种族运动纳入纳粹党内的做法值得大加赞赏。塞博滕道夫认为:“德国人需要一个会告诫他们,让他们紧盯目标而非路径的元首。”(118)该党并没有驱逐忠心耿耿的种族-秘术论者,而是说服他们接受了一个等级分明、全国一体的以希特勒为核心的纳粹党。(119)
在1925年“重建”该党之后几年,戈培尔承认,纳粹党“经常受到指责,说其失去了作为一场运动的特质……说种族论运动的思想体系庞大、宽泛、变动不居,还说该党削足适履,搞出各种强制性的一刀切”。接着,他说道,但是“种族论运动在这件事情上搁浅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种族论运动的核心,别人凡是不同意其观点的,都会被说成背叛了这一事业。这就是战前种族论运动的情况……如果种族论组织者明白如何组织一场伟大的运动(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那么种族论思想就会获胜,马克思主义赢不了。”(120)戈培尔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做出的同修黎社决裂的决定,与其玄学以及边缘科学观没什么关系,而与其毫无章法的政治进程有关。(121)
在纳粹党和修黎社决裂几十年后,纳粹的“老战士”仍然会哀叹希特勒对“以浪漫主义为底色的种族论想法”缺乏感情。(122)但是,希特勒之所以如此摒弃种族-秘术论,是因为“他是以一场‘运动’的概念来看待该党的,这就要抛弃以前修黎社之类团体搞阴谋的做法”。(123)“1920年到1923年是纳粹党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其间,它把自己从一个小而隐蔽的组织(阿道夫·希特勒称之为‘茶会’[tea club])变成了一场革命运动”。尽管抛弃了“茶会”性质的政治进路,但纳粹党员仍然“和种族论运动的根源密不可分”。(124)
三、纳粹的超自然想象
魏玛共和国的最初四年,是纳粹党的形成期,也是一个政治恐怖猖獗、时刻疑神疑鬼、革命泛滥的时期。从1919年初的左翼起义潮,到1920年3月右翼的卡普暴动(Kapp Putsch),以及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准军事组织的激进分子在街上互相攻击,暗杀政客,发动暴力的反政府行动。德国各地的家庭不得不吃力地面对数百万的死伤者。随后,作为对魏玛政府拖欠赔偿的行为的回应,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地带鲁尔河谷。1923年1月,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数百万德国人陷入贫困。
不难看出,这种右翼团体的暴力和危机都有超自然的影子。比如,萨克森的共产党员、革命分子马克斯·赫尔茨在1919年和1920年领导了两次暴动,后来为了躲避抓捕,穿越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消失得无影无踪。赫尔茨被说成“隐身人……邪恶的妖怪”,而他的故事则继续在萨克森他的种族论和右翼的对头中流传。甚至当地警方说赫尔茨的行为如超人,“千变万化”,可见超自然思维在构建右翼政治观点时有多么重要。(125)
萨克森是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总部所在地,当地人对赫尔茨的故事的普遍反应,仅仅是“在通货膨胀和随后的局势动荡甚嚣尘上之时”社会政治潮流和超自然主题广泛传播的一个例子。(126)就像我们所见的那样,这些因素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德国和奥地利全境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战争和革命刚一结束,它们就获得了受欢迎的势头,右翼对赫尔茨的无端恐惧也强化了这一趋势。(127)纳粹党正是从这种“种族论的子文化”中脱颖而出,在这种子文化中,“无论是异教,还是秘术都不会遭到排斥”。(128)
正如德国记者康拉德·海登所发现的,民族社会主义合并了“各种类型的政治理论的元素,从最反动的君主制到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从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到最不近人情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应有尽有”。(129)纳粹主义一以贯之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拒斥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客观性或因果关系概念……在那样的世界中,因果关系独立于超验力量”。(130)和修黎社决裂之后,纳粹党发展了一种可塑的话语体系,它吸收了战前的神秘主义、异教以及边缘科学的因素,在意识形态上更兼收并蓄,政治上也更平易近人,而我把这称为纳粹的超自然想象。
早期纳粹党的超自然思想
1923年,迪特里希·埃克哈特在临终之时,据说说了这样的话:希特勒“只管跳舞,我才是定调子的人”。(131)不管此话是否杜撰,反正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毕竟,埃克哈特是早期对希特勒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也是未来的纳粹领导人的榜样。埃克哈特在他的杂志《优秀德国人》(Auf Gut Deutsch)中,将知识和实用并重的政治手段与对北欧民间传说及日耳曼宗教神秘根源的真诚信仰结合在了一起。(132)在名为《米德加德蛇》(133)和《犹太人君临万物》(Jewry über alles)这样的文章中,埃克哈特宣扬了雅利安智慧学的原则以及“向来在幕后操纵的犹太人”是“吸血种姓”的奇谈怪论,而希特勒既是他的缪斯,也是他的助手。(134)
埃克哈特对宗教和神话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看法深信不疑。(135)在早期和希特勒的谈话中,他经常提到摩尼教、善恶二元对立、上帝和(犹太)魔鬼,这是一种准基督教和准异教诺斯替主义合体的雅利安智慧学,也是后来纳粹的宗教进路。(136)作为对拉加德和张伯伦的呼应,埃卡特认为,高等种族“印欧人”已经被主流基督教里的“犹太人的沙漠精魂”(137)所腐蚀。(138)和基督教“截然对立”的是“印度的智慧”,它超越了自然,认为万物和“世界灵魂”息息相通。(139)在此,埃卡特给希特勒上了一堂有关印度-雅利安神秘主义和种族-秘术宗教的速成课,后者同李斯特和兰茨的阿尔玛恩主义并无区别。(140)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帮忙将埃克哈特提出的“日耳曼精神和种族优越性的种族救赎论”,与“国际上邪恶的犹太人想用卑劣的手段夺取全世界的统治权的阴谋-末世……论”综合了起来。(141)罗森贝格在他最重要的作品《20世纪的迷思》(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将边缘科学的种族主义和印度-日耳曼异教的混合体引入了纳粹的超自然想象之中。(142)作为对雅利安智慧学家和雅利安-日耳曼宗教狂热分子的说法的呼应,罗森贝格声称印度西北部和波斯的古雅利安人创建了所有伟大的文明,后来由于和低等种族混在一起,受到犹太-基督教的恶劣影响,才渐趋衰落。(143)
照罗森贝格的说法,20世纪的新神话乃是“血的迷思,它在万字符的标志下,将世界革命释放了出来。这是种族灵魂的觉醒”。(144)罗森贝格热衷于将“种族灵魂”这一生物神秘论概念作为世界历史的发动机。但他也很谨慎,没有给任何特定宗教的教义以特别优待。(145)为引起德国人对神话的渴望,罗森贝格认为纳粹党必须吸收各种类型的雅利安-日耳曼宗教和种族-秘术传统。(146)起到救赎作用的“血的神话”和“种族灵魂的觉醒”理念,再次在战后的种族论环境中流行开来。(147)但是,没有哪个政党再认真一点对待这一观点,即阵亡士兵们的“神圣牺牲”或者为了挽回他们的死亡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反映了纳粹党的“一种宇宙论冲动……[想要]以崭新的方式重塑世界”。(148)
纳粹的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写道,透过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生者和死者“找到了通往永恒的道路”。(149)纳粹的同路人们出版了不少书,“其中有700多幅‘光荣的神龛[Ehrenhaine]’的插图”。这些死者“并没有真的死去……他们会在晚上爬出坟墓,造访我们的梦境”。(150)纳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接纳了“200万死去的德国人,他们进入了种族灵魂的英灵神殿(151)”。纳粹声称自己代表不死的战士,相比传统保守派,纳粹更注重神秘的“种族灵魂”,而活着的和死去的士兵都有这种“种族灵魂”。(152)
纳粹也会从消极的方面来乞灵于生者和死者。希特勒、希姆莱、罗森贝格以及纳粹的其他早期领导人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经常会提到怪物(鬼怪、恶魔、吸血鬼、木乃伊及其他超自然的比喻)。比如,在攻击共产主义时,说“肆虐各国的这场瘟疫,其始作俑者肯定是不折不扣的恶魔;因为只有在怪物而不是人的脑子里,一个组织的规划才具有形式和意义”。希特勒在其他地方也讲过,一个人“不能用魔王来驱赶魔鬼”。与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作斗争,也就意味着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避开资产阶级政党会议“一如魔鬼[避开]圣水”。(153)费德尔指责魏玛共和国把德国人变成了“僵尸”。(154)至于罗森贝格、希姆莱和希特勒,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犹太人同恶魔和吸血鬼联系在一起。(155)这让我们想起了纳粹对“通过血统代代相传的变革力量”的不可思议的痴迷。(156)对纳粹来说,德国土地“浸透了烈士的英雄之血,令人难以忘却”,而这烈士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者,还有早期“斗争”中的党员。正如一名纳粹诗人所说,德国的土地仍然“涌动着死者的鲜血”。(157)我们可以在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迷思》中见到这种以积极姿态从生物神秘论的角度对血的关注。相反,在阿尔图尔·丁特尔的《破坏血统之罪》一书中,从消极角度对犹太人的腐败堕落进行了超自然的幻想。
我们也别急着把这些超自然比喻当作纯粹的修辞手法,而是必须回顾一下纳粹高层痴迷于神秘学和边缘科学学说到了何种程度。出生于埃及,在埃及受了部分教育的鲁道夫·赫斯青少年时返回德国,一战期间志愿参军。战后,希特勒的这位未来的副元首去了慕尼黑,在卡尔·豪斯霍费尔的门下学习历史和地缘政治,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过豪斯霍费尔地缘政治学中的边缘科学进路。(158)受自己参军打仗的经历激发,再加上德国战败、革命爆发,赫斯便于1919年初加入了修黎社。(159)尽管赫斯后来因为投奔希特勒而与修黎社决裂,但他从未放弃过对种族-秘术论的兴趣。(160)他也继续资助占星术、人智学、佛教、印度教和西藏神秘主义的研究,甚至在1941年5月进行那趟臭名远扬的英国之行前(161)还咨询过占星师。(162)
出生于慕尼黑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接受培训,在1922年当上了一家化学工厂的农业助理,他就是在那年遇到了冲锋队的领导人恩斯特·罗姆。1923年8月,希姆莱加入了纳粹党,快速蹿升,成了希特勒核心圈子的一员。(163)年轻时,希姆莱就大量阅读了特奥多尔·弗里奇的著作,对于此人,他说:“我突然开始明白一些小时候没法理解的东西,比如这么多圣经故事有什么意义……宗教的可怕灾难和它造成的危险让我们窒息”。(164)当然,所谓“宗教”,希姆莱指的就是基督教,照弗里奇和其他雅利安智慧学家的说法,基督教试图取代《埃达》和《尼伯龙根之歌》(165),“雷神、芙蕾雅、洛基(166)以及其他北欧神灵”。(167)希姆莱还对东方宗教和秘术投入了大量精力,除了随身携带《埃达》之外,他还会带上佛教经典《吠陀》和《薄伽梵歌》。(168)
除了北欧异教和东方宗教之外,希姆莱还广泛阅读了边缘科学的著作,在他看来,边缘科学是以严肃的“学术”方法在研究玄学现象;比如,一本有关“占星术、催眠术、招魂术、心灵感应术”的著作和几本有关“摆锤探测术”的专著。他还研究“灵魂的轮回”,并相信“和亡者的灵魂进行交流是可能的”。(169)希姆莱对共济会和秘密骑士会的历史很着迷,并以此发展出了党卫军。(170)到1923年,希姆莱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洽的种族观,其中……既有玄学信仰也有对日耳曼的热情;有了这些因素,便生成了一种混合了政治乌托邦、浪漫的世界梦想、替代宗教的意识形态”。(171)
希姆莱和其他纳粹分子的超自然想象也包括了对狼人的痴迷。按照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一名副手的说法,法国或东方斯拉夫国家的狼人都和“巫术及魔鬼的施法”有关,与此不同,狼人在德国的异教传统中很大程度上都是正面角色。(172)罗森贝格的助手认为,即便在如今的德国,也存在许多“好的狼人”,会陪在威斯特法伦的“夜行者”左右,保护农民不受东普鲁士的“林中狼”的侵害。(173)除了日耳曼民间传说得到复兴之外,赫尔曼·伦斯的复仇故事《狼人》也让“这个可怕的词[狼人]在德国复活”,两次大战期间,这本书和丁特尔的《破坏血统之罪》同样畅销。(174)
受狼人启发的复仇故事,后来在弗利茨·克洛普的准军事组织“狼人组织”(Organisation Wehrwolf)中得到了最具体的政治和知识层面的体现。1923年初创立的“狼人组织”是为了因应法国占领鲁尔地区而设,它将自己视为“可怕的……狼群,在黑夜里狩猎牺牲品;而这正是这些反革命阴谋家所做的”。(175)就像“狼人组织”的一本小册子所说:“我们为什么战斗?因为北欧的鲜血在我们体内流淌,不战斗,无活路。”这本小册子还说:“当代教会已无法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只有“我们这个种族联盟运动,我们这些狼人,才能澄清未来的信仰并塑造这样的信仰”。(176)
“狼人组织”对边缘科学的激进理论和种族论信仰投入了大量精力,这种投入也因为克洛普对J.W.豪尔的日耳曼信仰运动、对“亚特兰蒂斯”学者和未来的党卫军领导人赫尔曼·威尔特和卢恩文字研究者齐格弗里德·库默的雅利安智慧学著作感兴趣而大大加强了。(177)“狼人组织”还和国防军元帅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具有秘术论倾向的坦能堡协会(Tannenberg Association)以及受修黎社启发的联盟高地建立了联系。克洛普甚至还为17岁以下的青少年设立了青年狼人组织(Jung Wehrwolf),徽标是“骷髅头”(后来被党卫军挪用)。(178)
1924年7月,希姆莱写道:“狼人站在种族主义的土地上。它需要每一位成员或新加入者无条件地投身爱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日耳曼性之中”。(179)由于“狼人组织”不断受到魏玛警方的监视(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被捕,纳粹党承受不起这种监视),希姆莱不敢加入克洛普的组织。(180)但未来的冲锋队头目和柏林的纳粹警察总长沃尔夫·格拉夫·冯·赫尔多夫成了“狼人组织”的首领。(181)赫尔多夫和恩斯特·罗姆都沉浸于种族-秘术学说之中,在“爱国主义准军事协会”中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纳粹领导人,他们只不过是其中一员而已,但最终却吸引了数千“狼人”和其他种族论团体,组建了褐衫队(Brownshirts),即冲锋队。(182)
早期的纳粹领导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阿塔曼纳运动中找到了他们对种族和空间进行超自然思考的额外灵感。(183)阿塔曼纳联盟是奥古斯特·格奥尔格·坎斯特勒创立于1924年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组织,坎斯特勒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德裔移民,后来成了纳粹。阿塔曼纳联盟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东欧夺取“生存空间”,创建“东方定居点”,以恢复日耳曼的种族和领土优势。(184)1926年,阿塔曼纳联盟差不多有600名成员在60个农场干活,大多数农场都在德国东部。4年后,已有近2000名成员在300个农场干活。(185)
除了向东方扩张这一实际目标之外,阿塔曼纳联盟还宣扬“秘术上的先入之见”以及“雅利安智慧学和神智学想法”,塑造了许多纳粹分子的种族观和空间观。(186)阿塔曼纳联盟还对生活改良运动做出回应,试图创建“一个有种族意识的由年轻人构成的共同体”,这些人“想摆脱不健康的、毁灭性的、肤浅的城市生活……[并]回归健康、艰苦却自然的乡村生活。他们戒酒、戒尼古丁,凡无益于心灵和身体健康发展的东西,一概都戒”。(187)他们会在晚上举行庆典,“大肆杀人放火”,使用古老的日耳曼卢恩符文,并带着万字符出来游行,视之为“象征太阳”的神圣符号,是“日耳曼神性、血统纯洁性和精神层面象征的日耳曼神圣符号”。(188)
阿塔曼纳联盟将“反斯拉夫主义、反城市主义”和“反波兰仇外行动”和极端的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呈现出负面意味。(189)和雅利安智慧学家一样,阿塔曼纳联盟还对种族混血发出警告,说“非北欧血统再次现身,企图攻击北欧人”。(190)在这种种族论宇宙学中,犹太人成了“腐败城市的象征”、吸血寄生虫,犹如肿瘤一样寄生在种族的躯体上,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将之去除。(191)
阿塔曼纳联盟为“民族社会主义信仰”的基本原则铺平了道路,也为在东方建立移民定居点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920年代中期,希姆莱加入了阿塔曼纳联盟,成为巴伐利亚分部的领袖(Gauführer),他就是在那儿遇到了未来的一些纳粹领导人,如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党卫军官员沃尔弗拉姆·西弗斯、纳粹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冯·施拉赫(此人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仪式上使用了阿塔曼纳符文),还有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被希姆莱任命为奥斯威辛的负责人。(193)也正是通过阿塔曼纳联盟,希姆莱见到了瓦尔特·达雷,此人后来担任党卫军种族和安置办公室(RuSHA)负责人。(194)
当时还年轻的达雷,整天泡在奥-德超自然圈子里,津津有味地阅读朗贝恩的《作为教育者的伦勃朗》和鲁道夫·施泰纳的人智学著作。(195)达雷也对李斯特和利本费尔斯宣扬的东方宗教及伊尔明信仰(196)(阿尔玛恩宗教)很感兴趣。(197)照达雷的说法,北欧日耳曼人不得不抛弃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无法“分辨血统和种族……[只有]很少被记录下来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从智慧变成信仰,将原始信仰保存在觉醒的大地母亲那里”。(198)
在两次大战期间出版的一系列书籍和小册子中,达雷将血统和土地的神秘观念提升到了准宗教的地步。(199)照一个纳粹诗人的说法,正是通过达雷,德国领土又开始被重新视为“神秘的‘民族’……生者和死者的大地母亲”,它是“永恒多育的子宫”,“汲取着无尽的源泉哺育[德国]”。(200)诗中写道:“迷惘,从你里面被连根拔起,我茫然四顾,我要回家,哦,母亲,带我回去/古老的血脉被唤醒了……从大地的心上撕下的泥块中/鲜血横流,滚烫的,血沫里带着果实和功绩……飘扬着红色,新种子的旗帜……崭新的帝国于是从鲜血和土里升起。”(201)达雷坚称,透过神秘的血和土的神秘学,北欧思想成了“黑暗纪元的一道光”,那是对“保存和承续种族的神圣法则”的认可。(202)
随着纳粹党将各种种族论的团体汇聚到一面旗帜之下,其力量逐渐壮大,修黎社、“狼人组织”、阿塔曼纳联盟的大多数成员都被吸收入党。(203)然而在魏玛共和国早期至中期,这些种族-秘术团体还只是政治和文化的试验场,取悦种族乌托邦和殖民东方的幻想,并帮助塑造纳粹的超自然想象。(204)
希特勒的超自然想象
比起同辈,希特勒对传统的神秘学学说的兴趣也许没那么大,但他对超自然的关注却是实实在在的。(205)1908年希特勒离开家乡林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已经相当欣赏北欧神话和日耳曼民间传说。(206)在维也纳,他看了瓦格纳歌剧的几十场演出,并试图根据北欧神话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元素自己创作歌剧。(207)希特勒还接触了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和卡尔·吕格的边缘科学种族学说及煽动性的反犹演说,卡尔·吕格是圭多·冯·李斯特学会的成员,希特勒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208)
不管希特勒是否读过兰茨·冯·利本费尔斯的杂志《奥斯塔拉》,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段时间看过雅利安智慧学方面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不知何故挑上了“兰茨·冯·利本费尔斯的《奥斯塔拉》里描述的摩尼教连环画中金发人和黑发人、英雄和替补、雅利安人和低等人种之间的二元论”。(209)整个1920年代,希特勒还对朗贝恩的《作为教育者的伦勃朗》和丁特尔的畅销书《破坏血统之罪》持正面看法。(210)
这些超自然方面的口味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图书室,1945年被美军101空降师在一座盐矿里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政治理论或哲学方面的书籍。(211)不过,希特勒确实拥有许多“关于流行医学、神奇疗法、烹饪、素食主义和特殊饮食”的书籍,还有几十本“有关沃坦和日耳曼神话中的神祇……魔法符号和玄学”的书。其中有恩斯特·谢尔特的《魔法》(Magic)和兰茨·冯·利本费尔斯的《日耳曼圣歌集:雅利安智慧学-种族神秘论和反犹主义的祈祷书》(The Book of German Psalms:The Prayerbook of Ariosophic-Racial Mystics and Anti-Semities)。(212)
希特勒从政后并不讳言这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他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提到了他对“如圭多·冯·李斯特和特奥多尔·弗里奇之类的种族论作家”的信赖。他先从李斯特说起,认为“在冰河时代,雅利安人在和自然界的艰苦斗争中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力量,其发展与生活在物资富足的世界里的其他种族截然不同……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种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太阳这个象征。所有的崇拜都是以光为基础,你可以找到这种象征,生火的方式,奎尔人,十字架。不仅可以在这儿[德国]见到这种万字符样子的十字架,也能在印度和日本的寺庙见到这种刻在柱子上的[符号]。而这就是雅利安文化[Kultur]曾经造出来给社会共享的万字符”。(213)希特勒曾告诉赫尔曼·劳施宁,“旧日的信仰将会通过骑士城堡再次散发荣光”,(214)雅利安年轻人将会在城堡里学习各种“宏大的、使自己神人合一”的原则。(215)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在描述自己的种族和历史理论时,再次呼应了雅利安智慧学。他说:“这片大陆上的人类文化和文明与雅利安人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雅利安人绝迹或衰落,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的黑暗帷幕就会罩住这个星球。”(216)种族混血会导致“人不像人猿不像猿的怪物”,希特勒如此断言,照搬了兰茨的“神学动物学”,还说“作为一切恶的象征的人格化的魔鬼”就会长成“犹太人的样子”。(217)“雅利安人放弃了自己血统的纯洁性,因此也就丧失了在他为自己建造的天堂逗留的机会”,他在其他地方如此说过。“他被淹没在种族混血之中,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能力,到最后,不仅精神上,而且身体上,都开始更像低等的土著人而不是自己的祖先……血统混合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水平的降低乃是旧日文化消亡的唯一因素。”(218)
希特勒后来把《我的奋斗》中的这样一些话删除了,以此表明自己并没有受到“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和“所谓的宗教改革人士”的影响。(219)然而,尽管作了这样的自我审查,希特勒也并没有摒弃“这些团体的神秘论民族主义”。(220)《我的奋斗》出版六年后,他的意识形态仍然没有抛弃边缘科学的神秘论基础。1931年,希特勒这么解释道:“我们不会仅仅从艺术或军事标准,甚至也不会从纯粹的科学标准来作判断。我们是通过人前进所需的精神能量来作判断的……我打算建立一个千年帝国,任何在这场战斗中支持我的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我会说那就是神圣)造物,是我的战友。在这决定性时刻,决定性因素不是身体力量之比,而是精神力量之比。”(221)
为了缓和自己公开援引种族-秘术论的做法,希特勒表达了一种愿望,想要将自己草创的运动和“一事无成的、无能的、往往还对日耳曼无比狂热的、认为古代什么都好的老右派”划清界限。(222)希特勒想打造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超自然想象,远超“当时的学院派种族-秘术论”。(223)民族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是更伟大更普世的东西;是一种受多种影响的思维方式,包括印度-雅利安宗教和神话。(224)“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如此大力强调北欧血统的优越性,确切地说是希望日耳曼人重生,却如此大量关注东方和亚洲的魔法,这相当难理解。但不管怎么说,事实就是如此。”(225)
确实,关于神秘主义——魔法——的核心因素方面,希特勒的想法很明晰。只是到近期,我们才发现他很有可能读过一本关于练习“魔法”的书,那是超心理学家恩斯特·谢尔特1923年出版的神秘学大作《魔法:历史、理论和实践》。(226)希特勒在这本书中的许多地方都划了线,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对边缘科学、神秘主义以及更普遍的“魔法思维”的看法有了独到的见解。在第一节中,希特勒在这句话下方划了线:“所有天才”都有能力驾驭“准宇宙(魔鬼)力量”,这种力量“会和许多悲惨和不幸结合在一起,但总是会带来最深刻的结果”。(227)
希特勒同意谢尔特的观点,即现代欧洲人满心都是“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缺乏对世界“更深层意义的感知”。(228)照希特勒的说法(借谢尔特之口),用一神论宗教取代旧的魔法传统所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建立了一种绝对的‘道德’,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的人”。幸好,前基督教时期摒弃了普世道德论而支持“民间‘习俗’”和“部落神灵的意志”所赋予的“以生活来统领一切”的观点。神或神在地上的载体可以以“完全专制”的方式来进行统治,“按照自己的意愿下达命令”,并要求“流血和毁灭”。以魔法为基础的异教道德“和‘人性’、‘兄弟情谊’,或抽象的‘善’无关”。谢尔特在被希特勒划出来的那个段落中还写道,“唯一相关的‘生活统领一切’的观点”“仅限于个别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会把这个视为完全自然的事情”。(229)
希特勒在“理论”方面举出的段落,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超自然想象。谢尔特解释说:“浮现出的想象(潜意识)”也许会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要么表现为幻觉,要么表现为现实”。(230)现代人“抵制这些见解……大肆宣扬什么‘实证论’”,并“把所有的‘想象’”斥为幻觉。但希特勒指出,他没意识到“他引以为傲的实证论世界观最终也取决于想象”,因为“每一种世界观都是基于想象力的基础-合成方法之上的”。(231)希特勒强调,“想象力最丰富的人是世界的主人,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造现实,而不会成为一个不扎实不定型的实证论的奴隶”。可是,“纯粹的实证论者类似于熵,会使宇宙能量完全贬值,而富有想象力者,魔法师,才是熵的真正焦点,才是世界焕然一新、世界重塑的、生命新生的真正焦点”。(232)
在划出了有关宇宙力量的操纵、人内心的“神”或“魔鬼”操纵的段落之后,希特勒又注意到谢尔特的话,即“每个恶魔-魔法世界都朝着以伟大的个人为中心的方向而去,而这些个人是产生基本的创造性概念的源泉。每个魔法师都被一个准宇宙能量的力场所包围”。被魔法师“感染”的个体此后就会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自己的“族群”,并“创造出一个以想象为框架的生活综合体,称为‘文化’”。(233)希特勒认为,为了利用这些“准宇宙能量”,“伟大的个体”就需要为种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做出牺牲。(234)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希特勒似乎对特莱特尔有关“实践”的段落特别感兴趣,即运用人自身的准宇宙能量、人自身的“魔法”来操控其他人。(235)
我并不是想要表明希特勒和希姆莱、赫斯或达雷一样,对神秘学和边缘科学思维方面也是无条件地投入。希特勒对超自然的兴趣少了教条主义色彩,多了功利性,这源于“他坚信人和宇宙存在某种神奇的联系”。希特勒之所以研究神秘学学说,是因为它们为他的政治宣传和对公众的操控提供了素材。(236)
比如,和许多纳粹分子不同,希特勒对共济会的危害性相对来说不怎么感兴趣。但照劳施宁的说法,他倒是确实欣赏共济会的“秘术学说”,认为它们“通过符号和按入会等级不同而设定的神秘仪式来进行传授。这个等级制组织和通过象征性仪式来入会的做法,不会烧脑,却又可以通过魔法和崇拜符号来激发想象力”。(237)不管希特勒对“胡思乱想的种族论学者”持什么样的保留态度,他都认识到超自然想象确实拥有吸引他的党内同僚和普通德国人的力量。(238)
***
纳粹党及其组织所受的种族-秘术运动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和铁锤协会本身,就是李斯特的阿尔玛恩骑士团和兰茨的新圣殿骑士团的民粹主义版本。赫尔曼·波尔和弗里奇的日耳曼骑士团分道扬镳是出于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原因,塞博滕道夫后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将修黎社同波尔的圣杯骑士团瓦尔法特分部区分了开来。德意志工人党同修黎社的决裂,只是种族-秘术运动脱离一帮无能的分支组织,演变成一个能够在魏玛共和国整个社会范围内获得支持的群众政党的又一步。
尽管有这些重要的转变,修黎社和早期纳粹运动都拥有超自然想象,这一点超越了它们内部政治和组织上的细微差异。(239)弗里奇、塞博滕道夫和瑙豪斯、埃克哈特、罗森贝格与希特勒、希姆莱、赫斯以及达雷,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迷恋北欧神话和日耳曼异教,迷恋诸如雅利安智慧学之类的神秘学学说,以及种族(“血统”)、空间(“土壤”)、心理学(“魔法”)这些边缘科学理论。(240)
莫尼卡·布莱克提醒我们,“纳粹主义来自日耳曼文化。从许多方面来看,其象征符号和图像都根植于过去”。“把旧符号拿来重塑”给了纳粹思想一种“熟悉感,使之显得没有什么革命性,而是稀松平常”。(241)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广义上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向来都是“含糊的,不确定的,而且刻意为了非理性的需求留出了最大可能的余地。其追随者效忠的并不是该学说的正统性,而是元首本人”。但是,纳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参照点不够清晰,和他们所呼吁或所激起的情感的强度并没什么关系”。(242)
如果说纳粹主义以超自然的方式进入政治,导致它和自由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渐行渐远,那么它对那些否认“‘客观体验’,贬低‘理性和知性却对本能和直觉青睐有加’,而且下意识地抹除了‘幻想和现实之间边界’”的德国人则是颇有吸引力的。(243)数百万德国人受到了战败、革命爆发、社会政治危机的打击,他们“抛却太过复杂、困难、令人泄气的现实,沉溺于精心编织的幻想之中”。(244)照彼得·费舍尔的说法,德国人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而是将政治和历史事件视作“最终由超自然力量来决定的变动不居的状态的一部分”。政治和社会现实“被转移到一个概念领域,这个领域由天堂激发的报应和奇迹、集体受难和复活这样的概念构成”。(245)
和魏玛共和国头十年主政的主流政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纳粹党利用了更广泛的超自然想象,它面对的是后者早已对世俗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的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和普通德国人一样,许多纳粹分子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这些人越来越将神秘主义、异教、边缘科学的受欢迎的层面当作应对现代生活复杂性的基础。(246)初创的纳粹党可能在1919年时脱离了修黎社,但其领导人继续利用两者共用的超自然想象来忽略和超越魏玛民主制的社会政治分歧。(247)
(1)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255.
(2)Rudolf von 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Urkundlich aus der Frühz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Munich:Deukula-Grassinger,1933,p.8.
(3)Hermann Gilbhard,Die Thule-Gesellschaft:vom okkulten-Mummenschanz zum Hakenkreuz,Munich:Kiessling,1994,pp.15-18.
(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43-4.
(5)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10-1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5-7.
(6)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92;Daim,Der Mann,pp.17-48;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
(7)Puschner and Vollnhals,‘Forschungs- und problem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p.18-20.
(8)Puschner and Vollnhals,‘Forschungs- und problem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p.22-3;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6-204;Treitel,Science,pp.210-42;Staudenmaier,‘Occultism,Race and Politics’,pp.47-70.
(9)Howe,Urania’s Children,pp.84-7;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0-4;Reginald Phelps,‘Before Hitler Came:The Thule Society and German Order’,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5:3(September 1963),pp.245-61;Mosse,Masses and Man,pp.165-71.
(10)Reginald Phelps,‘Theodor Fritsch und der Antisemitismus’,in Deutsche Rundschau 87(1961),pp.442-9;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4-5.
(11)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8-50.
(12)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57-8;Robert Gellately,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4,pp.163,176-83.
(13)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58-9;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4-6.
(1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14-16;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52-4;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45.
(15)Howe,Sebottendorff,pp.26-7;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5-7;Franz Wegener,Weishaar und der Geheimbund der Guoten,Gladbeck:Kulturförderverein Ruhrgebiet(KVFR),2005,pp.35-6;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64-5.
(16)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7-8.
(17)同上,pp.248-50;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5-7;Wegener,Weishaar,p.36。
(18)Winfried Mogge,‘Wir lieben Balder,den Lichten ...’,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p.49-50.
(19)Howe,Sebottendorff,pp.26-7;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45.
(20)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33-5.
(21)Egbert Klautke,‘Theodor Fritsch:The “Godfather” of German Antisemitism’,in Rebbeca Haynes and Martin Rady,eds,In the Shadow of Hitler,London:Tauris,2011,p.83;Wegener,Weishaar,p.36.
(22)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8-9.
(23)Howe,Sebottendorff,p.25.
(2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28;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45.
(25)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8-50.
(26)Puschner and Vollnhals,‘Forschungs- und problem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pp.22-3;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5-7.
(27)Rose,Thule-Gesellschaft,p.20.
(28)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9-50.
(29)Szczesny,‘Die Presse des Okkultismus’,p.119.
(30)Staudenmaier,Occultism,pp.64-5.
(31)Richard J. Evans,‘The Emergence of Nazi Ideology’,in Jane Caplan,ed.,Nazi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3.
(32)Egbert Klautke,‘Theodor Fritsch(1852-1933):The “Godfather” of German Anti-Semitism’,in Rebecca Haynes and Martyn Rady,eds,In the Shadow of Hitler:Personalities of the Righ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London:I. B. Tauris,2011,p.83.
(33)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7-8;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31-2.
(34)Howe,Sebottendorff,pp.5-7.
(35)Howe,Sebottendorff,pp.11-13;Rose,Thule-Gesellschaft,pp.26-32;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35-9.
(36)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39-40;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6-7.
(37)Peter Staudenmaier,‘Esoteric Alternatives in Imperial Germany:Science,Spirit,and the Modern Occult Revival’,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pp.23-41;and 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
(38)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p.73-93.
(39)Howe,Sebottendorff,pp.16-17.
(40)Howe,Urania’s Children,pp.86-9;Howe,Nostradamus,pp.126-7.
(41)Howe,Sebottendorff,pp.17-23.
(42)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41-3;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47-51;Rose,Thule-Gesellschaft,pp.32-3.
(43)Rose,Thule-Gesellschaft,p.20.
(44)Howe,Sebottendorff,pp.24-7,32-4;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20-3.
(45)Howe,Sebottendorff,pp.33-4.
(46)Howe,Sebottendorff,pp.28-9.
(47)Rose,Thule-Gesellschaft,pp.34-5;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41-3.
(48)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10-15;Arn Strohmeyer,Von Hyperborea ach Auschwitz:Wege eines antiken Mythos,Witten:PapyRossa,2005;Rose,Thule-Gesellschaft,pp.37-9;BAB:NS 26/865a,‘Zur 1000-Jahr-Verfassungsfeier Islands(930-1930)am 26.-28. Juni liegt abgeschlossen vor Thule:Altnordische Dichtung und Prosa’,24 vols,eds Felix Miedner,P. Herrmann,A. Heusler,R. Meißner,G. Meckel,F. Rancke,and W.H. Vogt,Jena: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30.
(49)Rose,Thule-Gesellschaft,pp.37-9;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35-42.
(50)Howe,Sebottendorff,p.35.
(51)同上,pp.33-4。
(52)Howe,Sebottendorff,pp.33-4.
(53)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23-5;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15-18;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54-5.
(54)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47-56.
(5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49.
(56)See Howe,Sebottendorff,p.31;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53-61;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7-8.
(57)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56-7.
(58)Howe,Sebottendorff,pp.36-7.
(59)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47-9.
(60)Rose,Thule-Gesellschaft,p.211.
(61)Black,‘Groening’,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p.213.
(62)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41-2.
(63)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45-61.
(64)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54-5. See also Hartwig von Rheden in BAK:N 1094I/77,pp.24-6.
(65)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52-62;Howe,Sebottendorff,pp.1-2,60-6.
(66)Ian Kershaw,Hitler:Hubris,London:Allen Lane,1998,pp.170-3.
(67)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105-9;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56-7;Kershaw,Hubris,pp.172-4.
(68)Kershaw,Hubris,pp.116-22.
(69)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105;Kershaw,Hubris,pp.119-20.
(70)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43-6;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60-6.
(71)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90-1.
(72)同上。
(73)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90-1.
(74)同上,pp.93-102。
(75)同上,pp.111-13。
(76)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76-87,136-47.
(77)Bund Oberland,自由军团的别称。——译者
(78)Phelps,‘Theodor Fritsch’,pp.442-9.
(79)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81-4;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148-51;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49-50.
(80)参见警方报告和报纸文章中关于DAP和迪特里希·埃克哈特的内容,BAB:R 1507/545,pp.319-32。
(81)Kershaw,Hubris,pp.138-9;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51-2;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103-25;material on right-wing associations,BAB:R 1507/2034,pp.101-3,111-12.
(82)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52-4;Mosse,Masses and Man,pp.204-5;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7-8,171-81.
(83)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52-4;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57-9;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7-8.
(84)Richard J. Evans,‘The Emergence of Nazi Ideology’,in Caplan,ed.,Nazi Germany,pp.42-3.
(85)Howe,Sebottendorff,pp.66-8;几乎“希特勒所有的早期合作者都和修黎社有关,哪怕他们并非修黎社成员”。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71-5。
(86)Howe,Sebottendorff,p.14.
(87)战斗人员“将战场上的流血事件解释为一种圣餐,能把他们变成国家的使徒”。Fisher,Fantasy,p.220。
(88)同上,p.220。
(89)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56-7.
(90)Howe,Nostradamus,pp.126-8.
(91)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70-6;Rose,Thule-Gesellschaft,pp.10-11;Michael Kellogg,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White Emigrés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 Socialism,1917-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70.
(92)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14-15.
(93)https://www.historisches-lexikon-bayerns.de/Lexikon/Deutschsozialistische_Partei_(DSP),_1920-1922.
(94)interest slavery,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发明的词,指人只能通过体力或脑力劳动来谋生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人通常都会受到剥削和压榨。他认为正是“利益奴隶制”让魏玛共和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只有破除这种制度,德国才能繁荣。——译者
(95)Kershaw,Hubris,pp.126-7.
(96)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183-9.
(97)据修黎社的一名成员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后的回忆:“对我来说,与神秘事务之间的关系总让我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把一些很成问题的成员带进修黎社。”See also ‘Vortrag Wilde uber Okkultismus’,7 May 1919. BAB:NS 26/2233。
(98)Puschner and Vollnhals,‘Forschungs- und problem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pp.22-3.
(99)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9-10,189-90;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50-1;Howe,Sebottendorff,pp.37-8;Darré biography in BAK:N 1094I/77,pp.5-6.
(100)Howe,Sebottendorff,pp.37-8.
(101)Goodrick-Clarke,Roots,pp.221;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152-66.
(102)Alan Bullock,Hitler:A Study in Tyranny,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1,p.67.
(103)Goodrick-Clarke,Roots,pp.150-4;Howe,Sebottendorff,pp.66-8,190-6;Ernst Piper,Alfred Rosenberg:Hitlers Chefideologe,Munich:Blessing,2005,pp.19-42;Robert Cecil,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New York:Dodd,Mead,and Co.,1972,pp.34-5.
(104)Puschner and Vollnhals,‘Forschungs- und problem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pp.22-3.
(105)Phelps,‘Before Hitler Came’,pp.254-6;另请参见警方报告22.2.24,BAB:R 1507/2022,pp.112-14;1.12.24,BAB:R 1507/2025。
(106)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57-8.
(107)Essner,Nürnberger Gesetze,pp.33-8;Samuel Koehne,‘Were the Nazis a völkisch Party? Paganism,Christianity,and the Nazi Christmas’,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4(2014),pp.765-9.
(108)Koehne,‘Paganism’,pp.765-9;参见以下警方报告6.1.23,BAB:R 1507/2019,pp.10-11;March 1927,BAB:R 1507/2032,pp.60-3;7.1.22,report on the Bund Oberland,BAB:R 1507/2016,p.75. Michael Kater,Das ‘Ahnenerbe’ der SS:1935-1945,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4,pp.17-18;16.10.34,letter from Gauamtsleiter Graf praising Schmid;10.12.34 letter;Frenzolf Schmid to RSK,12.8.35,BAK:R 9361-V/10777。
(109)同上,pp.778-9。
(110)同上,pp.777-8。
(111)Koehne,‘Paganism’,pp.781-3.
(112)同上,pp.783-4。
(113)Ormuzd,古波斯的光明神、善神,也译作阿胡拉·马兹达。——译者
(114)同上,pp.786-7。
(115)希特勒在1925年纳粹党再次奠基的仪式上,提拔丁特尔在党内的地位,将其排在第五。参见以下警方报告20.12.24,BAB:R 1507/2025,pp.141-5;Nico Ocken,Hitler’s Braune Hochburg:Der Aufstieg der NSDAP im Land,Thüriingen(1920-33),Hamburg:Diplomica,2013,p.65;Essner,Nürnberger Gesetze,pp.33-5。
(116)参见以下警方报告22.7.25,BAB:R 1507/2028,p.14;report from 1.10.28,BAB:R 1507/2029,pp.126-7;1927 reports,BAB:R 1507/2032,p.77;然而,直到1939年,党卫军仍然鼓励戈培尔的帝国文献室给丁特尔优待,因为他是“资历最老的党员之一、图林根大区的首任长官”。See SD Report,18.6.39,BAB:R 58/6217。
(117)Fisher,Fantasy,pp.5-6.
(118)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14-15.
(119)Treitel,Science,pp.216-17;Koehne,‘Paganism’,pp.760-2.
(120)The source:‘Erkenntnis und Propaganda’,Signale der neuen Zeit. 25 ausgewählte Reden von Dr. Joseph Goebbels,Munich: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34,pp.28-52.
(121)Puschner and Vollnhals,‘Forschungs- und problem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pp.22-3.
(122)Ernst Anrich,Protokoll,IfZG 1536/54(ZS Nr.542),pp.3-4.
(123)Bernard 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268.
(124)Koehne,‘Paganism’,p.764;see also Konrad A. Heiden,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New York:Alfred Knopf,1935,pp.66-9;Piper,Rosenberg,pp.15-17;Samuel Koehne,‘The Racial Yardstick:“Ethnotheism” and Official Nazi Views on Religion’,German Studies Review 37:3(October 2014),p.577.根据纳粹学者恩斯特·安里希的说法,“希特勒早期反对纳粹种族运动的言论被其支持者忽视了”。NL Ernst Anrich,IfZG:ZS 542 1536/54,pp.3-4。
(125)See John Ondrovcik,‘War,Revolution,and Phantasmagoria: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in Germany,1914-1921’,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
(126)Peter Longerich,Himml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77-8;Gilbhard,Thule-Gesellschaft,pp.15-21,67-9;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64-5;Szczesny,‘Die Presse des Okkultismus’,pp.119-22,131-44;Fisher,Fantasy,pp.11-12.
(127)Claus E. Bärsch,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Munich:Fink,1998,pp.43-4.
(128)Koehne,‘Paganism’,p.763;see also Bullock,Hitler,pp.79-80;Goodrick-Clark,Occult Roots,pp.169-70;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56-7;Bärsch,Politische Religion,pp.79-83;Trimondi,Hitler,pp.17-20.
(129)Heiden,History,pp.42,66.
(130)Fisher,Fantasy,p.6.
(131)Ryback,Hitler’s Private Library,p.30.
(132)Bullock,Hitler,pp.78-9.
(133)The Midgard Serpent,米德加德蛇是北欧神话中的人间巨蟒。——译者
(134)Kellogg,Russian Roots,pp.73-4;Alfred Rosenberg,Dietrich Eckart:Ein Vermächtnis,Munich:Eher,1935,pp.53-4.
(135)Steigmann-Gall,Holy Reich,pp.17-22,142-3;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pp.94-5.
(136)Steigmann-Gall,Holy Reich,pp.21-2;Dietrich Eckart,Der Bolschewismus von Moses bis Lenin:Zwiegespräch zwischen Adolf Hitler und mir,Munich:Hohenheichen,pp.18-25.
(137)desert spirit,民间传说中沙漠可怖的化身。——译者
(138)Rosenberg,Eckart,pp.23-4.
(139)同上,pp.26-8。
(140)Bärsch,Politische Religion,pp.58-9.
(141)Kellogg,Russian Roots,pp.70-3.
(142)Steigmann-Gall,Holy Reich,pp.17-22,142-3;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pp.94-5;Eckart,Bolschewismus,pp.18-25;Heiden,History,pp.66-9;Piper,Rosenberg,pp.15-17.
(143)Bärsch,Politische Religion,pp.198-9,206-8;Spence,Occult Causes,pp.128-9,144-6;Alfred Rosenberg,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mazon,2012(1930),1934,pp.21-144;Bronder,Bevor Hitler kam,pp.219-25.
(144)Rosenberg,Myth,p.4.
(145)同上,pp.5-7;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68-9。
(146)Piper,Rosenberg,pp.179-230;Williamson,Longing,pp.290-2;Mosse,Masses and Man,pp.71-5;Alfred Rosenberg,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als Verkünder und Begründer einer deutschen Zukunft,Munich:Bruckmann,1927;Spence,Occult Causes,pp.126-8;Kater,Ahnenerbe,pp.32-3.
(147)Bronder,Bevor Hitler kam,p.94.
(148)Monica Black,Death in Berl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9.
(149)Mosse,Masses and Man,p.167.
(150)同上,pp.71-3。
(151)英灵神殿是北欧神话中的天堂,也音译为瓦尔哈拉。——译者
(152)Cecil,Myth,pp.95-6;see also Steigmann-Gall,Holy Reich,p.263.
(153)Adolf Hitler,Mein Kampf,Boston,MA:Ralph Mannheim,1943,pp.402,324,327,544,665,141;see also H. Schneider,Der jüdische Vampyr Chaotisiert die Welt(Der Jude als Weltparasit),Lüneberg:Gauschulungsamt der NSDAP,1943;Fred Karsten,Vampyre des Aberglaubens,Berlin:Deutsche Kulturwacht,1935;Ernst Graf von Reventlow,The Vampire of the Continent,New York:Jackson,1916.
(154)Roger Griffin,ed.,Fas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21-2.
(155)Hitler,Mein Kampf,pp.63,662,480;Schneider,Der jüdische Vampyr;Karsten,Vampyre des Aberglaubens;Reventlow,Vampire of the Continent;Heiden,National Socialism,pp.66-70.
(156)Black,Death in Berlin,p.76.
(157)同上。
(158)Hans-Adolf Jacobsen,‘“Kampf um Lebensraum”:Zur Rolle des Geopolitikers Karl Haushofer im Dritten Reich’,German Studies Review 4:1(February 1981),pp.79-104.
(159)Wolf Heß,Rudolf Heß,Briefe 1908-1933,Munich/Vienna:Langen Müller,1987(25.6.19),p.243;Joachim Fest,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Portraits of the Nazi Leadership,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0,pp.4-5,190-1.
(160)Heß,Rudolf Heß,13.11.18,25.6.19,pp.235,243;Fest,Face of the Third Reich,pp.190-1.
(161)指颇受希特勒器重的德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于1941年5月10日驾机飞往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坠机,赫斯成功跳伞,只是脚踝受伤,在与丘吉尔见面后遭英方扣留,直至二战结束。希特勒对此声称并不知情。——译者
(162)Smith,Politics,pp.229-32;Ach,Hitlers Religion,pp.31-49;Wolf Rüdiger Hess,ed.,Rudolf Hess:Briefe,Munich:Lange,1987,pp.17-18;Glowka,Okkultgruppen,pp.25-6;Treitel,Science,pp.213-16;see also Bormann to Gauleiter,7.5.41,BAB:NS 6/334;Bronder,Bevor Hitler kam,pp.239-44.
(163)Heinz Höhne,Order of the Death’s Head:The Story of Hitler’s S.S.,New York:Coward-McCann,1970,pp.43-4.
(164)Longerich,Himmler,pp.70-1,78-9.
(165)Nibelungenlied,是德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译者
(166)芙蕾雅是北欧神话中爱情、战争、魔法、生育女神。洛基是北欧神话中的火、诡计、谎言之神。——译者
(167)Heather Pringle,The Master Plan:Himmler’s Scholars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Hyperion,2006,p.18.
(168)Trimondi,Hitler,pp.27-8.
(169)Longerich,Himmler,pp.77-8;参见关于Heinrich Himmler的目录(4.9.19-19.2.27),BAK,NL Himmler,N 1126/9;Treitel,Science,pp.214-15。
(170)Trimondi,Hitler,p.28.
(171)Longerich,Himmler,p.739.
(172)Wesen und Geschichte des Werwolfs,BAB:R 58/7237,pp.54-73.
(173)同上,pp.89-91。
(174)Robert Eisler,Man into Wolf,London:Spring,1948,p.34.
(175)同上,p.35;另请参见1927年的小册子和“狼人组织”的指导手册,no.32(November 1928),BAB:R 1501/125673b,pp.69-76。
(176)Kurt Frankenberger,Fertigmachen zum Einsatz,Halle:Wehrwolf-Verlag,1931,pp.3-5.
(177)Karla O. Poewe,New Religions and the Nazis,New York:Routledge,2006,pp.98-100.
(178)参见1927年3月关于狼人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的警方报告,BAB:R 1507/2032,March 1927,pp.60-6,74,101-4,112,126-9;参见警方关于Theodor Fritsch的报告以及Bund Oberland,16.3.25,BAB:R 1507/2026,pp.45-51。
(179)‘See Der Wehrwolf’,3.7.24,BAK:NL HImmler N 1126/17;参见警方关于准军事组织的报告,BAB:R 1507/2028,pp.18,95,151。
(180)同上。
(181)参见关于Wolf Graf von Helldorff的报告,BAK:R 1507/2027,pp.37-8;参见警方报告,26.1.26,19.3.26,BAB:R 1507/2029,pp.40-1,90。
(182)参见1926年初的警方报告,BAB:R 1507/2028,p.16,158-9,168;关于Edmund Heines的报告,BAB:R 1507/2027,p.39;on Röhm,BAB:R 1507/2028,pp.95-9,158-9;关于海因斯和准军事团体的报告,BAB:R 1507/2031,pp.65-7;on Heines and paramilitary,BAB:R 1507/2032,p.105;Fritz Kloppe speech,16.3.30,BAB:R 1501/125673b Bund Wehrwolf,31.10.28,BAB:R 1507/2029,pp.114-17。
(183)Dow and Lixfeld,eds,Nazification,pp.13-21.
(184)Kater,‘Artamanen’,pp.598-9,602-3;Stefan Brauckmann,‘Artamanen als völkisch-nationalistische Gruppierung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924-1935’,in Jahrbuch des Archivs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2:5. Wochenschau-Verlag,Schwalbach,2006;Bramwell,Blood and Soil,p.59.
(185)Stefan Breuer and Ina Schmidt,eds,Die Kommenden. Eine Zeitschrift der Bundischen Jugend(1926-1933),Schwalbach am Taunus:Wochenschau Verlag,2010,pp.26ff.
(186)Paula Diehl,Macht,Mythos,Utopie:Die Körperbilder der SS-Männer,Berlin:Akademie,2005,p.59;Kater ‘DieArtamanen’,pp.577-80,592-8.
(187)Kater,‘Artamanen’,pp.592-8.
(188)同上,p.603。
(189)Kater,‘Artamanen’,pp.598-9,602-3;Brauckmann,‘Artamanen’.
(190)Kater,‘Artamanen’,p.600;Kater,Ahnenerbe,p.31.
(191)Kater,‘Artamenen’,pp.599-601.
(192)同上,p.597。
(193)Höhne,Order,p.53;Hans-Christian Brandenburg,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und Irrwege einer Generation,2 vols,Cologne: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1982,pp.77-80(Die Artamanen);Julien Reitzenstein,Himmlers Forscher:Wehrwissenschaft and Medizinverbrechen im “Ahnenerbe” der SS. Paderborn:Schöningh,2014,pp.47-8.
(194)Brandenburg,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195)Bramwell,Blood and Soil,pp.41-3;see Steiner’s 1923 speech ‘Die Miterleben der Geistigkeit und Bildekräfte der Nature’,N 1094I-33.
(196)Irminism,是雅利安智慧学的一股潮流,信奉日耳曼神祇伊尔明。——译者
(197)Rudolf Steiner,‘Westliche und östliche Weltgegensätzlichkeit’,Anthroposophie und Soziologie 3. Die Zeit und ihre sozialen Mängel(Asien-Europa). N 1094I/33,pp.1-7;BAK:N 1094I-77,pp.107-13.
(198)NL Darré,BAK:N1094I-77,pp.94-7.
(199)同上,pp.107-13。
(200)Black,Death in Berlin,p.76.
(201)同上。
(202)NL Darré,BAK:N1094I-77,p.57;see also Essner,Nürnberger Gesetze,pp.78-9,154-5.
(203)Stefan Breuer,Die Völkischen in Deutschland,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8,pp.218-20.
(204)http://www.zeit.de/1958/42/ueber-die-artamanen-zur-ss;August Kenstler:R 1507/2031,Lage-Bericht nr.115 from 21.12.26,p.71.
(205)Sickinger,‘Hitler and the Occult’,pp.107-25.
(206)Mosse,Masses and Man,p.66;Hamann,Hitlers Wien,pp.39-45;Goodrick-Clark,Occult Roots,pp.192-3;August Kubizek,Young Hitler,pp.117,179-83,190-8;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p.95;see Repp,Reformers.
(207)Kubizek,Young Hitler,pp.117,179-83,190-8;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music/classical-music/8659814/Hitler-and-Wagner.html.
(208)Pammer,Hitlers Vorbilder,pp.10-11;see also 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6-7;Susan Power Bratton,‘From Iron Age Myth to Idealized National Landscape: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and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Fritz Lang’s Die Nibelungen’,Worldviews 4(2000),pp.195-212.
(209)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2,194-9;Daim,Der Mann,pp.17-48;Sebottendorff,Bevor Hitler kam,pp.188-90.
(210)Martin Leutsch,‘Karrieren des arischen Jesus zwischen 1918 und 1945’,in 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96-7;Essner,Nürnberger Gesetze,pp.33-8.
(211)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3/05/hitlers-forgotten-library/302727.
(212)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Das Buch der Psalmen Teutsch:das Gebetbuch der Ariosophen Rassenmystiker und Antisemiten,Vienna:Ostara,1926;Robert G.L. Waite,The Psychopathic God:Adolf Hitler,New York:Basic Books,1977.
(213)Koehne,‘Paganism’,pp.773-4.
(214)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268.
(215)Hermann Rauschning,The Voice of Destruction,New York:Putnam,1941,p.252.
(216)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71-2;see C.M. Vasey,Nazi Ideology,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6,p.60;Koehne,‘The Racial Yardstick’,pp.589-90.
(217)Hitler,Mein Kampf,pp.402,324;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67,70-1.
(218)See Spielvogel and Redles,‘Hitler’s Racial Ideology’;see also Anson Rabinbach and Sander Gilman,The Third Reich Sourcebook,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113;see also 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4-203;Mosse,Masses and Man,p.66;Hamann,Hitlers Wien,pp.39-4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93;Kubizek,Young Hitler,pp.117,179-83,190-8;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p.95;Hamann,Hitlers Wien,pp.7-9,285-323;Howe,Urania’s Children,p.4.
(219)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267.
(220)同上,pp.267-8。
(221)Vasey,Nazi Ideology,p.59.
(222)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67-8.
(223)希特勒的超自然思维是“吕格和舍纳勒的产物”,与旧种族运动的“失败榜样”相比,它“更粗糙”、更务实。Burleigh,‘National Socialism as a Political Religion’,pp.2-3。
(224)Hamann,Hitlers Wien,pp.327-9;Mosse,Masses and Man,pp.54-7,65-7,71-3;Ach,Hitlers Religion,p.52.
(225)Bronder,Bevor Hitler kam,pp.219-28.
(226)Ryback,Hitler’s Library,pp.159-62;Schertel,Magic;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p.74.
(227)Schertel,Magic,p.37.
(228)同上,pp.42-3。
(229)Schertel,Magic,p.45.
(230)同上,p.70。
(231)同上,p.72。
(232)同上,p.73。
(233)同上,pp.74,78-9。
(234)同上,pp.82-7;劳施宁在其他地方说过,“为了全面完成自己的使命”,希特勒相信在“最危急的时刻”,他“必须像殉道者一样死去”,牺牲自己。Rauschning,Voice of Destruction,p.252。
(235)Schertel,Magic,p.92;Sickinger,‘Hitler and the Occult’,p.108;Mosse,Masses and Man,pp.54-7,71-3.
(236)Rauschning,Voice of Destruction,p.253.
(237)同上,p.240。
(238)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64-5.
(239)See Kurlander,‘Hitler’s Monsters’.
(240)Treitel,Science,pp.73-96,155-9;Williamson,Longing,pp.285-7;Zander,Anthroposophie,pp.218-49,308-34.
(241)Black,Death in Berlin,p.71.
(242)Fest,Face of the Third Reich,p.188.
(243)Fisher,Fantasy,p.6.
(244)Fisher,Fantasy,p.6.
(245)同上,pp.5-6。
(246)Treitel,Science,pp.24-6,243-8.
(247)See Williamson,Longing;Steinmetz,Devil’s Handwriting;see also Cohn,Pursuit of the Millenium;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Grabner-Haider and Strasser,Hitlers mythische 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