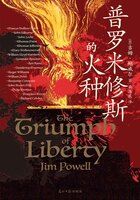
第7章 绿缎带的抗争:李尔本
在历史上,暴政多次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思考的突破。毫无疑问,17世纪中期的英国就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镇压、叛乱和内战的时代。政治小册子和传单铺天盖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就出自约翰·李尔本笔下。在80多本小册子中,他抨击宗教狭隘、税赋、审查、贸易限制和征兵制度。他拥护私有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结社、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治、权力分割以及限制政府权力的成文宪法。李尔本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这些强有力的思想集中在一起。
此外,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付诸实施。他是第一个敢于质疑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合法性的人,这个皇室法庭因镇压异议而臭名昭著。他第一个质疑议会充当法庭监禁政治对手的特权,质疑刑讯逼供。他质疑不经正式指控就监禁人的通常做法,质疑试图恐吓陪审团的法官。成年后他在大多数年月里都身陷囹圄,忍受了野蛮的毒打,曾四次面对死刑。
李尔本曾对一位朋友说:“我行动或做事并非借助偶然因素,而是基于原则;在灵魂深处,我完全相信这些原则是合理的、正确的、诚实的,因此,即使我在维护它们时需要付出生命代价,也决不会背弃它们。”
李尔本的对手称他为“平等派”(Leveller),为此他赢得民众的爱戴,使袒护压迫行为的刑事司法程序失去了民心。历史学家伦纳德·W.利维说:“其他人拥护公民自由,目的是获得自己的个人自由,但不让对手获得自由;而李尔本则在奉行自由的基本原则方面日趋一致,并且他是热情的倡导者……他牺牲了一切,就是为了自由地全方位抨击非正义……他的整个生涯就是为了自由而奋斗。”
李尔本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传记作家M.A.吉布这样描述20多岁的李尔本:“身材瘦小,外表羸弱,身体的耐力更让人担心。他衣着普通,打扮得像清教徒,头发垂到肩上,没有胡子;一张椭圆形长脸,额头很高,眼睛明亮而真诚,经常挂着忧郁的表情,这表明他内心非常狂热,能够激发他的精神,而那张坚毅的嘴则表明他意志坚强,有实现目标的勇气。”
利维承认:“像李尔本这样的人,把不合作主义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虽然让人钦佩,却非常难缠。他的要求太过苛刻,毫不妥协,对自己的理想绝不退让。他桀骜不驯、无所畏惧、不屈不挠、难以相处,是全世界最冷酷无情、最具争议性的人之一……英国没有谁比他更能讲话,没有谁比他更善于撰写政治小册子……如果李尔本是某个作家想象力的产物,人们或许会嘲笑这个牵强附会的人。在宗教、政治、经济学、社会改革、刑事司法等一切方面,他都是一个激进者。”
1614年或1615年,约翰·李尔本出生于英国的格林尼治。他的父母名叫理查德·李尔本和玛格丽特·李尔本,都是宫廷小官。
1625年,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未经伦敦主教许可,出版或进口图书都是非法的。这位主教名叫威廉·劳德,是牛津或者剑桥大学的副校长。隶属于皇家特许出版行会的拥有许可证的印刷商协助其对无证竞争对手进行执法。年轻的李尔本与许多无证印刷商结为朋友,他参观了城楼监狱,长老会的约翰·巴斯特维克博士就因为批评英国国教官员而被囚禁于此,耳朵被割掉。通过巴斯特维克,李尔本结识了长老会律师威廉·普林,此人曾多次发表言论抨击英国国教,并因此而被处以罚金;他还被取消了律师资格,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伦敦塔内,耳朵也被割掉,面颊上烙着两个大写首字母SL(意思是煽动性诽谤者)。
政府认为李尔本跟这些人交往,很可能会制造麻烦,因此他于1637年前往享有出版自由的荷兰。为了印刷和散发未经许可的小册子,他大概动用了自己的积蓄。他首先印刷了巴斯特维克博士的《连祷》。他于1637年12月返回英国,当即被同事出卖,遭到逮捕,囚禁在城楼监狱。他的案子被提交到星室法庭,这里与普通法庭不一样,诉讼不以审问被告为基础。那些被暗示有罪的人会被宣布有罪,然后判处监禁。宪法史学家F.W.梅特兰说:“这是一个由执行政策的政客组成的法庭,而不是由执行法律的法官组成的法庭。”
李尔本因荷兰之行和清教徒非法小册子而被严刑拷问,于是他开始抨击星室法庭。之前,他从未接到过传票,也从未被指控过任何罪名。他不愿为法庭书记员支付任何费用,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尽管如此,星室法庭还是对李尔本处以500英镑的罚款,并把他拴在马车上游街两英里,即从弗利特监狱一直到威斯敏斯特宫。中途,有人朝他裸露的背部抽打了约两百鞭,治疗他的医生说他的伤口“比烟斗还大”。他戴着颈手枷,竟然还面对听众慷慨激昂地抨击政府和国教。在炙热的阳光下暴晒了几个小时之后,李尔本被带回弗利特监狱,在一间寒冷、潮湿、阴暗的单人牢房里被铁链拴了4个月。后来,代表剑桥的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发表演讲,宣布星室法庭对李尔本的判决“是非法的,违反了臣民的自由”,李尔本获释了。1641年7月5日,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勉强同意,议会通过了废除星室法庭的提案。
李尔本设法恢复了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娶了伊丽莎白·杜尔为妻;后来,妻子凭借微薄的收入养育了4个孩子,在丈夫坐牢期间不断为他提供支持,当然这是后话。李尔本在叔叔的酿酒厂找了份工作,业余时间研究哲学和法律。1642年,他弄到了一本法学家爱德华·科克写的《法学总论》。科克曾经支持普通法,反对武断的圣谕。有了普通法,地方法官就可以逐一断案,由此形成一般性判例。在使用时,这些判例往往比法规更具可预见性。
国王与议会的斗争日益激烈,李尔本也卷入这场纷争,并在议会军担任上尉。他于1642年被俘,被囚禁在牛津城堡。他拒绝了以放弃自己原则为条件的赦免,结果被判处死刑。李尔本的妻子伊丽莎白与下议院交涉,劝说议员们:如果像李尔本这样效忠议会的人也要被处决的话,那么他们更应该处决被抓的保皇党人。于是,李尔本被释放了,但是他退出了议会军,因为此时已经晋升中将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下令,每个人都要订阅呼吁镇压宗教异见的《苏格兰长老会誓约》。李尔本宣称,他宁愿“去挖胡萝卜和芜菁”,也不会拥护强制性的宗教。
李尔本受到过约翰·弥尔顿的影响,弥尔顿曾被指控违反了议会1643年6月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在出版之前,文字作品必须经政府检查员批准,还需在掌管出版业的伦敦皇家特许出版行会注册。弥尔顿获准在议会面前为自己辩护,他发表的演说后来编为一本著名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1644)。他认为,只有开放市场,出版才能自由,真理才会胜利。
1645年1月,李尔本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冤情。他批评了清教徒威廉·普林,后者虽然领教过查理一世和劳德主教的狭隘,却无法容忍其他人持不同意见。议会官员发现了一台据说是印刷李尔本肇事小册子的印刷机,便用长矛挖出了他的一只眼睛。
7月19日,李尔本因为批评下议院议长而被监禁。他拒绝回答问题,并要求知晓对自己的指控,他坚持说:“跟英国最伟大的人一样,我有权享有属于自由人的所有特权。”被送回纽盖特监狱之后,他撰写了《英国的天赋权利》(1645),再次阐述了自己的信仰:应该用英语制定法律,以方便每个人阅读;只有进行正式起诉,只有参照已知法律,只有被告能面对原告并有机会进行辩护,审判才是合情合理的。他谴责政府完全控制布道,攻击政府许可商业垄断,支持贸易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指出,政客在议会任职越久,就越容易腐败,因此他呼吁每年进行一次议会竞选,提倡普选权。他督促人们尽可能多地通过宪法诉讼纠正冤假错案,并暗示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权起来造反。
1645年10月获释后,李尔本写了《正义者的辩护》一书,阐发他对上议院的不满。1646年6月11日,他被传唤至上议院,当局质问他是否知道这本最新出版的煽动性小册子。结果他反问对方,如果要控告他,将给他安个什么罪名。然后,他开始猛烈抨击议员:“你们让我们打仗,目的就是把骑在我们身上的老骑士和暴君赶下来,然后你们自己再骑在我们身上。”上议院把他送进了纽盖特监狱,他在这里写出了另一本小册子《维护自由民的自由》。
李尔本的朋友再次赶去为他辩护。伊丽莎白·李尔本一次次组织妇女团体前往下议院,请求为她的丈夫伸张正义。印刷商理查德·奥弗顿也撰写小册子为李尔本辩护,结果他也被关进了纽盖特监狱。
10月,奥弗顿完成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射向所有暴君和暴政的箭:从纽盖特监狱射进武断专制、享有特权的上议院的内脏》。他写道:“世界上每个人都天生获得了一份个人财产,任何人都不能侵犯或者侵占。对于每个人而言,他就是他自己,就是一种自我拥有,否则他就不是他自己……没有谁有权力支配我的权利和自由,反之亦然……所有人生来就平等地享有财产和自由。”
历史学家G.P.古奇提到:“议会如此不明智地对待英国最受欢迎之人,这显然是在为自己树敌。这一股新兴力量正在伺机而动,准备一举将议会摧毁。”李尔本的思想激发军队激进分子起草了《人民公约:以共同权利为基础,谋求稳固和目前的和平》,这是现代宪法的前身,它说明主权属于人民。它呼吁每两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规定代表和人口应该保持一定比例,并提出宗教自由,禁止征兵制,同时设想了一种法治:“在所有已经制定或者将要制定的法律中,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同等的约束;在普通法律程序中,职位、财产、特权、学位、出身或者地位都不能成为任何人免受制约的理由。”
1647年10月28日和29日,《人民公约》成为帕特尼“军队辩论”的议题,普通人都参与到讨论国家的未来中来。然而,这些激进的思想威胁有可能破坏克伦威尔取得军事成功所依赖的严厉纪律,因此他终止了辩论会。尽管如此,《人民公约》仍然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此前,人们从未尝试通过讨论去认真地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尽管还在监狱服刑,但李尔本却获准离开监狱一段时间,于是他开始组织第一个政党。李尔本的支持者佩戴海绿色的缎带,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下议院线人乔治·马斯特森汇报说,李尔本的密探“不仅手握请愿书,而且还进入王国各个郡的城镇、教区(如果可能的话),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自由和特权”。1648年1月,马斯特森向议院告密,议院命令李尔本接受审判,罪名是煽动罪和叛国罪,他再次入狱。李尔本说,伊丽莎白勇敢地挡在他与挥舞利剑的士兵之间,这才救了他一命。在监狱中,他撰写了一些小册子,比如《挑战暴君》(1月28日)、《人民的特权》(2月6日)、《鞭笞现行上议院》(2月27日)、《受压迫民众的呐喊》(与理查德·奥弗顿合作,2月28日)、《囚犯呼吁人身保护权》(4月4日)、《受压迫者强烈而悲切地请求上法庭》(4月7日)。
平等派提交了一份请愿书,80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释放李尔本。当时,内战之火可能重燃,下议院需要平等派的支持,因此在4月18日投票放弃了对李尔本的指控。议院投票决定给他3000英镑作为冤狱补偿,但是李尔本拒绝了纳税人的钱。
1648年11月,克伦威尔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军中很多人士都希望处死国王。然而,李尔本却宣称,自由取决于制约和平衡,因为他观察到,国王、议会和军队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不过,约翰·弥尔顿却赞同绞死国王。国王于1649年1月30日被执行了绞刑,弥尔顿立刻赶印了一本小册子捍卫他的立场;彼时,他正在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政权中担任秘书。
3月28日,议会军派遣了约100名士兵前去捉拿李尔本和奥弗顿,理由是怀疑他们撰写激进小册子。据说,克伦威尔大发雷霆:“我告诉你,先生,对付这些人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把他们碎尸万段。”在他被关进伦敦塔监狱之后,当局发布了一个新版的《人民公约》。
平等派为“伦敦塔诚实的约翰”散发请愿书,大约有4万人签名。他们举行集会,戴着海绿色缎带,高唱“身穿海绿色连衣裙的漂亮贝丝”。克伦威尔怒诉:“只要李尔本还活着,王国就永无宁日。”1649年5月,他在伯福德打垮了平等派,但他并没有处决李尔本,显然是害怕会引起强烈的危险反应。
不久,克伦威尔动身前去镇压爱尔兰叛乱,他们从1641年起就在反抗英国的统治。在爱尔兰东部海岸的德罗赫达和韦克斯福德,他下令发动了一场针对爱尔兰叛军的恐怖大屠杀,并把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转到英国人名下。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说:“在被克伦威尔征服的爱尔兰,长期以来,遭受迫害的牧师是人民的唯一领袖,因为英国人已经毁掉了爱尔兰的绅士阶层。克伦威尔的殖民使得爱尔兰人数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最典型的由牧师领导的民众。”
李尔本仍被关在伦敦塔中,他发表了另一本小册子《自由的法律基础》(1649年6月),抨击军政府“随心所欲地统治我们,把我们当成被征服的民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被保释出狱看望家人(两个儿子因患天花而奄奄一息)期间,他又发表了小册子《控告克伦威尔犯有叛国罪》(1649年7月),攻击更加严厉,并警告说,只要克伦威尔还活着,英国就“将一无所有……只有战争,年复一年,到处是割喉流血”。
9月14日,首席检察官埃德蒙·普里多想了解李尔本是否写过《伦敦年轻学徒的大声疾呼》一书。李尔本否认政府有质问他的权力,结果又被逮捕,被控犯有叛国罪。传记作家波林·格雷格说:“乍一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经历过斗争。然而,显而易见,多年的斗争已经让他的面貌显得粗犷,年轻人脸上的清秀已经杳无踪影。多年前眼睛受的伤害导致毁容,因此他的脸在安静时看起来略显阴沉。他的头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从耳边卷起,而是垂到肩膀上,变得有点儿灰白,有点儿蓬乱……可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眼睛和嘴巴上。23岁时,李尔本曾简单地认为,一件不公正的事如果被证实为不公正,就可以将其废除。7年后,幻灭和痛苦的挣扎在他嘴巴的形状和眼里的质疑中都留下了印记。”
李尔本一如既往为自己辩护。他不顾法官的反对,再三告诉陪审团,他们有权对本案的案情和所依法律做出裁决。这一原则被称为陪审团否决权,意思是说如果一条法律不公正,那么独立陪审团就有权宣布违反该法律的人无罪。1649年10月26日,李尔本出人意料地被无罪释放。但是,1651年12月,议会再次命令李尔本缴纳7000英镑罚款并离开英国,还威胁说如果他敢回国,就会被处以死刑。李尔本在1653年6月14日试图穿过英吉利海峡潜回英国,结果被治安官抓获,押送至纽盖特监狱。在等待审判之际,他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法律抗辩》,滔滔不绝地向法庭陈述自己应该有阅读起诉书的权利,并质疑其法律基础的合法性。陪审团的裁决是“约翰·李尔本没有触犯任何死罪条款”。他被送回伦敦塔,然后又被送到泽西岛的奥格尔山城堡,最后到了多佛城堡。在多佛城堡,他与贵格会教徒谈话,获得内心的些许安宁。这些教徒都是乔治·福克斯的追随者,福克斯是个制鞋学徒,相信即使没有牧师、祷告书或者仪式,神圣的启示(“内心之光”)也会出现。
1657年8月,李尔本获得假释前往埃尔特姆探望妻子,结果健康状况恶化。8月29日,他在伊丽莎白的怀抱中与世长辞,卒年大概是43岁。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将留下这句证言:我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自由。”有400多人跟随他的朴素木棺材,他被安葬在伯利恒教门附近的教堂墓地里。
斯图亚特君主政体于1660年复辟,但国王查理二世并未收回父王曾经拥有的所有权力。像星室法庭之类的皇室特权法庭再也没有出现过。控制税收的是议会,而不是国王。这些都是约翰·李尔本永恒遗产的一部分。他针对刑事司法改革的许多大胆要求也实现了。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说:“对约翰·李尔本的审判表明,清教徒革命为遭政府控告的人争取到了更多的自由……现在,有关事实和法律的问题都交给了陪审团,他们可以自由地宣布嫌犯无罪,而不用考虑后果;原告方的证人可以进入法庭,在被告面前当面陈述;被告方的证人也可以经传唤出庭;被控告者再也不用受国王王室法律顾问的质问,再也不用遭到严厉审讯,不用被迫为自己提供证据。慢慢地,经过这场血与泪的洗礼,正义与自由携手前行。”历史学家H.N.布雷斯福德补充说:“由于这个小伙子的勇敢,英国法律自始至终都没有以逼供为目标。对于美国人而言,这一权利似乎必不可少,因此他们把它体现在了宪法的第五条修正案中。”但是,李尔本却被人遗忘了。由于他的小册子没有署名,很快就散佚了;他的许多激动人心的句子都隐藏在大量关于具体法律案件的文章中,而后世之人对此并不关心。第二个大胆提出有关自由见解的人是哲学家约翰·洛克。牛津大学学者彼得·拉斯利特断言:“洛克明显继承了内战时期激进作品的成果,不过是从谈话和随意的接触中了解到的,而不是通过熟读书面材料。”
1679年,李尔本已经去世20多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阿尔杰农·西德尼、理查德·朗博尔德和他们在伦敦绿缎带俱乐部(Green Ribbon Club,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平等派时期)的同仁们酝酿了一场全面暴动,反对国王查理二世。事后沙夫茨伯里逃往波兰,但是其他反叛者都被逮捕,面临死刑。曾经是平等派成员的朗博尔德在绞刑架下发表演讲,再次肯定了平等派的原则。他宣称:“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被上帝所选中去骑在别人头上的,因为没有谁来到世上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也没有谁生来就穿着马靴、佩着马刺骑在别人背上。”托马斯·杰斐逊把朗博尔德的话稍加改编,写进了他在1826年6月24日的一封信中:“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或者正在意识到人权。科学之光普照大地,人们看清了这一事实:芸芸众生,降临世间,背上并无马鞍,也没有少数受宠之人,托上帝鸿福,穿马靴,佩马刺,合法地骑在他人身上。”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认识到了平等派的重要意义的作家之一。他写道:“在过去两百年里,英国仅仅是在缓慢地、尝试性地推行内战末期军政府提出的政治和宗教改革计划。”
我们今天享有的许多最基本的公民自由,约翰·李尔本都曾经为之奋斗过;他只不过是个学徒,却敢于提出关于自由的新见解,并坚持原则立场,不顾生命危险,反抗暴君,传播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