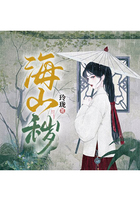
第1章 玲儿坠
定亲方没几日,我的未婚夫没了。
说是撞上仇家,当街被捅了刀子,连着当时同路商议婚事的我父母也没放过。
同一天里,我成了孤女,也成了未亡人。
民国三年,惊蛰,宜纳彩忌祈福。
农历二月才开头,北京城的冬还没缓过来,煤市东街上,却挤满了人。
好大一支人畜招摇的队伍,樟木妆奁、西洋穿衣镜、四匹枣红大马、两头小黑驴,另有一两人抬的大箱子跟在后面,喜洋洋美滋滋披红挂绿好不喜庆。
纵是没有唢呐开道,也不妨人知晓这是一只送彩的队伍。
最打眼的,还是队伍头上那个人,一个碗口粗的竹筒,上顶着托盘,下抵着脑瓜顶,既不抖也不晃,大摇大摆走在最前头。那托盘里垫着红布,红布上金灿灿一根寸宽的金条。
能撑得起这场面的,莫说煤市东街,横看半个南城,也只那一家……
彩礼送的上脸面,收礼的人家却未见得喜。
“可不能啊,不能让玲儿入洪家啊……当家的,可不能啊。”
“这有什么不能的?人家洪家二少爷是续弦,明媒正娶。”
“那是洪家……”
“废话,就是洪家,才拒不得!”
“讷讷,谁家的东西?”清脆脆的声儿断了屋内争执。
“这孩子,咋不知敲个门。”那福隆借责备掩饰尴尬,荣氏趁机扭头抹了脸上的泪。
那玲儿歪着头,水盈盈的杏眼眨了又眨,她一早就被父亲支去了叔公家送东西,这会儿回来,才进胡同子就有人跟她道喜,再看这满院子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玛玛刚才说什么洪家?”那玲儿又问。
那福隆回手拿过烟匣子,对着里面三两个烟袋锅左挑右选,又是填烟丝,又是对烟火,好半晌才鼓捣出个烟圈来,烟圈聚了又散,话却没一句。
“玛玛不吱声算怎个回事?可是煤市东街的洪家?”末了还是那玲儿自己回了自己的话。
“你也17了,这么大的闺女算出阁晚的了,洪家……你也知道些,咱家关里跑山货,来回的路子都靠洪家,跑山人没有不过洪家的。你嫁过去,也算享福了。”那福隆鼓了口烟,圆眼珠半耷拉着眼皮,像一只没什么精神的京巴狗。
“跑山人没有不过洪家的……八大胡同里那些个挂粉红灯笼的院子和海山赌坊呢?他们过不过洪家?”那玲儿盯着空中徐徐散去的烟气,冷了一张俏脸。
这话把荣氏刚抹干的眼泪又引了出来。
“当家的,回了吧,那样的人家……咱高攀不起啊!”荣氏哭着跪倒在那福隆脚边,反倒把那福隆惹恼了。
“回什么回?这样的婚回了,我那家关里的买卖还做不做?我这大个家业就为这毁了不成?你别一天哭唧唧的,这明媒正娶,你不乐意个什么劲儿?
要不是人家洪家想跟在旗的结亲,你以为能轮着咱那家?要不是我从小把玲儿当小子养,又是请先生又是见世面的,你以为人家能瞧上咱?这是我那家几辈子攒出来的缘分,行了,起来吧!”那福隆急吼吼地喊,好像自己这辈子呕心沥血培养她费尽了心思。
“那是您那时候没小子,这会有小子了,姑娘就不当人了,往开妓院的人家送……”那玲儿最是听不得这话,梗着脖子回嘴。
“啪”一巴掌抽在脸上,没说完的话给憋了回去。
那福隆走了,他是气的,莫说他在外面养个女人,就是娶进门来,又能怎么的?这丫头真是自小给惯坏了!
“讷讷知道的吧?前儿我去店里,大人孩子都带去了,伙计前后围着喊小东家……”
那玲儿又气又委屈,那孩子都五岁了,五岁……那玲儿自小做男孩打扮,十岁开始被那福隆带着关里关外的跑山货,到十二岁的时候,突然不让她跟了,也不允她跟先生读书,连店里也不让来了。
只说世道不太平,正赶上各地闹兵乱,讷讷也愿意她在家,这才恢复了女孩模样。这会儿看,不过就是早年间没儿子的时候,拿她当儿子养,真有儿子了,女儿也就不算什么了……
“男人嘛,外面有个把知冷热的,常有的事。”荣氏性子软,说的话也软,眼圈却是红了的。
那玲儿咬着嘴唇福了福身子,走了,走得极快,斗篷兜帽上滚的貉子毛边随着步子摇晃,好像被那无端冷风打乱了的荒草。
二月十二,宜交易,忌会亲友。
“玛玛、玛玛……讷讷……放我出去……”那玲儿连闹了几天,今儿更是一早给锁在了屋里。
“小姐,别闹了,老爷和夫人都出去了,胳膊拧不过大腿,陈妈瞧见了,洪家二少爷二十出头,跟你年岁相当,长得那叫一个俊,听说上头那个少奶奶是病殁的,留下个几岁的奶娃娃,从小带,一样亲。
何况那二少爷是受家里器重的,上面大少爷腿有残,这以后偌大的家不都得是小姐你当家……”嬷娘陈妈在门外絮絮叨叨,说着那福隆嘱咐过的话。
“讷讷也出去了?去哪了?”那玲儿眉梢轻挑,停了捶门。
“洪家来请期,日子定了,二少爷请未来岳父岳母去吃烤鸭哩!”陈妈喜滋滋地说,她也得了未来姑爷的赏,大买卖人家礼数就是周到,傲是傲了些——那样的人家,不傲才怪哩。
那玲儿倚着房门,冬要过去了,冷风从门缝挤进来,吹在耳边依旧刺骨,冷风吹凉了身子,也吹凉了心思。那些旧年里奔腾的心思都给这冷风扼住了,什么家里的独生女,什么关里关外,什么山货生意,什么去看看新学堂……都给扼住了……
被扼住的那玲儿,又一次伸手推向房门,冰凉、冷硬的木门像被冷风凝住一般,动也不动,那玲儿的手就那么抵着,直到手指冻僵,才恍惚听得门外一阵嘈杂。
乱糟糟脚步声近前,早前怎么也推不动的门“咔哒”一声开了,开得轻易又痛快。
陈妈半个身子栽进来,哭嚎悲凄:“小姐……我苦命的小姐啊……”。
越过陈妈,那玲儿看见了警察。
警察是客气的,少见的客气。可嘴里的话却说得那玲儿浑身冰冷。
“节哀……”末了,眼见着为首的官爷嘴开了又合,她使劲地听,却也只听见了一阵嗡鸣声,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陈妈……”警察走了,陈妈还在哭,那玲儿抖着腕子扯住她,大声问。
“他们说的啥?我……听不清……”那玲儿只觉得自己耳朵里嗡嗡作响,响得心烦。
“小姐……小姐……怎么办啊,怎么遇见这种事呢?好端端的三个人,怎么就没了呢?说是有人寻仇,咋就寻到咱们头上了啊,老爷和夫人都、都……咋这洪家二少爷他们也敢动手啊?这可如何是好啊……礼也过了,日子也定了……这是、这是……我苦命的小姐哟!”
陈妈说了一堆,那玲儿还是听不清,可明明听不清,眼泪却落了下来。
哭了半晌,迎着冷风吹得浑身打哆嗦,陈妈苶呆呆杵在一旁,脸上亦是两条泪沟,不算浑浊的眼满目茫然。
“洪家来人了……”门房扯嗓子跑进来,慌的。这个时候的那家,没有不慌的,人人都听见了,人人都知道了,那福隆和荣氏在去饭馆的路上被人捅了,就连洪家二少爷都没躲过去。
四五个练家子从墙上跳下来,不问不喊直接甩刀子,谁能想到在自家地盘碰上茬子。
洪家二少爷一点准备没有就让人割了脖子,那福隆路边捡了块石头还没来得及扔,就让人捅穿了肚子,荣氏吓得直嚎,也给人捅个对穿……消息早就传遍了,甚至比警察说的还仔细。
洪家送来了那福隆和荣氏的遗体,来人是个会办事儿的,里里外外说得明白、说得得体。
“大少爷交代了,日后二少奶奶的事儿就是洪家的事儿,人生无常,遭逢如此变故,洪家日后就是二少奶奶的依靠……”那玲儿耳中还杂着嗡鸣,眼盯在已入了棺的二老身上。
棺是上等的杉木,那福隆身量不高,想来这棺木是临时购置,对内里的人来说过于宽大了,荣氏的棺尚且合体,可内里的身子却僵直得骇人,刻进面容的恐惧并不曾随着生气一起消散。
“办丧有小的们,二少奶奶缓缓心神,莫坏了身子……”那人还在一样样交代,那玲儿却只觉得冷,从心里往外的冒着寒。
这寒比那挤进门缝的冷风要命多了,这会儿子想来,那算什么冷呢?不过是自己矫情罢了,嫁人而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乐呵呵应了多好,何苦闹那几天,二老临了也没听着句好话儿……这人,真就没得这么轻易?她不信,她不能信!
“真是寻仇?洪家想怎么查?可能还逝者一个公道?”那玲儿盯着棺,含着泪,声儿清冷得像数九寒冬里冻脆了的冰棱。
来人顿了顿才应:“回二少奶奶话,青天白日里的命案,自然都托给了警察署,署长那边大少爷打点过了,二少奶奶缓缓心神,在家安心服丧,莫坏了规矩,外边的事儿自有外边的人操心。”
黑道儿寻仇的事儿托给警察署?这天底下的稀奇事儿还真都让她碰见了?她不信!
那玲儿想说点什么,可她只觉得自己像冰天雪地里的一条鱼,张着嘴,没有声儿,甩甩尾巴,寻不着水,拼了命的劲儿都使出去,没得一点用。
说什么?凭着她?听听人家的话“外面的事儿自有外边的人操心”,她这会儿子还能说个什么?
隐隐的猜测引出无端寒意,冻得嘴皮子发抖,肩膀随着呼吸轻轻地颤,旁人眼里看来,是道不尽的悲。
那玲儿没言语,洪家人没言语,谁也没言语。
待嫁的新妇,眨眼就成了孤零零的望门寡,克死未过门的丈夫,还克死父母,这样的女子,这辈子,大抵就是如此了……
改朝换代的日子过得人心惶惶,越是没味儿的日子,人就越爱看热闹,咂嘛咂嘛别人的热闹,自己的日子也就有味儿了。
有时候生怕热闹不够味儿,还得自己再加上点佐料,佐料是咸的,每一次加料,都是在苦主伤口上撒盐,可看热闹的人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这热闹好不好看。
那家的丧在看热闹的人眼里,倒是连盐都不用加……
二月十三,宜交易,忌纳喜。
那家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小院子里十几个人忙忙活活唱丧,胡同里也支了丧棚,花圈白布挂了半个胡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往院里进,对着灵棚拜的涕泪横流,左一句那公,又一句老亲翁,那福隆这辈子都没得到过这种礼遇。
那玲儿站在灵棚旁,一身重孝,头盘髻,簪白绢。
头一次盘发不是为喜,反是为丧,待嫁的姑娘转天儿就成了守寡的妇,她大抵也算那家祖上头一个了。
“小姐、小姐,那、那……那女人带着小、小子来了,要归宗……”陈妈慌张张跑进来,话跟烫嘴似的不知该怎么说。
那玲儿却听明白了,不光听明白了,因着唱丧的声停了,她还听见了女人的哭声儿。
一身孝的女人领着孩子一路哭喊,进了灵棚拉着孩子就要叩头。
“我的老爷哎……我给您送行来了……你这走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女人嗓门大,哭得惨,竟没人上去拦。
那玲儿气得浑身发抖,回身抡起圆凳砸过去,人群这才乱起来,拉架的拉架,劝和的劝和,撵人的撵人。
陈妈扯着女人头发往外拽,女人冲进灵棚抱着棺木不撒手,孩子淌着鼻涕哭嚎……好一通乱,乱得那玲儿心头起火。
“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过媒了还是下定了?跑我那家来认亲了?这头是你说磕就磕的?轰出去!”那玲儿一通喊,陈妈立马下死手,女人满脑袋白绢花掉了一地。
“虎子是那家的儿子,你不能轰出去,这一支就虎子一个根儿,列位宗族长辈给个公道啊!”女人倒也不是软柿子,既然来了,自然也就没做和和善善的准备。
族里来帮衬的两个叔公,面有难色,那福隆外面养儿子的事儿,他们是知道的,那福隆准备今年把人抬进门的事儿,他们也是知道的,那是儿子,总不能扔外面,何况提前还收了女人递的银子……
“既然是那家的种……”到底有人开了口。
那玲儿扭转头昂起脖颈,旧日里水汪汪的杏眼冰刀一样看过来,声儿大得近乎破音:“我讷讷还没入土呐!”
这一声喊,让开口的人虚了心,那福隆的生意是靠着荣氏家里起来的,不然哪里能这些年没让人进门。头两年那玲儿外祖没了,荣氏又性子软,那福隆才渐渐起了心思,可到底那家承着荣家的恩呢。
“我的老爷啊,那家不容人啊,我就和虎子去陪您吧……”女人见没人帮衬,扯嗓子又是一声嚎,猫起身子就往墙上撞。
女人是真下了狠,撞得使劲,“哎哟”一声直挺挺翻倒在地,眼前一片白,半晌没觉出疼。
她撞上的,是那玲儿抛过来的纸牛,人扑在纸牛上,压碎了竹坯框,纸碎做的鬃毛落在冷风里哗刷刷乱响。
“那家的丧,你见哪门子红?”那玲儿气得恨不能伸手扇她几巴掌。
“娘……娘……”
“哟,洪家来人了!”
也不知道是小孩子扯嗓子的哭还是碍着门前的洪家人,那玲儿转了话风儿。
“等丧办完了,我给你句话,真是那家的孩子,也不能让他流落外头学那不三不四的,我家是行丧,不是绝户,说话的人还跟这站着呢!”末这一句,是说给旁人听的,在院里的,在院外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旁人。
那玲儿话说完,也不管纸活堆里趴着的女人,也不管那想开口又碍着洪家人的族叔,径直往门前迎去。
洪家人是来磕头的,来的是大少爷身边的人。
哀乐再起,唱丧的声儿又灌满了那家院儿。
“贵客惜别……”知宾颤巍巍喊。
一应的礼作罢,洪家人没走。
“二少奶奶节哀,大少爷有话儿,两边都是丧,二少奶奶先尽孝,自家这头人多,忙得过来。等事儿了了,西边临山那头有座庵,什么时候想清静了,什么时候送您过去。”这话儿说的没背人,声儿倒是不大,可该听见的都听见了。
那家的热闹算是传开了,停灵头一天,外头的女人带孩子闹丧,那家姑娘摔凳子砸人,洪家来人瞧见嫌没规矩,要给送庵里去,那家的产业给族里人盯上了……
传言就像预言,比那半仙掐卦还准。
接下来的日子里,族里那些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的三叔六公全来了,无一不是劝她把外面的孩子收回来,若是她看着碍眼,他们可以代养,到底姓那,总不能让她玛玛九泉之下不安心……
那玲儿先是不言,后是怒骂,一个两个惦记的都是那家那点家产,去大留小这种事都好意思拿来说,只差没说等她去了庵里,他们就来接房子……
惊蛰虽过了,到底不是春,夜寒得袭人骨缝。
那家乱的得一塌糊涂,陈妈病了,门房日间累了,夜里睡得死,原本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除了白日里做饭的厨娘,也就一个短工,眼见那家出事儿,结了工钱走了,这会儿连个燃炭的人都没有。
夜寒,不在开窗。心伤,不分昼夜。
那玲儿坐在榻上,裹着棉被,泪珠子一串串滚,除了泪,一声也无。白日里说了太多话,骂了太多人,这会儿,除了哭,她什么也不想做,更不想睡,怕睡了再醒……又是白天……
夜,总会明。人,总要活。
好容易熬到出殡的日子,洪家是赏了面子的,胡同丧棚里纸活堆得小山似的,清一色的细坯泡纸,工精活细还好烧,送丧的队伍更是排出一整条胡同,纸牛纸马开路,丧乐震耳,哭声连天。
不赏面子的,是那家自己人。
“你一个闺女家,打什么幡儿?又不是没儿子!”
“你一个望门寡去给爹娘摔盆摔瓦?扯淡呢嘛!”
“有儿子就让儿子来,你玛玛下去见了列祖列宗也有面儿!”
那玲儿举着幡儿站在棺前,脑仁疼得直蹦。
屋漏自然还得赶上连夜雨,不知哪个王八蛋接了外面的女人和儿子过来,让她闹眼睛。
女人作势要哭,那玲儿挥着幡儿冲过去,给死人引路的白幡儿碎遭遭戳在女人眼珠子前,忌讳的人忘了嚎。
“你儿子姓那,你可不姓,去大留小不是难事儿,这会儿给人当刀使,自己跟外面让人抹了脖子,你哭都没地儿哭!”趁着女人怔愣,转又从腰间抽出一柄小刀来。
嵌八宝的小银刀,那玲儿早年跟那福隆跑关外时候得的,一直喜欢的很,比巴掌大不多少,可戳破脖子还是够的。
女人给吓了一跳,扯着孩子往后退,刀却架在了那玲儿自己颈子上。
“幡儿,闺女不让打,还有远房的子侄,轮不着旁的人,不行,今儿你们就再葬一个!”眼是红的,声儿是冷的,心底是厌烦的,那玲儿这些日子只觉出一个厌烦,这样的日子,使人厌烦,要真能这么了了,也不是不行。
众人又惊又怒,这当小子一样养大的孩子竟没规矩到这个份上,敢跟族里长辈叫停。
几个老头想上前,却被门外人声打断。
“怎么着?那家能耐了?要逼死我洪家的媳妇儿?”声不高,音色也是好听的,却没人敢答话。
碍眼的人一个接一个让开,只剩下举着刀的那玲儿对上轮椅上的那双眼。
眼深,色沉,深潭水一般。
满院子的人,一声也无,闹哄了好些天的那家院儿里,头回静得连头发丝儿落地都能听见。
那玲儿长出口气,安静啊,真好啊,她觉得有些无力,却只能使劲儿挺直脊梁,瘦弱的身子裹在棉袍里,一身重孝,让她看起来像朵开在关外雪地扎根冰层下的冰凌花。
“给亲家翁送行。”轮椅上的人开口。
“洪大少爷。”那玲儿收回刀见礼,不用人说,她能猜出来,除了洪家大少爷洪长年,还能是谁呢?相传大少爷早年伤了腿,洪家的买卖才转了一半到二少手里,为此兄弟俩还闹了一阵子,传言总归是听过的,更何况推轮椅的正是那日来传话的人。
洪长年燃了三支香,合十做礼,他的身份,他的身体,纵使晚辈不行大礼,也是应当。
礼数尽了,洪长年才摆手道:“送老二那天,洪家来人接你。”声音是温润的,人也长得周正,只是常年不良于行,略显清瘦了些。
那玲儿盯着深潭一样的眉目,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洪家人走了。
丧乐起,哭声哀,没有哪个远房子侄敢接幡儿,白幡儿扛在了那玲儿肩头,也再没人敢多说一句。
从送去庵子里寻清净到接进洪家送二少爷……洪家的态度,变了。
二月二十七,宜安葬,忌合婚。
那玲儿今儿的孝与早前不同,白麻斜襟袄子外三尺孝布围腰,头戴本白的“箍子”,发髻上的花倒是照旧。
天未亮便出门,不过七八日,人又瘦了几分,越发显得孝服宽大。洪宅门脸宽,偌大的正门,那玲儿轻飘飘的脚步迈进去,活像谁丢了的魂魄,生气微渺。
卍字云纹的青砖影壁,门堂里阔得能停下人力车,这样的人家哪里像个民宅?可它又的确是个民宅,普普通通的如意门,门簪小、门墩无,倒也不曾越制,可这门造得却比广亮大门还宽,内宅之大更是恨不能跨出半个胡同。就是这样的宅子,偏生落在煤市东街这种地方,可这是洪家,也就不稀奇了。
那玲儿随着管家媳妇往里走,直奔西苑灵堂,黑漆漆的夜,看不清洪家到底多大,只觉走了好半晌才到。
偌大的灵堂,跪了好些人,却是一声也无,没有寻常人家的哭丧声。
“二少奶奶今儿辛苦。”管家媳妇站定在棺旁,一旁的丫头立马捧来蒲团。
那玲儿跪坐下,盯着牌位上的名字——洪长生,这是她头一回看见自己丈夫的名儿,也只有名儿。
那玲儿跪在那,看着牌位,挨着棺,身后守灵的人换了两班,那玲儿没动过,腿麻了,膝疼了,可她不想动,她现在一静下来就不想动,静啊,太难得了……
洪家也是真的静,没人理她,没人看她,就好像没她这么个人,那玲儿忍不住暗嘲自己一句“在哪儿都是不得待见的人”。
夜就这么过了,东方既白的时候,灵堂外隐隐起了动静,灵堂里的人越发少了。
“该添油了。”那玲儿盯着牌位旁已开始炸花的长明灯轻声道。
身后垂了半宿脑袋的丫头立马起身,动作利落地添油换蜡,末了还给那玲儿行了个礼。
那玲儿挺了挺腰,垂着的眼没敢抬,怕露了怯。她本是嘀咕一句,没想到真有人应,真有人动,还有人给她行礼,看来,在洪家倒比在自己家的人高看些。
大殓之礼,孝子贤孙扶棺送灵。
可洪家二少爷的孝子太小,扶不了棺,只着人背着,手里拿着幡儿。
那玲儿站在棺旁,看着那小娃,不过四五岁模样,俏生生的眼红得可怜。
“别哭了。”那玲儿忍不住拿帕子替他抹了抹泪。
“嗯嗯……你谁啊?”小娃却不领情,挥手推她。
“我……叫那玲儿。”那玲儿不知该怎么介绍自己。
“你在这儿干啥的?”小娃抽抽搭搭地问。
“送你爹。”那玲儿如实答。
“送哪去啊?”小娃听着了想知道的事儿,忘了哭。
“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那玲儿歪头。
“死人都去那吗?”小娃这话问得不像个小娃。
“嗯,我爹娘前几天送过去了,他们没回来,想来是个好地方。”那玲儿抿嘴笑,笑着笑着,泪下来了。
“大大说了,人都是要死的,你哭啥呀?”小娃劝她。
那玲儿又笑了:“你知道的还挺多,那你眼珠子是为啥哭红的?”
“哇……”这一声问,算问到小娃的伤心处了。
“我想爹爹……”小娃哭得直抽,吓坏了身底下背着他的人,慌张张把小人儿放下来,小人儿索性跑到那玲儿身边儿要抱。
“我瞧你不错,以后伺候孙少爷吧。”小娃边哭边把鼻涕抹在那玲儿的衣摆上,他就是孙少爷,大家都这么叫他,他也就这么叫自己。
那玲儿哭笑不得,抬眼间,有人推着轮椅进了院儿,小娃也重新又给背了上。
还是那张周正的脸,还是那双深潭一样的眼,没说话,没动作。
“不知他们兄弟是不是长相有似……”那玲儿如此想着,却不曾扭头看向身后棺木,她好像从没想看过棺里的人。
阴阳先生起调儿门,丧乐声里棺木起,如龙一样的送葬队伍出了洪家大门,那玲儿和一应女眷送到门口,飘洒洒纸钱落下,哭丧声又起,有撕心裂肺的嚎,也有抽搭搭的哭,更有人踉踉跄跄奔出门跪地叩头……
这才是丧,是家里有人的丧。
那福隆和荣氏走的时候,除了那玲儿,一声真哭也无……
那家,没人了……
三月初一,宜嫁娶,忌破土。
那家外面的女人又来了。
“头七才过,你就这么急?”那玲儿没有好脸色,她不是生气,她是真的病,头疼得挨不住。
“你总要给我句话……”女人原本是鼓着气势来的,可这会儿不知怎的,她有点怕那玲儿,真没见过哪家未嫁的姑娘这么横的,砸人打人还拿招魂幡指着生人,嘴里也利索,虽没什么难听的骂,可句句戳人脊梁骨。
那玲儿看着虎子,五岁的孩子,比洪家小娃大不多少,圆脸大眼,的确是像那福隆的。
“那家,你可以进……”那玲儿抬眼看向女人。
“这宅子你不能进,这是我讷讷住的地儿。”后面的话定住了女人半笑不笑的脸。
“山货行,给你吧。”那玲儿这话说得轻巧,心里的悲凉却恨不能缢死人。
“那咱明儿立个字据。”女人压着翘开花的嘴角,忙不迭上前一步。
那玲儿狠压眉心:“行,不傻,立吧,那家的东西给你儿子护住了,日后你们娘俩是升官发财还是饿死街边,与我那玲儿无关……”话没说完,女人跟想起什么似的,挑着眼又开口:“虎子到底是那家的儿子,这好歹是那家祖宅……”
“啪——”那玲儿手里的茶碗拍在桌几上,女人的话给吓了回去。
“祖什么宅?那家是什么大户人家不成?还祖宅?这是我玛玛和讷讷早年间置办的,那家祖上就是个包衣,你真以为在旗就是大户人家了?大清亡了,满族人不值钱,你也甭想着这宅里是不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有,我也不给你!”那玲儿腾地起身,女人吓得扯着孩子就走,走得头也不敢回。
那玲儿长出口气,身子软在椅上,清净了,可怎么这么乏啊,才一个月不到,就跟过了半辈子似的。
三月初四,宜动土,忌远行。
洪长生的头七一过,洪家人就来了。
那玲儿看着罩了黑纱的人力车,耳边是陈妈呜咽咽的哭,半天才挪了一步,一步腿就软了,每向前一步,就是靠近绝路一步,几步远的车,黑漆漆的纱被风吹得鼓起,纱后面不是座子,是再不能见光的人生……
“不、不去庵里。”那玲儿迈出去的脚往后撤,她本是打算认命的,山货行都给出去了,她还有什么不肯认的呢?可这会儿看着那黑蒙蒙的车,她害怕了,后半辈子,就这么黑蒙蒙地过?不,她不想。
可没人管她想不想。
“不去庵里,那小的就替洪家谢二少奶奶守贞。”话音未落,人群里上来个小子,托着三尺白绫。
“青天白日,你们要害人命不成?”那玲儿唇不见血色,自古寡妇两条路,孤零零守贞的活,痛快快守贞的死。更何况,望门寡的媳妇丧期里自杀,官家是要赏烈女牌子的,洪家又有什么不敢呢?
“二少奶奶总要挑条路走……”洪家人垂首,态度是恭敬的,恭敬而冷漠。
那玲儿扭身要走,洪家人呼啦啦围了满院儿。
“二少奶奶是见过世面的,您这身份还这么住这儿,不合适。”洪家来的还是大少爷身边的人,四十上下的中年汉子,身材壮硕,说话难听,可态度柔和,柔和地劝人去死。
话没说完,白绫小蛇一样攀上脖颈,自缢,何须登高,有个人跟后面勒住了,两手下压,一扥,气管就压住了,再一扥,脖颈就折了……
冰凉凉的白绫,刀子一样压在咽喉上,吸进来的气儿已开始不够喘,喉骨压向内里,针扎似的疼之后是铺天盖地地晕……
“好、不、不住、这儿……”挣扎着吐出几个字,白绫松了气力,冷气涌进肺里,激起猛一阵咳。
“请二少奶奶上车。”话还是恭敬的。
那玲儿扯落白绫,咬牙看着地面:“我要进洪家,既然得你们称一声二少奶奶,那我就去看顾孙少爷,娘带儿子,总合规矩吧?”清凌凌的声儿落地,像折断的冰棱,锋利又清脆。
裹着黑纱的人力车走了,那玲儿透过黑纱看着夕阳余晖,虽不大清,到底还有光……
那玲儿这次进的,是洪家的侧门,东侧门。
轮椅咕噜噜压过青石板,洪长年身上盖着厚厚的大氅。
深潭似的眼盯着那玲儿。
那玲儿张了张嘴,突然笑了。
她原本想问不去庵里是不是就真要杀了她?她以为他是好人。然后她就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洪家怎么会有好人?
煤市东街的洪家,下九流里最说得上话的人家,八大胡同的掌旗人。逼良为娼、立赌做局、压码头抽成、笼消息讹人、捅刀子茬架……这样的人家,怎么会有好人?这样的人家,是她巴巴上赶着要进的人家……
那玲儿笑了,笑得不甜,笑得不多,笑得像哭。
轮椅上的人鹰眉微蹙,洪长年没想到她见了他是这个表情,就像他也没想到她会拿椅子扔人,没想到她真敢打幡儿,没想到一个待嫁的姑娘竟一点不像个待嫁的姑娘……下边人回的话儿里就已经给了他好几个没想到。
洪长年又笑了,眉头展开,深潭一样的眼映出微光,他真的笑了,纵是前边那么多没想到,可这会儿,她要来洪家,他却是想到了的……毕竟,这是条活路啊……
夜,静得能听见风声,没有鸟叫,没有虫鸣,只有风声,罕见的,洪长年觉得这吹过东苑的风除了凉点,声儿还挺安人心。
“我愿进洪家看顾孙少爷。”那玲儿开了口。
洪长年没应声,也没拒绝,一如那玲儿每次见他时的模样,让人看不明、猜不透。
“礼过了,孝也守了,洪家日后的规矩有一个算一个,我那玲儿都照着来……求大少爷,给条好活的路……”那玲儿福下身子,既然那家的女儿做不得了,她就做洪家的媳妇儿。
“呵。”轻笑出声,深潭无波。
“送二少奶奶去西苑吧。”洪大少爷给了条活路,那玲儿跪地欲拜,却被拦了住。
“进洪家,好活不好活的,不好说啊。”洪长年话说得柔和,像一句良言,良言难劝该死鬼的良言。
娇小的人儿给送走,洪长年微抬手,厅外暗处闪出人来。
“盯着点,有什么不该有的动作……先报……看看这那家丫头还能搞出什么想不到的事儿来,要真为了那家老头的死来的,也算我没白高看她一眼……呵。”洪长年温和的语调一如既往,轻笑声里周正的脸上满目坦然,坦然得像个君子,正人君子。
轮椅压着青石板咕噜噜走了,穿过风声的洪长年,眉是蹙的,这会儿,他又觉得这风声不安心了。
但,有意思……洪家,除了藏污纳垢之外,很久都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