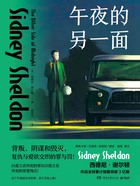
序曲
雅典:一九四七
街上车流涌动。警长乔治斯·斯库里透过灰蒙蒙的风挡玻璃向外望去。雅典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旅馆鳞次栉比,此刻感觉它们就像是矗立在一条宽阔无比的保龄球轨道上的那一排排木瓶,被球击中后,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倒下去了。
“二十分钟就能到,”身着警服的警员一边开车,一边向他保证道,“路上不堵。”
斯库里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仍然对着街上的高楼大厦发呆。一种奇妙的幻觉一直吸引着他。八月,骄阳散发出炫目的金光和阵阵热浪,把一幢幢楼房包裹起来,这些楼房看上去恰似一幅由钢铁与玻璃做成的美丽大瀑布,从空中向街道倾泻而下。
此时是中午十二点十分,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偶有三五人懒懒散散地走着,三辆警车驶过,他们也只是好奇地瞥了一眼。警车向东驶往距离市中心二十英里[1]的海莱尼孔机场。警长斯库里坐在第一辆警车里。按照惯例,烈日炎炎的午后,他的下属外出工作,他会待在舒适凉爽的办公室里。但今天的情况绝非寻常,斯库里必须亲自前往机场。他有两个考虑。第一,今天来自全球各地的名流将抵达机场,必须以合适的礼仪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保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顺利通过海关检查。第二个考虑,也是更为重要的考虑:整个机场将挤满外国报纸记者和新闻摄影记者。斯库里警长可不傻,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他就在想,新闻里如能播放他负责接待这些名流的报道,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该不会有什么坏处吧。这起举世瞩目的轰动事件能发生在他的辖区内,简直是命中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傻子才会白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此,他分别与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两个人——他的情人和妻子——进行了极其详细的讨论。安娜已近中年,农民出身,其貌不扬,性情乖戾,她告诫斯库里别去机场,做好幕后指挥,这样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他也不会受到任何牵连。而梅利娜,这位可爱、美丽又年轻的天使,则建议他亲自接待这些名流。梅利娜和他想的一样:这样的大事件可以使他一举成名。如果斯库里处理得好的话,至少能加薪;如果老天保佑,现任警察局长退休后,他甚至可能会接替这一职位。基于此,斯库里第一百次感叹于如此讽刺的事实——梅利娜是他的妻子,而安娜是他的情妇。他又一次开始琢磨自己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斯库里现在把思绪转回到眼前的事上。他必须确保机场的事情进展顺利,万无一失。他这次带来的十几名警员都是精兵强将。他心里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操控媒体。一群群的大报和名刊记者从世界各地拥入雅典,这让他着实吃了一惊。斯库里本人已经接受了六次采访,每次采访记者说的语言都不同,他的回答被译成德语、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如此出风头,斯库里便开始沾沾自喜,局长打来电话提醒他说,他身为警长公开评论尚未举行的谋杀案审判是不明智的。斯库里心想,局长说这话的真正动机肯定是嫉妒。不过,谨慎起见,斯库里决定不与局长计较这些,拒绝了之后所有的采访。当然,新闻记者总会把镜头对准那些抵达雅典机场的名流拍摄,如果斯库里碰巧出现在机场接待名流,被镜头拍到了,局长也不便诘难他。
汽车在西格鲁大道疾驰着,抵达海边时便左转驶向法利龙湾。这时,斯库里感到了压力,觉得腹部一阵紧缩。距离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了。斯库里把今晚抵达雅典的名人名单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
阿尔芒·戈蒂埃开始晕机了。他格外疼惜自己,也更爱惜自己的生命,对坐飞机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再加上希腊海岸夏季常见的湍急气流导致的颠簸,他感到阵阵恶心。他个子高,面容清瘦,有着富有书卷气的五官、高高的前额和一张时刻准备嘲弄人的嘴巴。二十二岁时,戈蒂埃就在不景气的法国电影业建立了新浪潮电影公司;随后几年,他的电影票房大涨。作为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导演之一,他的导演生涯已经登峰造极了。如果不是二十分钟前的晕机,这次旅行还是很愉快的。空姐认出了他这位大导演,很体贴地解决了他的晕机问题,并告诉他愿意随时为他效劳。飞行途中,也有几位乘客走过来对他说,他们非常欣赏他导演的电影和戏剧。不过,他最感兴趣的却是一位正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就读的英国女大学生。她正在写一篇关于戏剧的硕士论文,而阿尔芒·戈蒂埃就是她的研究对象。他们谈得很投机,但是这女孩后来提到了诺艾尔·佩奇。
“你以前是她的导演,对吧?”她问道,“我希望能去听听对她的审判。这将是一场好戏。”
戈蒂埃发觉自己猛然抓紧座位扶手,他对这个名字的反应如此强烈,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虽然事隔多年,但一想起诺艾尔,戈蒂埃就感到心中又有了往日的那种刺痛。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诺艾尔一样使他动真心,以后也不会再有。三个月前,戈蒂埃读到了诺艾尔被捕的消息,打那天起,他便毫无心思做别的事。他给诺艾尔又发电报又写信,表示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她,但始终没有得到她的回复。他一直不愿参加对诺艾尔的审判,但他知道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他自己明白,他这样关心她,就是想看看自从他们分手后,她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他承认还有另一个原因,骨子里对戏剧的那种追求驱使着他去观看这场不可错过的戏剧,在法官宣读对诺艾尔的生死判决时,去观察她的表情。
这时,飞机广播里突然传来飞行员刺耳的通知:三分钟后,飞机将在雅典降落。想到将再次见到诺艾尔,戈蒂埃开始兴奋起来,晕机的不适顿然消失。
此时,伊斯雷尔·卡茨医生正乘坐着飞机从开普敦赶往雅典。在开普敦大学刚刚建立的大型附属医院——格鲁特·西乌医院里,他是一名神经外科主任医生,担任医院院长职务,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之一。医学杂志经常刊登他的最新医学成果,他医治过的病人中有首相、总统和国王。
卡茨医生乘坐的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他想放松一下,便靠在了椅背上。他中等身材,一张坚毅睿智的脸,一双棕色的眸子深深凹陷着,修长的双手不安地动来动去。卡茨医生十分疲惫,他开始感到右腿像往常一样疼了起来。他的右腿其实已经不在了,早在六年前就被一个大个子用斧头砍掉了。
今天的事情可真多。天刚亮,卡茨医生就完成了一台手术,又马不停蹄地去查看了五六个病人的情况。为了能来雅典参加对诺艾尔的审判,他甚至不得不从董事会会议上中途退场。他的妻子埃丝特也曾试图劝他不要去雅典。
“伊斯雷尔,你现在什么也帮不了她。”也许埃丝特说的是对的,但诺艾尔·佩奇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一命,对他有大恩。卡茨医生现在想起诺艾尔,依然能感觉到和她在一起时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感觉。以前只要和她待在一起,都会有这种感觉。仿佛光是对她的回忆就足以弥合岁月留下的隔阂。当然,这是浪漫的幻想。那些美好的岁月已经消逝了。卡茨医生感到飞机开始抖动,放下轮子开始下降了。俯瞰窗外,他知道开罗到了。他将在这里转乘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雅典,去见诺艾尔。诺艾尔真的犯了谋杀罪吗?当飞机驶向跑道时,他想起了她在巴黎犯下的另一桩可怕的谋杀案。
菲利普·索雷尔站在自己的私人游艇上,凭栏远眺,看到了渐行渐近的比雷埃夫斯港。他十分享受此次的海上航行,因为他可以远离粉丝的烦扰,这可是十分难得的。索雷尔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颇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然而他成为巨星的阻碍还挺多的。他长得真算不上英俊,相反,他的脸很肿,像个连输了十几场比赛的拳击手,鼻梁也摔断过好几次,头发稀稀拉拉,走路也有些跛。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菲利普·索雷尔极具性感魅力。他受过教育,言语温和,有着与生俱来的温文尔雅的气质,再加上那卡车司机般黝黑的脸庞和强壮的体魄,使得女人为之疯狂,男人则视之为英雄。眼看着游艇就要到达港口,索雷尔再次问自己,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参加对诺艾尔的审判,他把一部电影的拍摄档期推迟了。他很清楚,只要他出现在法庭上,每天必然会被媒体记者围堵,而他的新闻经纪人和助理都不在身边,无法为他遮挡,那他将成为媒体记者的猎物。记者们肯定会把他出席这场审判的意图曲解为他想借助前情妇的谋杀案审判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无论他怎么考量,这都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但他一定要再见诺艾尔一面,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她一下。当游艇开始向海港的白石防波堤靠拢时,他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他所熟知的,和他同枕共眠过,并且他爱过的诺艾尔的形象,于是他的结论便是:诺艾尔完全具备实施谋杀的条件。
正当菲利普·索雷尔的游艇驶近希腊海岸时,美国总统特别助理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远程班机正处于海莱尼孔机场西北一百英里的高空。威廉·弗雷泽,五十出头,头发灰白,长相英俊,皱纹已爬上了他的脸庞,让他透着一种威严的气质。他盯着手里的案件诉讼摘要,一个多小时未翻一页,身体也未挪动分毫。为了此次雅典之行,弗雷泽也顾不上国会正处于危机中,硬着头皮请了假。他知道接下来的几周对他来说将多么痛苦,但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这是一次复仇之旅,这个想法让弗雷泽后背发凉,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一阵满足感。为了将自己的思绪从明天就要举行的审判这件事上移开,弗雷泽把视线转向窗外。他看到了一艘游船一颠一晃地朝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希腊海岸驶去。
连续三天了,奥古斯特·拉肖一直被晕船和内心的恐惧折磨着。他之所以晕船,是因为他在马赛登上的这艘游轮正好遇上了密史脱拉暴风,不停地剧烈颠簸;他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害怕妻子发现他这次偷偷摸摸出来要干的事。奥古斯特·拉肖,六十出头,身材矮胖,两条腿又粗又短,秃了顶,满脸麻子,一双小眼睛像猪一样贪婪,薄薄的嘴唇经常叼着一根廉价的雪茄。拉肖在马赛开了一家服装店,他可没钱像富人那样到处去度假,至少他经常对妻子这样说。当然,他也可以为自己开脱说,这次旅行并不是去度假。他一定要再见到他亲爱的诺艾尔。她离开他有很多年了,他一直在报纸和杂志的八卦专栏贪婪地搜寻着有关她职业生涯的点点滴滴。诺艾尔出演她的第一部戏时,他乘火车一路赶到巴黎来看她,但诺艾尔愚蠢的秘书死活不让他们见面。后来他看了诺艾尔主演的电影,一遍又一遍地看,反复回味着他们那难忘的一夜。是的,这次旅行会花不少钱,但奥古斯特·拉肖知道每一分钱花得都是值得的。他的宝贝诺艾尔会记得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她会向他寻求保护,而他则会贿赂法官或其他官员——如果不花太多钱的话——诺艾尔就会被释放,他会把她安置在马赛的一间小公寓里,这样她可以随时等候他的召唤。
但愿妻子别发现他背着她干的这些事。
在雅典市的莫纳斯蒂拉基贫民区里,弗雷德里克·斯塔夫罗斯正在他狭小的律师所工作,办公室设在一栋破旧大楼的二楼。作为年轻人,斯塔夫罗斯有想法,有追求,有野心。既然选了律师这个行业,他就拼命地想把它经营好。因为请不起助理,他不得不亲力亲为,包揽了所有那些调查法律背景材料的烦琐工作。通常他十分讨厌做这些琐碎的事情,但这次他却不在意,因为他明白,如果他赢了这场官司,将会有源源不断的顾客找上门来,如此他将再也不用为后半生的生计发愁。他可以和埃琳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了。他会搬进一套豪华的办公室,聘请助理,加入像阿西尼·莱斯基这样的上流社会俱乐部,在那里结识富有的潜在客户。这种华丽转型其实早已启动了。最近,弗雷德里克·斯塔夫罗斯走在雅典的大街上,就会有在报纸上见过他照片的人认出他,和他攀谈。短短几周内,他就从无名小卒摇身一变成为拉里·道格拉斯的辩护律师。斯塔夫罗斯打心底里觉得道格拉斯不是理想客户。与其替道格拉斯这样的无足轻重的人辩护,还不如为艳丽迷人的诺艾尔·佩奇效劳。可惜他自己就是个无名之辈,是没有资格为诺艾尔辩护的。不过,他,弗雷德里克·斯塔夫罗斯,能够在本世纪最轰动的谋杀案中为被告做辩护律师,这风头足够了。如果被告被宣判无罪,大家都会获得一份荣耀。然而,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斯塔夫罗斯,他反复在心里盘算着审判的结果:两名被告都被指控犯有同一罪行,另一名律师正为诺艾尔·佩奇辩护,那么如果诺艾尔被判无罪,拉里被判有罪……斯塔夫罗斯不寒而栗,不敢继续想下去。有不少记者不断问斯塔夫罗斯是否认为两个被告都有罪。这些记者也太天真了,他暗自感到好笑。两个被告是否有罪重要吗?他们手中的金钱足够让他们买到最好的法律辩护。就他的被告而言,他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过。但对诺艾尔·佩奇的律师而言……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拿破仑·乔塔斯已经被聘请为诺艾尔的辩护律师,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了。乔塔斯从未在任何大案中败诉。弗雷德里克·斯塔夫罗斯在心里这样盘算着,不禁喜上眉梢。虽然他不会告诉别人,但他确实准备暗中凭借拿破仑·乔塔斯的才能来为自己的被告打赢这场官司。
正当弗雷德里克·斯塔夫罗斯在他那昏暗破旧的办公室埋头苦干时,拿破仑·乔塔斯正在雅典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科隆纳其区的豪华别墅里参加一场隆重的晚宴。乔塔斯身材瘦削,一脸皱纹,一双猎犬式的大眼睛透着机敏,夹杂着些许戚伤。他那温和的让人琢磨不透的言谈举止背后隐藏着他过人的智慧和犀利的洞察力。乔塔斯坐在那里,用刀叉拨弄着盘中的甜点,思考着明天就要开始的这场审判。那天晚上,大家的闲谈大都围绕着这场即将举行的审判,讨论都是点到为止。客人们十分谨慎,没有直截了当地向乔塔斯提出审判的相关问题。晚宴快要结束了,大家都在畅饮茴香酒和白兰地酒,这时女主人问他道:“和我们讲讲,你觉得他们有罪吗?”
乔塔斯一脸无辜的样子,回答道:“他们怎么会有罪?其中一位可是我的委托人啊。”他说完话,大家都笑了,认可了他的回答。
“诺艾尔·佩奇的性格品行到底怎么样?”
乔塔斯一时拿不准该怎么说。“她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女人。”他十分注意自己的措辞,“她很漂亮,很有才华……”说着说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愿意对诺艾尔评头论足,她的一切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几个月前,他还只是粗略地知道她是个十分迷人的演员,她妖娆的身影常出现在杂志的八卦专栏里,她美艳的照片常被刊登在电影杂志的封面上。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的照片,他对所有女演员都怀有那种冷漠和蔑视,所以印象中她不过是个花瓶而已。但是,天哪,他大错特错了!自从与诺艾尔见面以来,他就情不自禁、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为了诺艾尔·佩奇,他打破了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绝不和客户产生任何情感纠葛。那天下午他同意担任她的辩护律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时他正收拾着行李,准备和他的情人一起去巴黎和伦敦度假三周。他从来没想过能有什么东西让他的旅行计划泡汤。但仅仅听到一个名字,就让他的计划泡汤了。他回想着当时的情景:他的管家走进他的卧室,将电话递给他,说了一个名字——康斯坦丁·德米里斯。
康斯坦丁·德米里斯有一座很私密的岛屿。除了直升机和游艇外,你找不到别的方法进入这座岛屿。岛上的机场和私人港口,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带枪的警卫带着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在巡逻。这座岛屿是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的私人王国,没有人可以擅自闯入。多年来,来岛的访客包括国王和王后、总统和前总统、电影明星、歌剧演员、著名作家和画家。他们离开时,都对这座岛称赞不已。康斯坦丁·德米里斯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巨富,也是世界上极有权势的人之一。他有自己独特的品位和处事风格,深谙金钱可以给他带来美好的一切。
在装修精美的书房里,德米里斯悠然自得地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吸着为他配制的板状埃及香烟,琢磨着明天早上的公开审判。几个月来,媒体一直想采访他,但他基本都躲掉了。情妇因谋杀罪被捕这件事本身对他的打击已经够大了,更何况他的名字也被卷入这场官司,哪怕这种牵连不那么直接。接受任何采访无异于火上浇油,他必须拒绝采访。他在想,诺艾尔此刻在圣尼科德莫斯街监狱里的感受如何?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对她将要面临的考验,她是否恐慌?他想起了他与拿破仑·乔塔斯的上一次谈话。他表达了对乔塔斯律师的信任,相信乔塔斯不会辜负他。但同时,德米里斯也让乔塔斯感觉到,对德米里斯来说,诺艾尔是否有罪并不重要。康斯坦丁·德米里斯向乔塔斯支付了巨额的辩护费用,要乔塔斯保证他所付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为诺艾尔辩护。就这一点来讲,他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审判肯定会顺利进行的。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的记性很好,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他记得凯瑟琳·道格拉斯最喜欢的花是希腊玫瑰。他伸手从桌上拿起一个记事本,写道:“希腊玫瑰:凯瑟琳·道格拉斯。”
为凯瑟琳做这点小事,相比他的计划来说,真是微不足道。
注释:
[1]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093公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