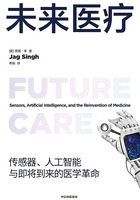
第3章 序言
阳光透过大大的、未被遮挡的窗户洒进来,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已经非常熟悉的房间。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前有一个发灰的木柜和一台方形的电视机,左边是那扇窗户,一张有些褪色的沙发侧对着我的病床。病床两侧是两个钢制的输液架:一个安装了平板电脑(iPad),方便我与护士沟通;另一个则挂着我的药物和注射液。我努力转过头去,可以看到显示心率、血氧饱和度和血压的监护器。这里已经变成我所称为“家”的地方。此时是2020年的3月初。这是疫情初期,人们面对疫情显得手足无措——没有经过批准的药物,也没有明确的治疗指南,我们无法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应对之道,我们拥有的大多是猜测。
我是被送进急诊科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由于血氧饱和度下降,胸部X线检查和计算机断层成像扫描(CT)的结果也很糟糕,医生立刻决定将我转入重症监护室。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可能会被派上用场的呼吸机,随着血氧水平恢复稳定,我被转移到医院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收治病区。医生告诉我,我会失去嗅觉。他这么说其实并不准确,与其说我闻不到任何气味,不如说我被一种腐烂的刺鼻气味淹没,这种气味每时每刻都在困扰我。我一直被提醒,病毒已经寄生在鼻咽部,并开始控制我的身体。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我整日发高烧,浑身都被疼痛深深地笼罩。每次照镜子,我都可以看到这场病对我的摧残。我瘦了将近7千克,衣服挂在瘦弱的身体上,显得松松垮垮。咳嗽仍在持续,血氧水平也总是令我担心,游离在随时可能需要供氧的边缘。夹在手指上的血氧饱和度监测仪显示的数值通常在90左右。当它偶尔降到80左右时,我会尽我所能保持深呼吸,并挣扎着从床上站起来扩胸。我不希望护士看到那些低数值,因为我不想再回到重症监护室。
凭借医学背景,我能够较为清晰地评估自己的状况。我的双肺都受到了侵袭。我知道,一旦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就意味着病毒正在占据上风。面对55岁的自己,我已经为可能发生的不良结局做好了心理准备。糟糕的疫情报告从法国和意大利传来,用上呼吸机的患者很难恢复自主呼吸,而且许多人因此过早地离世。我很庆幸的一点是,我在重症监护室待的时间很短,没有用到呼吸机,但我深知自己的状况并不乐观。
这真的让我很沮丧。我想不明白,除了患有糖尿病,其他时候我一直很健康,而且糖尿病是可以通过饮食和锻炼控制的。我从未住过院,30多年来诊治病人期间,我从未请过一天假。我并不意外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作为医生,我认为这是职业风险所在。我知道感染这种病毒并不受患者的年龄、性别、种族或其他人口特征影响,也不受他们过去健康状况的限制,所以即便感染了,也在意料之中。但真正震撼我的,是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导致我必须住院。我原本以为如果感染了这种病毒,以我的身体状况可以充分应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在的病房禁止探望,所以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非常感激我的家人以及使我们能够面对面交流的技术。家人每天都会鼓励我,提醒我他们对我的爱。虽然我通常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我觉得自己很脆弱,需要情感的支撑。每次与家人视频通话时,我发现自己除了简单的回应或者摇摇头之外,无法说出其他话,因为我害怕声音会暴露内心的无助。我常常在忍不住要哭的时候突然挂断电话。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面庞仍然是那么好,他们的电话帮助我集中精力努力康复。
我能走的最远的距离,就是到盥洗室的六步路。每走完一趟,都前所未有地感到呼吸困难。对于呼吸时的绝望和挣扎,我只能形容为在全速奔跑时只通过一根吸管呼吸。如此微量的运动就导致呼吸困难,仅此一点就令人感到不安。持续咳嗽和不稳定的体温消耗了储备的体力,我很快便体重大减,肌肉流失严重。让我震惊的是,我现在能够用两只手轻松地环抱住自己的大腿。我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被重新送回重症监护室的恐惧挥之不去,我知道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因为我已经签了同意书,如果主治医师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将接受紧急插管术、呼吸机辅助和血流动力学监测。尽管身体十分疲惫,我仍决定按照护士的指导,用诱发性肺量计进行肺部锻炼。这个仪器就放在我的床头,我本想对着这个仪器深深地呼气,但经常因为咳嗽而不得不停下来。
在病区,我时常被其他病房传来的咳嗽声打扰。从他们的咳嗽声和病房外紧张忙碌的声音中,我可以判断病友们身体状况是否在恶化。每当鼓起勇气询问他们的状况时,我往往被告知他们已被转入重症监护室,需要接受插管术治疗,并且使用呼吸机来辅助呼吸。
我感到非常孤独。我不仅与家人隔离,还与病区的其他病人分隔。前来为我量体温的医护人员戴着口罩、身穿防护服,我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脸,更别说辨认出每天是不是同一位护士来照顾我。我感觉我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不可能在其他场合认出来病房的任何一个人。尽管这样,在那段特殊时期,我仍然非常珍惜与他们的每一次接触。医生和护士的探视是我与外界唯一的面对面接触,哪怕时间短暂且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探视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少,最后都变成了视频通话。每当床边输液架上的iPad响起,我便知道又到了快速视频检查时间。看起来,即使在医院内部,医疗护理也在逐渐转为远程服务。一开始,我对此感到不适。但越想越明白,视频检查可以避免医护人员不必要的接触和潜在的感染风险。而实际上,医疗团队能为我提供的治疗并不多,更多的是缓解症状。我们都在等待,看到底是病毒胜出,还是人类胜出。
在病区最初的7天,我的数据都不容乐观。到了第8天,当iPad响起时,我看到医生正对着摄像头微笑。她告诉我血液检查结果很好,那些最让我们担忧的指标已经开始下降。她已经查看了病房外显示器上我的心率、血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等数据。她认为我已经可以回家了。她还提到,医院正在接收越来越多的患者,病床已经开始紧张。
或许是察觉到我对于自身病情的突然转变感到困惑,医生安慰我说,我的生命体征和临床病程都可以远程评估。由于近年来远程医疗的进步,我可以在家里得到有效且快速的治疗。她向我介绍了我将在家里使用的各种工具和传感器,以便在卧室就能测量体温、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头晕使我感到不适。虽然我生病已超过3周,但距离疫情刚刚暴发没多久。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我短暂住院期间,远程医疗设施和人们对它的依赖都在快速增长。当时就能看出,尽管这种变化因当下需求而生,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医疗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