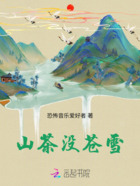
第22章 再出戏
祭祀礼成,不过三两时辰。
素白衣裳的人却都是个个谨慎,心中计策万千回转。
众人皆知,云川和岱渊闹掰,此桥之祭定会不平。
欲求战火以积家业的,必定两边联合,为钱财齐齐背弃礼教。
欲稳固自己权财地位的,必定上下勾结,营私着为非作歹。
而这盘棋,多少人为财、多少人为利、多少人为权,一一都将在祭祀后的春日宴上分明。
出人意料,祭典却一切照常,未有任何纰漏。
素衣人又依次退下,在山脚营地换了布衣。
齐齐隐瞒身份,步行入林,向林中乡野猎户讨教。
比较谁在夜幕降临前,除却自己身份地位后,以平凡人劳作带会的菜食多。
此之谓:“寻露食。”
叶芫自是将局子布好,就等着逐着利益气味寻食的蝼蚁跌进蜜罐里。
蝼蚁们最欲得的蜜糖。
是留给贪污腐败的人的最后大饼,也是留给清醒者们行动的讯息。
祥和,福瑞,寻鹿山。
大山河作围,小人儿计局。
幽幽咽咽,林间影婆娑。叶芫着褐色布衣,一切华丽的去了,气度却仍可见不凡。
依照惯例,马被人牵走,侍从留营帐。
叶芫脚步不稳地行在落叶堆上,偶踩着朽枝,惊飞鸟雀,扑腾俩声后,林中寂静更盛。
内力极强,曾不知有人跟随?
此时,三步远的树后,凌司尘正缓着乱拍的心跳,五丈遥的岩后,练家子屏息待命。
翠叶摞,风起墨发,光依稀,衬人出尘。
布衣简,步似风中莲,宛宛,柔比青青柳。
哨音起,促短刺耳,却只一瞬。
心跳声太吵,藏匿者忙慌,未有所觉。
心跳杂乱,手中炙烫,似只触及他才止得。
风息,光没叶重重,人影闪;
风起,暖意破雾瘴,刀剑急。
凌司尘还躲在树后,在乱拍的心跳里犹犹豫豫。
是否要向人问好?
是商量着同行还是偷偷帮助?
全然未觉身后潜伏着蠢蠢欲动的杀机。
“嗯,呆鹅。”
叶芫听着暗箭破空,心中如是想着。
轻功运,五息轻,足点叶尖。
极快地。
褐色融入林叶阴影里,提起呆鹅。转袖间,毒针四射。
只听风速突急了瞬。
刀剑叮当就落了一地。又惊起归巢鸟离了家,愤怒地死在了凌思远和假扮猎户的侍卫长弓下。
“那边可是有事?”
凌思远一脸懵,呆呆的地转头,疑惑的表情随着话语微有波动,看得侍卫长格外无语。
俩人寻声而前,只见林间枝头横穿了许多黑布,一条条挂在光影交错里,像极躲在水里的游鱼。
随光影而动,隐匿身形,伺机而动,一击必杀。
可惜,这一击未能出。
叶芫运息拈那风中落叶,玉指葱葱,内力一送。
只见漫天飞叶里,有颤落如蝶,有急锋似刃。
褐衣人只只回头一望,那空茫而深邃黝黑的眸就摄了刺客的魄。
个个慌不择路,衣服刮树,人摔入崖只是寻常。
凌司尘本还忧心林中忽有急风,恐有人潜行刺杀,忙不迭想寻叶芫,自己来好好护着。
不曾想,这人竟有这般身手!
那次坠崖的红绸定也是他自护的工具。
真是稀奇。
侍卫长那般魁梧的汉子都能被他从崖边成功提起,真真厉害,可怎又如此体弱?
叶落,影移,遮住叶芫晦涩不明的神情,那双深邃夺魄的眸,和沾着血微微勾起的嘴角。
褐衣袖动,凌司尘下意识扯住,一把牵人入怀,抱得叶芫猝不及防,袖中流云剑险些脱鞘伤人。
凌司尘立在微小罅隙投下的光束里,叶芫瘦弱的身躯被紧紧抱住,从暗影里走出,来带光中。
温暖,满足,惬意,安然。
大抵存在神明的赌注,这一拥抱竟在微风带起的光影交错里显得格外合理。
静默,从对方的身上嗅到别人不曾拥有的味道。
奇特,心中繁杂全然退却,只余一缕心魂追着那味道,心脏也随对方的呼吸频率急增而颤动不止。
耳朵尖渐渐红了,从春三月的花到冬日红梅,大抵有过象征。
一次困于少年初春懵懂里的共白头。
十年后,你还会记得他也曾如此明媚吗?
大抵不会吧。
毕竟,你都觉得这岱渊的皇城入冬就冷的紧。
是父皇的死、是幼妹的和亲,还是北郊的白山茶开了,你母后在其间安详的仪容?
不清。
难懂。
终以南门外的红梅做节,以北郊的白山茶为序,渡这心上人的未归魂。
风起,心动难止。
匆匆赶到的凌思远和侍卫长站在阴影里,所思各异。
“啊?这处怕是有遇刺客,叶芫不会遇险受伤吧。”
凌思远步伐随风,步步踩在光暗分界线上,白净的小脸上尽是焦急。
侍卫长虽也向动静处寻,心中焦急万分,却仍是留意周围环境。
一步一步及其谨慎,以至全身都隐在暗中,短打的藏青色猎户服也极好的帮他隐匿。
暗夜里的怪物可得光明救赎?
大抵是吧。
若怪物在暗影里不曾想过囚禁流动的光,这光大抵是会救赎它的。
树上零星挂着黑色线头和布条,若非路过的风牵起一角树叶,这些物品还不由得见。
“究竟是杀谁的刺客?难道又是那小公子出的手?这般厉害,曾会回宫就病倒?”
侍卫长想的出神,直直越过了凌思远。
不顾礼仪。
本也不用顾忌,身边这个小屁孩看得出来?
凌思远看着侍卫长熟悉的背影,心中暗叹:
“啧,我在你眼中就是傻子一个?好好的侍卫服不穿,非穿这款式像极的衣服潜伏,以为贴个胡子就没人认识了。骗谁呢!”
手指攥紧,隐隐发紫。
“该死的奴才,这人是什么身份?你竟还敢惦记!真是皮痒了哈。”
凌思远突就挂上了更无害灿烂的笑容,装作若无其事,急急追上前者步伐。
藏青与褐紫明暗中闪烁,偶掠树梢,沙沙声在寂静的林中格外引人注目。
叶芫终是缓过神来,挣扎着从凌司尘的怀里出来,却仍是慢了。
光下,树间,光斑错杂,人却立在灿阳里,相拥坦诚,嬉笑打闹。
叫人好不羡慕。
凌思远和侍卫长如是想着,脸上不多的假笑都齐齐收拢。
站在暗影里,死盯着前方光中动静。
而叶芫几经挣扎,竟被凌司尘越抱越紧,用着蹩脚的轻功飞了一段,直直落在了最高的树冠,再不敢动弹半分。
前是高崖,后是陡树,水逆不是?
树高极,冠却平极,随便人躺坐。叶芫被放下,稳稳的坐在了最高处。
山风不及触,都懒懒地绕在了数干,缓缓散却。只余树叶沙沙作响。
叶芫提着的心暂且放下半点,极快地瞥眼在略低处偷乐的人,兴趣起,心中思索缓停。
“怪哉,我救你,你倒还倒贴我,拐人到此处,方便我综观全局吗?”
再偷瞟眼,不知不觉间出了神,眸子就钉在别人身上,丝毫不觉。
这般动作让自己在凌司尘的眼中究竟多么可爱俏皮,像极那软萌的兔子,温柔可亲,又极能防御。
手不自觉揉上叶芫的发,两人都是一怔,缓过了神来。
手回袖中,反反复复搓揉着,重温那柔顺与奇异感觉。
叶芫重将眸子转向林中。局做在西北,靠近福瑞的凌昆营帐。
光寸寸移,打到一顶不起眼的轿上,帘帐被一白玉镶金扇柄挑起,露出林瑄的眉眼。
带笑的,嗜血的嗤笑,在他极普通的脸上显得奇怪,周围侍卫却个个低头无言。
嗯。无人敢言。
谁让这主子在青楼逛从不泄露消息?问如何。
杀之,剥皮。
食之,汆水。
而福瑞桥另一端,林辉用西洋镜看着自家长子的举动,心绪复杂。
若是设局,血缘究竟能弃?
叹人局落人头落,观生死如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