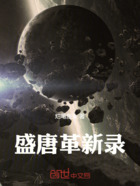
第12章 齿轮迷局
永徽三年秋分,国子监的演武场被晨雾笼罩,青铜铸就的浑天仪在雾中若隐若现,十二根蟠龙柱上的齿轮纹与神机监的标志遥相呼应。明工科的首次殿试即将在此举行,三十六名来自天下的匠人考生已在丹墀下列队,腰间统一佩戴着青铜齿轮形的准考证,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林砚之站在观礼台上,手中捧着李治亲赐的“格物致知”玉圭,目光扫过考生们携带的各式器械:有人背着竹制的龙骨水车模型,有人抱着裹着橡胶膜的青铜纺轮,最显眼的是来自杭州的年轻匠人沈括,他的木车上载着一台半人高的织布机,齿轮组在晨风中轻轻转动,发出细碎的“咔嗒”声。
“诸位考生,”他的声音通过青铜传声筒传遍全场,“今日殿试分两轮:首轮考‘器用之实’,需现场改良国子监的旧织机;次轮考‘格物之思’,论‘科技与民生之辨’。”他抬手示意,八名宫娥推出现场准备的老旧织机,木架上的经线早已纠缠如麻,“开始吧。”
沈括是第一个动手的。他绕着织机踱步,忽然蹲下身,从袖中取出片薄如蝉翼的橡胶垫,垫在齿轮咬合处:“旧织机的噪声源自齿轮间隙过大,橡胶可缓冲震动。”他又取出微型铜锤,在齿轮边缘敲出细密的齿纹,“每寸十六齿,与长安城的标准齿轮同径,日后更换无需定制。”
其他考生纷纷效仿,有人用硝石溶液淬火加固木轴,有人用琉璃镜反射阳光照亮经线。林砚之注意到一名来自岭南的陶匠,竟在织机的踏板处安装了小型的“神火加热器”,用微量火剂保持踏板干燥,防止南方潮气导致的木材变形。
“好个‘防潮踏’!”韦弘机在旁赞叹,“若推广至江南,织户每年可省三成损帛。”他忽然压低声音,“不过洛阳传来消息,长孙祥买通了三名监考博士,试图在论辩环节刁难考生。”
与此同时,洛阳的关陇贵族府邸内,长孙祥正对着铜镜整理衣冠,袖口藏着的毒针在晨光中泛着青芒。桌上摆着伪造的“考生密信”,信中用墨门古字写着“九月初九,炸毀太极宫”,落款处盖着沈括的私印——那是他花高价从黑市购得的匠人印记。
“大人,”管家低声禀报,“已买通国子监的直讲官,他们会在论辩时提出‘匠人乱政’之问。”长孙祥点头,目光落在墙上的地图,陇右道的地道入口被红笔圈住,“告诉突厥狼卫,只要明工科停摆,地道工程便可重启。”
长安演武场,首轮考核接近尾声。沈括的织机已能流畅运转,改良后的齿轮组将织布效率提升了一倍,更妙的是他在机尾安装了“误差校正器”——用磁石与铜球制成的平衡装置,能自动调整纬线的松紧。
“沈括,”林砚之亲自检查织机,“为何不用全青铜齿轮,却保留木架?”
“回监丞,”沈括抱拳,袖口露出绣着“工”字的内衬,“木架取松木之轻,青铜齿轮取坚韧,橡胶垫取缓冲,三者结合方为‘器用之道’。”他忽然从怀中掏出小册,“小人还记了《织机改良十则》,愿献与神机监。”
林砚之翻开册子,工整的小楷记录着齿轮模数、橡胶配比、应力计算,其中“以齿轮定尺寸,以模数通天下”的观点让他眼前一亮:“此乃‘标准化’雏形,可记于《天工开物补遗》。”
次轮论辩在正午开始。当沈括面对“匠人入仕是否乱了四民之序”的诘问时,他指向演武场角落的神火路灯:“昔年大禹治水,凿龙门、疏九河,何尝不是匠人之事?如今明工科考生,不过是继大禹之术,解百姓之难。”他举起手中的橡胶水囊,“此物能让长安百姓雨季不湿鞋,难道不是比空谈义理更有裨益?”
场下传来掌声,却被突然闯入的金吾卫打断。一名校尉跪地禀报:“监丞,东市发现考生密信,欲在重阳佳节行刺陛下!”林砚之接过密信,扫过内容便知是伪造,却在看到落款时心中一沉——沈括的印鉴虽真,字迹却带着西北狼毫的刚硬,与他江南软笔的文风迥异。
“沈括,你可知罪?”直讲官孔颖达趁机发难,“私通突厥,图谋不轨!”
沈括却不慌乱:“大人,此信墨色泛青,是用陇右道的石绿墨所写,而小人所用墨锭,产自徽州松烟。”他取出自己的笔砚,“且信中‘器械’二字写作‘器诫’,乃突厥语发音之误,我大唐匠人,岂会犯此错?”
林砚之暗自点头,沈括的辩解暗合墨门“察色辨伪”之术。他转向金吾卫:“去查陇右道的墨商,近期谁买过石绿墨。”又对孔颖达拱手,“诸位若疑考生,不妨考校他们的‘格物之思’——真匠人,必懂细节。”
论辩结束时,暮色已染透国子监的飞檐。林砚之刚要离场,却见沈括被一群胡商围住,他们指着他的织机模型,用粟特语兴奋地交谈。“沈先生,”一名波斯商人操着生硬的汉语,“我愿出百金,买这织机的图纸。”
“不可。”林砚之出言阻止,却见沈括摇头:“图纸可送,但有二愿:一愿此机传入波斯,助织妇减轻辛劳;二愿波斯匠人回赠琉璃工坊的‘吹制七法’。”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匠人之道,本应互通有无。”
是夜,神机监的密道内,杜挽月正在分析密信的纸张纤维:“纸浆中混有胡麻纤维,是突厥狼卫惯用的造纸术。”她忽然抬头,“更重要的是,信中提到的‘九月初九’,正是终南山地宫的‘地动仪重置日’,暗火同盟想趁核心调试时发动袭击。”
林砚之望向墙上的《长安防御图》,四门的声波屏障、地宫的蒸汽核心、明工科的考场,构成一个精密的齿轮系统。他忽然想起沈括的“标准化”理念,取出青铜模具,开始设计“通用齿轮组”——这种齿轮可用于织机、弩炮、水车上,让匠人无需重复制造。
“哥,”砚礼抱着新制的“应力感应甲”闯入,甲胄表面的青铜鳞片能随震动频率开合,“沈括帮我改良了感应装置,现在能提前一刻察觉地下十米的挖掘声。”少年的脸上带着兴奋,“他还说,想看看地宫的永动核心。”
洛阳,长孙祥的书房内,烛火突然被风吹灭。当他点燃油灯,发现书桌上多了封匿名信,牛皮纸上印着清晰的齿轮纹,内容只有一行小字:“九月初九,地道无水。”他脸色骤变,想起陇右道的地道依赖地下水冷却,若无水,挖掘队将被地热蒸熟。
“大人,突厥传来急报!”管家冲进房,“地道突然涌出沸水,三十名狼卫被烫死!”长孙祥握紧信纸,齿轮纹在油灯下泛着冷光,他忽然想起白天收到的密报——明工科考生中,有人改良了“地热能引流术”。
九月初九,重阳节。长安太极宫的重阳宴上,李治举起沈括改良的琉璃酒盏,酒液在齿轮形的盏底折射出七彩光芒。“沈卿,”皇帝笑道,“听说你改良了织机,可曾想过改良朕的舆图?”
沈括跪地,呈上一卷《天下水利图》:“陛下,小人用齿轮联动原理,制出‘自动测绘仪’,可随马车行进自动绘制地形图,误差不过半寸。”
宴后,林砚之带沈括来到神机监的地下工坊,揭开覆盖在“蒸汽测绘车”上的油布。青铜车身布满齿轮与刻度,车顶的磁针随方位转动,带动车内的羊皮纸自动展开。“此车若行于陇右,”林砚之轻声道,“暗火同盟的地道将无所遁形。”
沈括的眼中闪过震撼,忽然从怀中掏出另一本册子,封面写着《梦溪笔谈》:“监丞,小人愿将所见所闻记于此,让后世匠人皆知,科技非奇技淫巧,乃强国之本。”
深夜,终南山地宫,林砚之独自来到永动核心室。齿轮的轰鸣中,他忽然听见细微的摩擦声——那是应力感应甲的预警。他望向核心底部,那里静静躺着白天收到的礼物:沈括亲手制作的“齿轮镇纸”,底座刻着“格物致知,匠心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