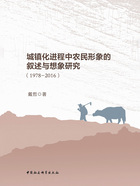
第一章 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一种对生活和世界的总体性想象
随着1947年中共颁布了《土地法大纲》,中国的乡村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每个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但与此同时,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土地的自由流动,很可能造成新的土地兼并,当时的文学也对这一问题有所察觉,并将其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李准《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农民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想象来自对地主生活方式的模仿。如此一来,原来乡村共同体中相互扶助的风气开始减弱。那么,当土地改革使每个农民都分到自己的土地,谁才是土地改革最大的受益者?赵树理极具前瞻性地在当时的写作中分别对此进行了思考,比如《邪不压正》和《三里湾》。在他看来,土地改革最大的得益者应当是干部,因为干部可以相对多地分到好地,同时他们又掌握着权力,那么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压迫性集团。无疑,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叙述和思考,这在后来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以及本章即将讨论的冯幺爸的《乡场上》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50年代便开始实行了合作化运动,于是就有了类似柳青《创业史》这样的作品。柳青在“题叙”中告诉我们,梁生宝母子逃荒、梁三老汉重组家庭、三代人创立家业不仅没有成功,还遭遇了破产,而“土改”使梁三老汉又有了创家立业的理想。而与此同时,梁生宝却热衷于集体事业。故事最后告诉我们,只有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互助组组长梁生宝,才能够成功创业,创的是集体的业,也只有集体化的生产模式,才能让梁三老汉,以及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走出千百年贫穷的死循环。由此,这样的文学叙述为集体化确立了合法性,《创业史》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经典作品。
这样的一种关于集体化的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了中断。然而有意思的是,80年代的逻辑起点,却重新回到了“土改”后被合作化打断的历史。具体而言,由1946年“土改”所带来的分田到户、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重新成为80年代对于农民及其生活的想象。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地前进着。1978年,中国再次开始实行乡村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都可以分到土地,每个农民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回土改的模式,曾经强烈存在却又被压抑和中断的小生产者的梦想再次复活。换言之,中国现代历史上两次现代化的转型——1949年和1980年——其动力都来自小生产者的梦想,都是回到土地单干,自给自足。正如薛暮桥在回忆录中说,“从根本上说,土地毕竟是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辈梦寐以求的,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土地,他们愿意有一段时间发展小农经济是自然的。取消封建制度,发展小农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说明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需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1]虽然经济学家薛暮桥这段话针对的是第一次土地改革以及合作化,但是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于解释80年代初期农民对于土地改革的热情。与此同时,某种意义上集体化叙事的中断,也进一步突出了合作化运动时期“集体劳动”的危机和问题,“集体劳动一方面在生产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在同时生产个人主义,最后,当集体劳动在现实中受挫,这一记忆以及记忆的叙述,就会对这一生产方式提出终结的要求”。[2]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指对土地的情感,更包括了个人发家致富、光耀门楣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更存在于农民的血液之中,所以梁三老汉才一直抱有“创业”的美好梦想和对富裕中农生活的向往。
毫无疑问,文学也参与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变化中来,从而有力地介入到了改革之中,所以我们会看到,文学写作从伤痕文学(如刘心武《班主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迅速转到对乡村和农民的书写,从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否定,开始转化为对未来生活的新的想象。显然,农村改革为这种新的想象提供了文学实践的空间。正如1949年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上两次现代化转型的动力都来自小生产者的梦想,在80年代早期的文学叙述中,也同样塑造了一系列的“小生产者”的农民形象,围绕这些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文学写作者展开了对乡村的未来的想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对这些农民形象所展开的叙述,呈现了曾经被中断的历史如何成为80年代逻辑的起点。具体而言,本章将柳青的《创业史》作为文本,首先对集体化叙事以及相关的农民形象展开论述,从而呈现土地改革运动如何被集体化运动中断,集体劳动如何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以此作为80年代关于“小生产者”叙述的前史,重点展开对80年代早期农民形象的探究。对于80年代“小生产者”及其叙述的讨论则针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乡场上》这三个经典文本,围绕“饥饿”“财产”“尊严”这三个符号展开,力图呈现集体化如何遭遇了文学叙述的解构,以及乡村改革/包产到户如何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个人劳动的正当性在这一过程中又如何被确立。实际上,这三个符号不仅在80年代关于农民的文学叙述中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农民的文学叙述中都多次被征用,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和政治语境之下,其被征用的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需要强调的是,写作者对于“小生产者”的想象,不只是从经济层面出发,还指向了政治层面,其中包含着某种“正义”的理念,是一种对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想象。因此,80年代初期关于“小生产者”的叙述与想象饱含力量,经由“小生产者”所形成的乡村世界也同样极为完满,仿佛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当然,这样的农民形象与乡村想象,其内在包含着自身的矛盾。可恰恰因为如此,重新审视“小生产者”形象成为后来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以来的农民形象及其带来的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