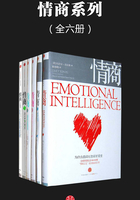
第五章
为什么会有一见钟情
一对夫妻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接吻时的情景,那是他们关系转变的里程碑。
他们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一天下午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们都感慨找个合适的伴侣太难了。说到这里,他们停了下来,凝视着对方,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两秒钟。
然后,当他们走到外面打算分手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突然,他们感觉好像有种神奇的力量使他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
他们都说自己并没有打算接吻,但是直到几年之后他们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不由自主的浪漫举动。
他们之间长时间的凝视可能是促成这个吻的必要前奏。诗人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就是说通过眼睛人们可以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神经学对眼睛的看法也与此类似。说得具体一点,眼睛的投射可以直接反映到大脑中负责同理心的部位——前额叶皮层中的眶额区域。
四目相视会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间形成回路。让我们用神经学来分析一下这个浪漫时刻吧。当两个人目光相会时,他们的眶额区域会紧密联系,这一区域对于眼神交流等暗示特别敏感。这些负责社交的神经通道对于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连接大脑皮层与下皮层的眶额皮层也是大路神经系统和小路神经系统的交汇点,因此也是处理社交活动的中心。我们内心的思想与情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在这里进行交流,因此眶额皮层相当于一个高速的社交计算器,告诉我们自己对交流对象的感觉、交流对象对我们的感觉以及如何应对他们的反应等。
机智、和谐、流畅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一神经系统。比如,眶额皮层中的神经细胞可以帮助我们察觉别人的面部表情,或者根据别人的语气来推测他们的情感,并且可以把这些信息与我们的内心思想相结合来进行判断。比如在本章开头的故事中,两位主人公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都感觉到对彼此有好感。
这些神经系统还能够反映出哪些人或事物是我们最关注的。比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的研究显示,当新生儿的母亲看到自己宝宝的照片时,她们的眶额皮层会被激活,而看到别的宝宝时却没有多大反应。而且她们的眶额皮层越是活跃,她们就越是慈爱、温柔。
用专业术语来说,眶额皮层赋予了我们对于社交生活的“享乐主义价值观”,让我们知道我们喜欢谁、厌恶谁、崇拜谁。因此,它也是人们接吻时神经活动的关键所在。
眶额皮层还会决定我们的社交审美,比如我们是否喜欢某个人的气味等。人体的气味是能够唤起人们强烈的喜爱或者厌恶感觉的最初信号。我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爱上一个女人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喜欢她的味道。
甚至在我们的理性思维感知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的涌动时,这些潜意识的情感就已经开始指挥我们的行动了。这就是那个不由自主的吻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一见钟情的魔力
下面是我认识的一位教授选择助手的经历,选择一名好的助手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助手是他在工作时间中接触最多的人。
“我走进接待室的时候她正好坐在那里,看到她后我立刻感觉自己放松了下来。从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当然随后我也看了她的简历和其他资料,但是从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自己肯定会请她来工作,而且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因此而有过一丝后悔。”
凭直觉判断我们是否喜欢某个初次见面的人也就是在推测我们是否能与其建立和谐关系,或者至少顺利相处下去。但是在潜在朋友、商业伙伴或者配偶中,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究竟是亲近还是疏远他们的呢?
这个过程中的大部分决定似乎都是在人们初次见面时的最初几分钟内作出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班级的大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只用了3~10分钟的时间来熟悉某位同学——当时的陌生人。随即他们会对同学们进行衡量,决定哪些同学可以发展为自己的亲密朋友,哪些只能作为点头之交。9个星期之后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第一印象所决定的好恶与后来大家的实际交往情况相当吻合。
在作出类似瞬间反应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一组非同寻常的神经细胞:形状类似于纺锤的大脑细胞。神经学家们猜测,纺锤形细胞就是这种快速社交直觉的奥秘所在,是它们决定了判断的高速度。
许多神经解剖学家猜测,这种纺锤形细胞很可能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所在。与人类最为相似的灵长类动物(比如猿类)的大脑中该类神经细胞的数量只有几百个,人类大脑中该类神经细胞的数量比它们要高出1 000多倍,而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中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类细胞。一些科学家推测,纺锤形细胞还可能是某些人(或者灵长类动物)社交意识或者社交敏感性强于其他人(或者灵长类动物)的原因所在。大脑成像研究发现,社交意识较强的人,也就是那些不仅可以审时度势,而且在社交场合中可以感知他人感受的人的前扣带皮层的活动都异常活跃。
纺锤形细胞集中的眶额皮层中有一个区域在我们需要对别人作出情感回应,特别是产生原始同理心的时候会被激活。对大脑进行的扫描显示,当一位母亲听到自己宝宝的哭声,或者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所爱之人的痛苦时,这一区域就会被激活。在我们看到自己所爱之人的照片,或者发现一位迷人的对象,或者判断我们是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等情绪大幅波动的时候,这一区域也会被激活。
另外一个存在大量纺锤形细胞的区域是前扣带皮层,这一区域在社交活动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指导我们展示及识别面部表情,并会在我们产生强烈情绪时被激活。这个区域与杏仁核有着密切关联,而杏仁核正是许多强烈情绪的触发点,同时也是我们最初的情绪判断开始之处。
正是这些细胞决定了小路神经系统反应的快速。比如,甚至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察觉了什么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是否喜欢它。纺锤形细胞可以解释小路神经系统何以能够在我们确切知道感知对象为何物之前就判断出我们是否喜欢它。
这种瞬间判断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这些纺锤形细胞共同组成了我们的社交指导系统。
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亨利·詹姆斯的《金碗》(The Golden Bowl)一书中,新婚不久的女主角玛吉·沃尔弗去拜访居住在乡间长期鳏居的父亲,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在场,这些人中间似乎有一些女士对她的父亲颇感兴趣。
在对父亲的短暂一瞥中,玛吉突然意识到,为了抚养自己长大而一直清心寡欲的父亲现在已经打算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就在那时,父亲也从她的目光中明白虽然女儿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她已经了解了自己的心思。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父亲却有种“读懂女儿心思”的感觉。
在这个无声的对话中,“她的眼睛无法从他身上移开,她以自己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他们共同的心思”。
对于房间内这种相互间思想无声交流的详细描写占据了这本小说的开头几页。而且作者还详尽描写了在父亲再婚之后这种心有灵犀的无声交流所产生的余波。
亨利·詹姆斯所敏锐捕捉到的是我们通过感知对他人内心的洞察:瞬间的一个表情就能够使我们了解大量信息。这种社交判断的自发性是由于负责它的神经系统似乎一直处于“开启”状态,随时可以对周围的情况作出反应。即使其他的大脑区域都处于静止状态,有四类神经系统一直都在积极活动,就像是空转的神经发动机一样,随时可以迅速作出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类神经系统中有三类都涉及社交判断。当我们想到或者看到交流对象时,这些处于空转状态的神经系统的活性就会增强。
由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之一马尔科·亚科博尼和社会神经学的创立者马修·利伯曼所领导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对这些区域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大脑的默认活动,也就是在普通状态下大脑的自发活动,似乎一直在为社交活动而运转。
“人际敏感”神经系统的高新陈代谢率显示了社交世界对于大脑构造的特殊重要性。回忆我们的社交生活似乎是大脑空闲时最乐意进行的活动,就像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一样。事实上,只有当大脑处理非人际活动,比如结算支票本时,这些“人际”区域才会平静下来。
与此相反,对物体作出判断的大脑区域必须经过热身才能运转。这也是我们对于他人的判断在瞬间就能完成,而对周围物体的判断却需要一段时间的原因。在任何社交情景中,负责社交的神经区域都会被激活,它们会对周围的人进行评价,从而决定他们将来的关系,或者他们是否会有进一步的交往。
大脑中的系列活动就开始于这种初步的快速判断,它主要涉及扣带皮层以及通过纺锤形细胞与之相连的眶额皮层。这种小路神经系统会延伸到大脑的各个情感区域中。这一神经网络所产生的初步感觉,在大路神经系统的引导下可以发展成为意识性更强的反应,比如某个行为或者仅仅是心有灵犀的无声对话,就像玛吉与父亲那样。
眶额皮层–扣带回系统会在我们从多种选项中作出判断时活跃起来。这一系统会对我们感受到的一切事物进行评价、赋值,也就是喜欢或不喜欢,从而决定我们对事物意义的认识。虽然目前仍有争议,但这种情绪演算就是大脑用来组织我们行动的基本价值体系,在任何时候大脑都会据此决定我们行动的优先级。因此这种神经节点在我们作出社交决策(即我们经常作出的那些可能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与否的猜测)时至关重要。
想象一下在社交生活中大脑实现这一过程的惊人速度吧。在与陌生人相遇的时候,这些神经区域会在1/20秒的时间内对他们作出初步判断。
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反应了。一旦眶额皮层对于这种喜欢或者不喜欢作出判断,它对该区域神经活动的影响还会持续半秒钟。同时,前额叶皮层附近的神经系统会为大脑提供社交常识,对于该场合下的得体行为作出更加成熟的判断。
眶额皮层接收这些社交常识之后,会平衡人们的最初冲动(比如,离开这里)和最佳方式(找到一个可以被大家接受的理由离开)。眶额皮层的决定并不是经过对社交规则的有意识思考后进行的,而仅仅是通过一种“正确”的感觉进行的判断。
总之,眶额皮层可以在我们对他人产生初步印象之后指导我们的下一步行动。通过抑制最初的冲动,眶额皮层会指挥我们做出得体行为,至少可以阻止我们做出或者说出可能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或话语。
这个过程在任何社交活动中都会发生。我们最初的社交指导机制依赖于一系列模糊的情感倾向:如果我们喜欢某个人,它会指导我们的下一步社交活动;如果我们厌恶某个人,它就会指导我们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随着社交的深入,如果我们的情感发生了变化,社交大脑也会悄悄调整我们的言行。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在瞬间发生的过程,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社交生活的质量。
姐姐是个“偏执狂”
我所认识的一位女士曾经向我讲述了她姐姐的事情,她的姐姐由于某种精神疾病脾气变得特别暴躁。在她们亲密无间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姐姐就会变得极端敌对,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偏执狂”。
就像这位女士所描述的那样,“每次我亲近她的时候,她都会伤害我”。
因此她开始尽量躲避这种“情感攻击”,看到姐姐打来的未接电话时她并不会立刻回复,和姐姐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而且如果电话录音中姐姐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她就会等一两天再回电话,让姐姐冷静下来。
尽管如此,她仍然关心姐姐,并且希望姐妹间能够亲密无间。因此当她们在一起时如果姐姐发作的话,她就会提醒自己姐姐患有精神疾病,这样她就不会把姐姐的愤怒看做对自己的攻击了,她也因此避免了不良情绪的传染。
虽然情绪传染的自发性会使我们容易因为不良情绪而心情低落,但这仅仅是一系列生理过程的开始。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消除这种传染。在遭遇不良情绪的时候,这种心理策略可以让我们拉开与对方的心理距离,从而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小路神经系统的运行速度很快,就像打一个响指一样。但是我们并不一定受它的支配,如果小路神经系统的反应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话,大路神经系统就会运转起来保护我们。
大路神经系统为我们提供的其他选择大部分也是通过眶额皮层附近的神经系统来实现的。来往于小路神经系统中心的信息流使我们产生最初的情感反应,比如情绪传染等。同时,眶额皮层会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理性大脑,使它仔细衡量这一反应,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对周围情况进行详细考虑之后再作出一个更加成熟的决定。这两个平行的神经通道在人们的每次交往中都会活动,而眶额皮层就是它们之间的中转站。
小路神经系统就像我们的第六感一样,它使我们在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感受之前就与别人产生了同感。小路神经系统在没有外力干扰情况下所产生的情感状态是非常容易受到感染的,也就是说随时可能产生原始同理心。
与之相反,大路神经系统会在小路神经系统发生情感变化的时候有意识地关注我们的交流对象,以更好地了解当前的情形。这就使我们的理性大脑,特别是前额叶皮层活跃起来。这样,虽然小路神经系统非常容易受到传染,但是大路神经系统的反应却有许多其他可能性。在几毫秒之后大路神经系统的大部分神经系统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可能作出的反应就多了许多。
因此,尽管小路神经系统使我们的情感在瞬间贴近别人,但是大路神经系统却会产生更为复杂的社交意识,指挥我们作出更加得体的反应。这种灵活性的实现依赖于前额叶皮层——大脑的管理中心。
前额叶切除术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风靡一时的精神病疗法,它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切断眶额皮层与大脑其他区域的联系。虽然当时神经学家们还不十分清楚大脑中各个区域的具体功能,更不清楚眶额皮层的作用,但是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本极度狂躁不安的病人在接受手术后会平静下来。这对当时因为收留众多精神病患者而经常一片混乱的精神病院来说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虽然接受该手术的病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当时的科学家们还是发现了两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副作用”:病人的情绪变得没有任何起伏,甚至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情感,而且他们面对新的社交环境时完全无所适从。当然,现在神经学家们已经了解到这是因为眶额皮层协调着我们的情感与外部社交环境,告诉我们应对的措施。如果缺少了这一区域,人们面对新的社交环境就会不知所措。
你的大脑是如何作出非理性决定的
假设你和一个陌生人要分配10美元,由他提出方案,你来决定是否接受。如果陌生人提出给你2美元,你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还是接受这2美元比较划算。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这2美元,那个陌生人就会得到8美元。因此不管是否划算,大部分人都会对这种分配方案感到愤慨,而如果他只给你1美元,大部分人都会义愤填膺。
在这种被行为经济学家称为“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游戏中,人们的上述反应一次次得到了验证。在两人一组的游戏中,一个人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个决定是否接受。如果所有的方案都被拒绝的话,那么最终两个人什么都得不到。
在这个游戏中,如果一个人提出的方案中分配给他人的份额太少,那么就很有可能引发对方的愤怒。最后通牒博弈游戏经常被应用在对经济决策的模拟之中,而且在普林斯顿大学大脑、思维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科恩的倡导下,这种游戏还被应用在社会神经学的研究中。科恩的科研小组研究了进行这个游戏时参与双方的大脑活动情况。
科恩是神经经济学的先驱,这一领域主要分析促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决策的神经因素。在人们作出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大路神经系统和小路神经系统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一领域主要研究人们作出驱动经济市场运行的非理性决定时大脑的活动。
“如果一个人只给另外一个人1美元,”科恩说,“那么对方的反应很可能就是‘见鬼去吧’。但是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这种反应是非理性的,因为1美元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强。人们的这种反应使经济学家们不知所措,因为他们的理论认为人们总是会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实际上,人们有时甚至情愿放弃自己一个月的薪水,也不愿意接受不公平的方案。”
如果在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中人们只有一次提出分配方案的机会,那么份额过低的分配方案经常会引发对方的愤怒。但是如果他们有多次分配的机会,那么双方很可能通过讨价还价来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比较满意的协议。
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不仅仅是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对抗,它还是双方的大路神经系统与小路神经系统,也就是认知与情感之间激烈的拔河比赛。大路神经系统主要依赖大脑的理性中心——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眶额皮层位于前额叶皮层的底部,隔离着中脑的小路神经系统情感中心,比如杏仁核等。
通过观察大路神经系统与小路神经系统拉锯战中神经系统的活动,科恩分辨出了理性的前额叶皮层与作出“见鬼去吧”等草率决定的小路神经系统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活跃的小路神经系统是脑岛,它和杏仁核一样,会对一些强烈情绪有所反应。科恩进行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小路神经系统的反应越强烈,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游戏双方的决定就越缺乏理性。而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越活跃,他们的决定就会越平衡。
在《大脑的硫化》(The Vulcanization of the Brain)一文中,科恩集中探讨了大路神经系统的抽象神经活动与小路神经系统活动之间的平衡问题。大路神经系统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详细理性的思考,而小路神经系统则迅速形成初步的情感倾向。科恩认为,究竟哪一个系统能够占上风取决于前额叶皮层——理性的调节中心的力量。
在人类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前额叶皮层的体积是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前额叶皮层比人类的要小得多。和其他负责某个特定功能的大脑区域不同,前额叶皮层这个管理中心作出反应所需要的时间要稍长一些。但是和其他一些全能的大脑推动器一样,这一区域特别灵活,它所能胜任的工作要远远多于其他区域。
科恩对我说:“前额叶皮层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世界、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
尽管天才的人类在推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石油消费大户和石油战争,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过剩的卡路里,电子邮件和个人资料盗窃等,但是我们创造性的前额叶皮层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危险,就像当初它引发这些危险一样。许多危险和诱惑都来自小路神经系统在遇到大路神经系统所制造出来的机会时对于放纵和滥用的原始渴望。要安全地度过这些危险同样也需要依赖大路神经系统。
就像科恩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更轻易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糖和脂肪等,但是我们必须平衡自己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要达到这种平衡必须依靠前额叶皮层,它会对我们的冲动说“不”——比如阻止自己吃第二块巧克力蛋糕,或者抑制自己遭遇轻视后进行疯狂报复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大路神经系统就完全控制了小路神经系统。
他为什么会如此冲动
居住在英格兰利物浦的一位男士每个星期都坚持买相同号码的彩票:14、17、22、24、42和47。
一天,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这个号码竟然中了200万英镑的大奖。
但是这个星期,而且只有这个星期,他忘了买彩票。
于是他在极度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一篇关于作出错误决定之后悔恨心理的学术文章中,作者引用了关于这一悲剧的报道。悔恨的情绪会引发眶额皮层的活动,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自责感,这种自责很可能会引发类似那个彩民那样的精神错乱,但是眶额皮层关键区域受损的病人就不会产生类似的悔恨感觉。不管他们的决定多么糟糕,他们都不会察觉这一点,更不会因此而后悔。
眶额皮层可以调节杏仁核——激情与冲动的发源地。像小孩子一样,眶额皮层受损的病人通常会丧失控制情感冲动的能力,比如,当他们看到别人愁眉不展时,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模仿。缺少了眶额皮层的约束,他们的杏仁核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
这些病人还会对社交规范茫然不知。比如,他们可能会去拥抱或者亲吻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所讲的笑话没有任何品位,只有3岁的孩子才可能因此发笑。他们会愉快地把自己最令人尴尬的一面展示给别人,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可笑。尽管他们在解释社交规范时头脑清楚,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当自己违反社交规范时却浑然不觉。由此可见,如果眶额皮层受损,大路神经系统似乎就丧失了指挥小路神经系统的能力。
退役老兵在新闻报道中看到战争场面,会引起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噩梦的痛苦回忆,这时他们的眶额皮层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一过程的主导者就是过度活跃的杏仁核,类似于自己以前所受创伤的模糊信号也会使它产生痛苦情绪。而在通常情况下,眶额皮层会衡量这样的恐惧感觉并且能够分辨出这只是电视节目,而不是真实的敌人的进攻。
在大路神经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杏仁核就没有办法在大脑中捣乱了。眶额皮层中含有一类可以抑制杏仁核冲动的神经细胞,它们可以对边缘系统产生的冲动说“不”。当小路神经系统发出最初的情感冲动(比如我想大喊大叫,或者她使我感到非常紧张,所以我想离开这里)信号时,眶额皮层会更加全面地衡量当时的形势(这里是图书馆,或者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并且相应地调节这些最初的情感信号,及时地制止这些情感冲动。
当眶额皮层这一情感刹车装置失灵时,我们就很有可能做出不得体的行为。在下面的实验中,研究者安排互不相识的大学生们进入网上聊天室聊天。结果令人震惊,每五组对话中就有一组很快转向关于性的话题,他们语言露骨,讨论性姿势,而且还赤裸裸地挑逗对方。
实验者事后看到这些聊天记录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接待这些学生进出实验室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大学生都非常严肃、谦逊和礼貌,总之和他们在网上聊天时的放肆行为完全不同。
在现实生活中与刚刚认识不久的陌生人聊天时,大概没有人敢讨论如此露骨的性话题。原因很简单: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们会与对方形成情感回路,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得到主要来自对方面部表情和语气等的反馈信息,这些反馈信息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自己的行为与话语是否得体。
导读
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们会与对方形成情感回路,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得到主要来自对方面部表情和语气等的反馈信息,这些反馈信息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自己的行为与话语是否得体。
自从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之后,成人们就经常在网上像小孩子一样攻击他人,这种行为也类似于以上实验中提到的关于性话题的讨论。通常情况下,大路神经系统会告诫我们遵守一定的社交规范。但是网上进行的交流缺少面对面的反馈信息,而这种反馈信息正是眶额皮层帮助我们遵守社交规范所不可或缺的。
什么在决定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多么悲惨的场景啊。那个可怜的女人独自站在教堂前面,不停地哭泣。教堂里肯定在举行葬礼,她肯定在为失去了一位至亲至爱的人而伤心欲绝。
但是转念一想,这不是一个葬礼。在教堂前面停着一辆装饰着漂亮鲜花的豪华轿车——原来这是一场婚礼!多么甜蜜的时刻啊……
这是一位女士看到一张在教堂前面哭泣的女人的照片时的心理活动。第一眼看上去像是葬礼,因此她的心里充满了悲伤,眼睛中闪烁着同情的泪光。
但是她的转念一想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心情。认为那个女人是在参加婚礼,并且想象婚礼上的温馨场景之后,她的悲伤变成了高兴。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会随着认知而改变。
凯文·奥克斯纳的一项大脑成像研究就分析了这种日常交流中的琐碎细节发生时的大脑机制。在30多岁的时候,奥克斯纳就已经成为这一新兴领域的领军人物。当我去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所在的谢莫洪大楼拜访他时,发现整个大楼就像一个杂乱、充满异味的养兔厂,而他的办公室却非常整洁干净。他在那里向我阐述了他的方法。
在奥克斯纳的一项研究中,一位志愿者一动不动地躺在哥伦比亚大学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中心的一个黑暗、狭长的成像仪器中。他的头部上方有一个鸟笼状的仪器,这个仪器可以探测到大脑中原子所发射的脑电波。在这个鸟笼状仪器上有一个成45度角的镜子,可以帮助他看到机器另一端自己露在外面的脚。
虽然这个场景在自然情况下很少出现,但是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大脑在接受某一特定刺激(比如看到惊恐的人们的照片,或者通过耳机听到婴儿的笑声等)后的活动情况。通过这种大脑成像研究,可以帮助神经学家们精确地描绘出在各种人际交流过程中大脑的活动情况。
在奥克斯纳的研究中,女性志愿者会首先观看照片,产生对照片的最初感觉。然后实验者再指导她们重新思考照片上的情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那个从葬礼到婚礼的思路转变就发生在此类实验中。重新思考使得她们引发悲伤的情绪中心得到了控制。具体的过程大致如下:杏仁核的右半部,也就是痛苦情绪的发源地,会对照片上的情景迅速进行自动评估,得出这是一个葬礼的结论,然后引发她们的悲伤情绪。
作出这种最初情感反应所用的时间非常短,而且这一过程是下意识进行的,因此在杏仁核产生这种反应并且引发大脑其他区域活动的时候,理性思维中心还没有完成对于该情景的分析。而且连接情感与认知中心的神经系统还会对这种一触即发的反应进行核实与完善,这样,我们的第一印象就形成了(多悲惨啊——她在为葬礼而哭泣)。
对照片进行有意识的重新分析(这是一场婚礼,而不是葬礼)会使人们产生较为愉快的心情,从而使杏仁核和其他相关神经系统平静下来。奥克斯纳的研究发现,前扣带皮层越活跃,这种反思改善心情的威力就越明显。而且,前额叶皮层中某些区域的活动越活跃,杏仁核在反思过程中就越平静。因此,当大路神经系统取得发言权后,小路神经系统就默不作声了。
当我们有意识地接触某个痛苦场景时,大路神经系统可以通过前额叶皮层中任何一个神经系统的活动来控制杏仁核。我们在反思时采取的心理策略决定了哪个神经系统会被激活。如果我们用客观的、像医生一样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别人的不幸,比如一位重病病人的痛苦,好像我们与他没有任何情感交流一样(这就是医务工作者通常采取的态度),那么前额叶皮层的某一个神经系统就会被激活。
如果我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考虑病人的状况,比如病情不至于致命,或者很有可能康复等,那么这种态度就会激活前额叶皮层中另外一类神经系统的活动,通过改变我们感知事物的角度,我们也改变了它对我们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就像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库斯·奥里利厄斯在几千年前所说的那样,痛苦“不是由事件本身,而是由你对待它的态度所导致的,因此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消除它”。
这个反思实验的结果纠正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我们对于自己的心理状态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的许多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是在“一眨眼的工夫”自动产生的。
“一切思想、情感与行为都是自动产生的说法令人沮丧,”奥克斯纳评论说,“反思改变了我们的情感反应。当我们有意识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就取得了对自己情感的控制权。”
即使我们仅仅是在心里梳理自己的情感也可以帮助杏仁核平静下来。一方面,它会使我们重新考虑可能作出的消极反应,更加全面地考虑当前的情景,从而促使我们作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大路神经系统的这种控制与调节还意味着我们即使面对不良情绪传染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反应。比如,我们可以抵制一个恐惧的人歇斯底里情绪的传染,事实上,我们可以保持冷静并且竭力帮助他平静下来。如果我们不喜欢别人的激动状态,我们也可以抵制他的传染,坚决地保持自己希望拥有的心境。
丰富多彩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种可能。在应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时,小路神经系统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反应,但是决定我们的最终思想、情感与行为的还是大路神经系统。
终结“社交恐惧症”
戴维·盖伊第一次怯场是在16岁的时候。那是在一堂英语课上,戴维的老师要他在课堂上朗读他的周记,而他头脑中浮现的都是同学们的影子。尽管戴维立志做一名作家,而且也在不断尝试新的写作技巧,但是他的同学们都对写作不屑一顾。和其他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们讨厌装腔作势,而且一个个尖酸刻薄。
戴维极力避免他们的讽刺与嘲笑。这时他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他的怯场表现还不仅如此:他的脸变得通红,手心在出汗,而且心跳快得都要喘不过气来了。他越是想努力摆脱这种状态,怯场的症状就越严重。
从此戴维就落下了怯场的毛病。尽管他在第二年被提名为班长,但是一想到做班长要演讲他就放弃了。即使在他到了30多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之后,他仍然避免公开演讲,也拒绝朗诵自己的小说。
戴维·盖伊这种害怕公开演讲的症状十分普遍。调查显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恐惧症,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有此症状。但是在观众面前怯场只是“社交恐惧症”的众多症状之一,精神病诊断手册把这些焦虑统称为“社交恐惧”。其他的形式还包括从结交新朋友或与陌生人交谈,到在公共场所进餐或者共同使用洗手间等场合下的不安表现。
就像戴维的情况一样,社交恐惧症通常出现在青春期,但是这种恐惧可能会持续一生。患有此症的人会尽量避免可能引发自己恐惧的场合,而且一想到这些场合就会引发他们的焦虑。
戴维这样的人的怯场还会对他们的生理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只要他们想到任何一个观众的嘲弄,他们的杏仁核就会被激活,使身体产生大量压力荷尔蒙。因此戴维仅仅想象同学们的嘲笑就会引发生理系统的强烈反应。
这种习得性恐惧部分是由杏仁核回路中心的一类神经系统导致的,约瑟夫·勒杜克斯把它称为“恐惧中心”。勒杜克斯几十年来一直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从事神经细胞的研究,因此非常熟悉杏仁核中的神经分布情况。勒杜克斯发现,接受感官信息的杏仁核中的神经细胞,以及接受恐惧信息的相邻区域,在感知到恐惧时的活动会与平时不同。
我们的记忆总是处于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回忆某次经历,大脑就会根据我们现在的兴趣和理解来更新它。勒杜克斯解释说,回忆某次经历在细胞层面上意味着它会被重新巩固,随后新合成的蛋白质会稍微改变它的化学构成。
每当我们进行回忆的时候,我们都会调整它的化学构成,调整的具体情况取决于我们回忆时出现的新信息。如果我们只是重新经历同样的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就会进一步加深。
但是大路神经系统是可以对小路神经系统进行调节的。如果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找到减轻恐惧的方式,那么在大脑对同样的经历进行再次编码时就会减弱它对我们的影响力。这样,曾经使我们感到恐惧的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小。勒杜克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杏仁核内的细胞会发生改变,使我们对以前的恐惧经历产生免疫力。因此,治疗恐惧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恐惧的神经细胞。
事实上,有些治疗有时会刻意使人们重新体验引发他们恐惧的经历,这样他们可以在经历恐惧的时候练习克服恐惧的方法。这种治疗首先通过缓慢的腹部呼吸使人们平静下来,然后使他们体验威胁性情景,而且通常威胁的程度会不断上升。
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愤怒情绪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纽约市的一位交警因为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骂做“下流母狗”而怒火中烧,因此她在接受这种治疗时,这个词语被反复提到了多次,首先是用平静的语调,然后用比较恶劣的语气,最后还加上了下流手势。而这位交警在治疗中的任务就是坐在那里,尽可能地使自己平静。最后治疗取得了疗效:不管这个词语的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厌恶,她都能够平静对待了。这样她重新投入工作之后即使再次碰到辱骂,大概也能心平气和地开罚单了。
有时治疗师们会在安全范围之内尽可能地为病人重现引发他们社交焦虑的场景。一位认知治疗师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治疗小组作为临时观众来帮助病人克服自己对于公开演讲的恐惧。在治疗过程中,病人不仅练习放松的方式,还会锻炼抵抗焦虑的能力。同时,治疗师还要求临时观众为病人增加困难,比如讥笑他们,或者做出百无聊赖或毫无兴趣的表情等。
当然这种对于恐慌或者愤怒的体验必须在病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曾经有一位即将接受这种治疗的女士找了个借口跑进卫生间把自己反锁了起来,拒绝出来面对挑战。最后在医生的耐心劝说之下她才出来继续接受治疗。
勒杜克斯认为,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从不同视角看待自己痛苦经历的人一起重新体验过去的痛苦经历,就可以重新对这种经历进行编码,从而减轻你的痛苦。这可能就是病人和治疗师在遇到困难时安慰自己的良方之一:接受治疗的过程本身就有可能改变大脑对不良信息的储存。
勒杜克斯说:“这就像是内心产生忧虑之后我们又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它。我们是在利用大路神经系统来重新塑造小路神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