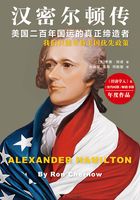
![]()
尽管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会让人散漫怠惰的热带岛屿上,但是他在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做职员的日子里,天天打交道的却都是繁忙的商船和不断变化的市场,这让他早早便经历了快节奏的现代商业活动的洗礼。在这段日子里,尽管他遇到不少挫折,但是汉密尔顿所处的已不仅仅是世界上一个晦暗的角落,他的第一份工作让他真正见识了全球贸易的精彩纷呈和世界列强的纵横捭阖。正因为汉密尔顿在这一片由一家贸易公司开拓的土地上工作,他才有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
比克曼-克鲁格商行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当地种植园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都可以买到:木材、面包、面粉、大米、猪油、黑豌豆、黑啤酒、苹果酒、松木、橡木、铁环、木瓦、石灰、绳子、灯黑、砖头、骡子和耕牛。这给汉密尔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学习平台。他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一大堆让人一看就头疼的货物清单,在这里,他练就了一手华美、清晰而流畅的好书法;在这里,他不得不去记住商船的航海路线,去跟进货船的行踪;在这里,他必须学会用不同的货币单位来计算货物的价钱,无论是葡萄牙硬币、西班牙银元、英镑、丹麦的达克特,还是荷兰的斯泰佛,他都要烂熟于心。他的儿子约翰·C.汉密尔顿在回忆起自己父亲的时候说道:“爸爸曾经专门讲过,在他所从事的那么多工作中,唯有在比克曼-克鲁格商行的这段经历令他受益匪浅。”[1]或许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一个小小年纪就满脑子都是生意经的汉密尔顿。
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坐落于当地的国王路与国王十字路交叉口的一处高地上,这里有商行的一家商店和紧挨这家商店的仓库。每天早上,汉密尔顿一定就是从这里出发,吹着清新惬意的海风,一路下坡,轻轻松松地溜达到繁忙的码头区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在圣·克罗伊岛的码头区有专用的码头和货船,这个年轻的职员就在这里查验到港的货物,在这些货物中,一定有不少偷偷运进来的走私货。码头附近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一桶桶的蔗糖、朗姆酒和糖蜜被马车运到这里,等待被装船运到北美去换取谷物、面粉、木材和各式各样的钉子。圣·克罗伊岛这个由中立的丹麦控制的小岛长期以来扮演着当时英国和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各个殖民地之间桥梁的角色。岛上的贸易一直以来是由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控制着,因此,英语而不是丹麦语成了岛上的通用语言。于是,母语是英语并且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汉密尔顿在这里便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比克曼-克鲁格商行的工作让汉密尔顿有机会早早地和纽约——这个他未来居住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在当时,纽约商人大量参与到与西印度群岛进行的贸易中。许多曼哈顿的商行都会派一个年轻的家族成员到西印度群岛当地去充任商行在那里的代理人,尼古拉斯·克鲁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身于纽约的名门望族,父亲亨利·克鲁格(Henry Cruger)是一位富有的商人、船东和纽约州皇家立法会的议员,他的叔叔约翰·克鲁格(John Cruger)曾经长期担任纽约市市长以及印花税法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照理说应当是铁杆亲英派的高贵世家,在政治上却出现了裂痕,尼古拉斯住在英国的兄弟小亨利·克鲁格(Henry Cruger Jr.)当时是显赫的英国国会议员,在他所在的布里斯托选区,与他同时当选的另一位议员就是令人尊敬的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而尼古拉斯本人,相反地却站到了反叛的殖民地居民一边,并成了乔治·华盛顿的忠实追随者。有人猜测,汉密尔顿的第一个政治导师就是这位尼古拉斯·克鲁格。也正是这位尼古拉斯·克鲁格,让汉密尔顿第一次认识了一群积极进取、心怀天下的纽约商人,这些人就是联邦党人所大加赞赏的社会精英的模范代表。
作为一个孤儿,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无所事事的资格,于是他的身上就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驱使他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这个高度自律的年轻人做事情从来都是斩钉截铁,毫不拖泥带水。在他进入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后,汉密尔顿就已经不像一个普通的13岁男孩那样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了,在商行的工作对他来说,只是让他有了更大的压力,更有紧迫感罢了。当他的同龄人为了一些无聊的事情而浪费青春的时候,汉密尔顿却过着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这让他这条大鱼最终从圣·克罗伊岛这个小鱼缸中跳了出来。要知道,在圣·克罗伊斯这个等级森严的完全静止了的社会中,汉密尔顿这样出身低微却又自负而敏感的年轻人,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他的朋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Nathaniel Pendleton)后来讲道,一提起自己的小职员身份,汉密尔顿就“耿耿于怀,这几乎使他想要放弃在商业上的发展”。[2]在为数不多的保存下来的汉密尔顿早期书信中,有一封写于1769年11月11日的信颇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态。这封用娟秀的字体写成的信阴郁低沉,在信中,这个14岁的少年对自己的卑微身份愤愤不已,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痛心疾首。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了。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汉密尔顿的那位面貌相似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此时他正就读于纽约的国王学院。汉密尔顿在信中写道:
爱德华,我承认我也有弱点,我的野心是如此的明显,我鄙视作为一名小职员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或者命运总是对我加以嘲弄。我会用一生来冒险,提升我的社会地位,这不是我的性格。爱德华,我很确信,少年时代的经历使我没有任何希望马上就能出人头地,那也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会为未来做好准备。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可能会说我这样做是痴心妄想。我的这个傻念头让自己感到惭愧,希望你会为我保守秘密,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当计划者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时这样的计划就会获得成功的事例。最后我想说,我真希望现在就爆发一场战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3]
汉密尔顿的这封短信是那么准确地预言了他的未来!这个渴望在沙场上大显身手、马革裹尸的年轻人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战争。在这封信里,汉密尔顿流露出了强烈的耻辱心,而成年以后的他,就经常会故意用虚张声势的外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从一开始,他就一直担心那过度膨胀的野心会让自己腐化堕落,而他也一直坚持决不能为了征服世界而罔顾自己的道德,这两点对汉密尔顿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尽管信中的措辞有些笨拙,但他表现出一个14岁少年令人惊讶的成熟,并由此开始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光彩。
汉密尔顿有足够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才华。1769年,大卫·比克曼退出了商行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科尼利厄斯·考特莱特(Cornelius Kortright)同样出自名门的纽约商人。于是商行便改名为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过了两年,由于健康原因,尼古拉斯返回纽约接受为期五个月的治疗,在这期间,他让汉密尔顿这个早熟的小职员当上了临时掌柜。一捆汉密尔顿写下的商务信件展示了这个第一次独当一面的家伙是如何“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他开始很卖力气地去索要那些应收账款。在一封写给克鲁格的信中,他向自己的东家保证说:“相信我,先生,我正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为您要账。”[4]在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往来通信是有关一条名叫霹雳号(Thunderbolt)的单桅帆船的。克鲁格拥有这条船的一部分所有权,在1772年的时候,这条船正装运着几十头倒霉的骡子穿越大海。汉密尔顿需要安排这条船安全地经过南美洲的西北海岸(这在当时是西班牙的地盘),同时还需要与无数敌对国家的船只周旋。因此,汉密尔顿不遗余力地向他的老板们建议在霹雳号上加装四门大炮以备不测。在一封写给当时督办库拉索地区生意的塔勒曼·克鲁格(Tileman Cruger)的信中,汉密尔顿说道:“这样一条船如果没有配备必要的武装,那它一定会落入别人之手,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太可惜了。”[5]当这条船最终抵达圣·克罗伊岛的时候,那些骡子已经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了。于是,汉密尔顿用一种不容分说的口气教训船长道:“你得好好反省在这次不幸的旅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你得把这些损失全都补偿给东家。”[6]在未来的日子里,汉密尔顿这种口气的训话,将会被无数的下属领略到。这个年轻的后生尚未成年便表现出了杀伐决断的魄力,即便是面对一位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老水手,他也能毫不犹豫地开腔训话。汉密尔顿就是这么一个一心想出头主持局面,并且也有这个能力的野心勃勃的家伙。于是,当尼古拉斯·克鲁格在1772年3月回到圣·克罗伊岛的时候,他便感到非常失落了。
汉密尔顿的学徒生涯让他获益匪浅。他清楚地了解了商人和走私者是如何玩弄那些瞒天过海的把戏的,这让他力主在美国建立海岸警卫队和海关体系。他发现生意经常会受到现金流和到期债务的困扰,而一套统一的货币体系将非常有利于刺激贸易。最后,他还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西印度群岛所面临的窘境:西印度群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在贸易世界中却处于食物链的下游,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这里的经济过度依赖甘蔗种植与蔗糖的出口。在后来他那篇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就表述过这个难题。或许,汉密尔顿在后来极力主张多元化的制造业与农业经济就是源于他在西印度群岛做商行学徒时期的直观感受。
虽然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主要经营食品和纺织品,然而至少有一年这家商行的货船参与运输了一种更容易腐烂的“货物”——奴隶。在奴隶船上,成百上千的奴隶被铐在一起塞进恶臭的船舱中,有许多人就在这可怕的运输中窒息而死。于是,这样的船上总是散发着可怕的恶臭,以至于岸上的人在数里之遥就能闻到海上奴隶船飘来的臭气。1771年1月23日,在汉密尔顿还在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打工的时候,这家商行在双语的《皇家荷属美洲公报》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刚刚从非洲向风海岸进了一船奴隶,下个星期一就在商行的码头当场拍卖,300个上等奴隶咯!”[7]第二年,尼古拉斯·克鲁格又从非洲黄金海岸进口了250名奴隶,这次,他抱怨道,这些奴隶的“牙口一点也不好,骨瘦如柴的”。[8]人们现在只能想象汉密尔顿在检验、看守这些即将被拍卖的奴隶并给他们定价向别人推荐时看到的是怎样非人的场面。为了让这些奴隶看起来光鲜一些,他们身上的毛会被剃掉,然后再被涂上棕榈油,直到他们的肌肉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有一些买主会直接带着烙铁来到拍卖场,一买下奴隶,就会在他们的身上烙下记号。从尼古拉斯·克鲁格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追捕逃亡奴隶的消息来看,贩卖人口应该也是商行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密尔顿来到圣·克罗伊岛的时候,岛上的奴隶人口在十年内已经翻了一番,于是种植园主开始联合起来,以便能够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或者阻止奴隶向邻近的西班牙统治下的,能够确保他们自由的波多黎各的大规模逃亡。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没有哪个白人能够置身事外:他要么充当奴隶制度的卫士,要么就离开这里远走高飞。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与歧义,丹麦当局印发了一本宣传册“圣·克罗伊斯战士手册”。这本宣传册清楚地规定,岛上的每个年满16岁的成年白人男子都有义务(从1771年开始,汉密尔顿也具备了履行义务的资格)在军队中服役,每个月大家都必须自备枪支弹药参加军事训练。如果要塞的炮声连续响两次,那么所有的白人男子都必须马上带上家伙到要塞集合。
当造反的奴隶在克里斯蒂安斯伐恩被公开处决的时候,白人男子就会把城堡包围起来以防止其他的奴隶惹是生非。在这时,任何攻击白人的奴隶一定会被绞死或者斩首,而对于奴隶来说,相对于被烧红的烙铁折磨和阉割来说,被立即处死更像是一种解脱。在这里,为了让奴隶对白人们俯首帖耳,对奴隶的惩罚是地狱般的。如果一个奴隶举起手抵挡奴隶主的鞭打,那么他的这只手将会被立刻砍掉。如果一个逃跑的奴隶在三个月内被抓了回来,那么他的一只脚就会被砍掉。如果他敢再跑一次,那么剩下的那只脚也会被砍掉。惯犯的脖子上会被套上可怕的铁环,铁环上镶着向里突出的钉子,这样,当这个奴隶打算爬过种植园厚厚的篱笆逃走的时候,他的脖子就会被钉子扎烂。
如果不了解这些他在青年时代所亲眼目睹的残酷场面和后来在美国蔓延的对他希望的剥夺,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汉密尔顿的政见。从浅里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贸易让汉密尔顿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以至于后来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往深里讲,在这个宗法社会中,种植园主终日生活在对奴隶起义的恐惧之中,于是他们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营,这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离开圣·克罗伊岛之后,他还一直深深地陷于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之中,因此对于“自由”并不怎么感冒。于是,他一方面反对种植园主的暴政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又恐惧那些心怀仇恨的奴隶的可能的起义,他的童年生活带给他的最大遗产,或许就是这么一种暧昧的态度。在他的一生中,对专制和无政府主义的恐惧与矛盾心理,一直是萦绕在汉密尔顿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汉密尔顿也是自学成才,一有空闲,他就会抓紧时间读书。这个年轻人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汉密尔顿或许在那时就已经预感到,有朝一日,写作会让他摆脱低贱的身份而跻身于同时代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的行列中。西印度群岛并没有哪家商店有书卖,如果想买书,就得事先预订。于是《皇家荷属美洲公报》的发行对于求知若渴的汉密尔顿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由于当时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国王(King Christian VII)是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表兄和姐夫,这份报纸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了亲英的立场。每期报纸都会刊登当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其他一些雄辩家在英国国会的精彩辩论和有关英国王室的种种阿谀之言。
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可能发表他文章的报纸后,汉密尔顿就开始大量地创作诗歌了。一旦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汉密尔顿就开始滔滔不绝了。亚历山大·蒲柏的优美诗句和精妙结论让这个年轻的小职员着了魔。就像蒲柏在早年模仿古典诗人的作品一样,汉密尔顿也炮制了不少模仿蒲柏风格的诗文。在1771年4月6日,他在《公报》发表了两首诗。在一封写给公报编辑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先生,作为一个不到17岁的年轻人,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能在仔细阅读我写的这两首诗后,觉得它们还值得在您的报纸上占据一小块版面并允许刊登它们的话,我将对您感激不尽。您顺从的仆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发表的这两首爱情诗对待感情的视角完全不同。这个好空想的诗人在第一首诗中歌颂了他的初恋情人,诗中的这个女孩正躺在河边,身边是一群可爱的小羊羔;而诗人则跪在爱人面前,用一个深情的吻唤醒了女孩,然后含情脉脉地将女孩搂入怀中,最终赢得佳人的芳心。诗人吟咏道:“相信我,男女神圣的结合会让爱情加倍的甜蜜。”[9]在第二首诗中,诗人却摇身一变成了个浪荡公子,这首诗的开场白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短句:“希利亚是一个狡猾的小荡妇。”这首诗描绘了一个狡猾得像猫一样的女人:
瞧,那柔滑的小手,
那小娘儿们精致地把它们藏起来
在呼噜声中;但如果
你轻轻用力捏她一下
她便会立刻尖叫一声,弓起细软的背部;
对你还是充满了善意。
第一首诗就像是一个憧憬着贤良淑德的美妇人的未成年小伙子写下的赞美诗,而第二首诗却像是一个已经尝过了无数女人的滋味,彻底抛弃了对妇女节操的任何幻想的年轻但却消极厌世的情场老手吟哦的小调。这两首诗所描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纯洁无瑕的小天使和现实轻浮的狐狸精。同时迷恋这两种人所带来的麻烦,一直纠缠着汉密尔顿的一生,让他无法脱身,并使他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诽谤与丑闻中。
第二年,汉密尔顿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两首诗,这时候,我们得称呼他为一个“宗教诗人”了。汉密尔顿心灵的变化或许源于一位名叫休·诺克斯(Hugh Knox)的长老会神父。年轻英俊的诺克斯出生在北爱尔兰,祖先是苏格兰人,移民到美洲后在特拉华州的一个学校做教师。这个轻浮的花花公子起初对宗教信仰没有半点兴趣,然而一桩奇怪的事改变了他的一生。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一个诺克斯经常去鬼混的酒馆,他当着那些醉醺醺的狐朋狗友们的面,拙劣地模仿自己的赞助人,可敬的约翰·罗杰斯牧师(Reverend John Rodgers)布道的样子,来换取那些醉汉们的哈哈大笑。在这之后,诺克斯却突然坐了下来,为自己的亵渎神灵而震动不已,同时,那布道的场景一直在自己的脑海中回荡,他突然发现自己被这布道打动了。于是他突然决定到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当时的校长,著名的神学家老亚伦·伯尔(Aaron Burr Sr.)去学习神学。而这位老亚伦·伯尔校长,就是那个日后会置汉密尔顿于死地的人的父亲。或许正是从诺克斯神父的口中,汉密尔顿第一次听说了“亚伦·伯尔”这个名字。
诺克斯在1755年被伯尔任命为牧师,他决定献身于传播福音的事业中,于是他奉命前往了荷属西印度群岛的萨巴岛。萨巴岛,离尼维斯岛不远,方圆不过12平方千米,并没有其他加勒比岛屿那样迷人的海滩,这个孤零零的小岛足够摧垮哪怕是最坚忍的传教士。波涛汹涌的大海常年冲击着怪石嶙峋的海岸,这使得船只在这里靠岸成了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身为这里唯一的一个传教士,诺克斯住在一个叫“坑底”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位于一座死火山洞的底部,一串石阶是这里唯一通向外界的道路。至于那些灵魂需要诺克斯来拯救的居民,诺克斯描绘了这样一幅凄惨的画面:“这里的年轻人和已婚男人不光毫无虔诚的信仰,而且干脆就是一群和自己的黑奴通奸的乱伦者、花花公子、晚上的暴徒、醉鬼、赌棍、不守安息日规矩的守财奴、不去教堂的渎神者、不守信用的骗子和从事不公平交易的奸商……”[10]在这个岛上,受过传统教育的博学的诺克斯没有与他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兜里也没什么钱。1771年,诺克斯神父到圣·克罗伊岛访问,在这里,他受到了当地长老会教徒的盛情款待,他们邀请诺克斯神父搬到圣·克罗伊岛来。于是,在1772年,诺克斯跳槽到苏格兰长老会做一名牧师,这份神圣的工作带给他的还有比以前在“坑底”多得多的薪水。
经过了在萨巴岛的孤独岁月,这位45岁的诺克斯神父感觉自己在圣·克罗伊岛迎来了第二春。这位博学的神父后来还写了几卷宗教训诫,他仁慈而宽容,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后来他非常热心地支持美国独立),反对蓄奴(尽管他自己也拥有几个奴隶),他的一些观点非常吸引汉密尔顿。在诺克斯神父早期的信件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坚定地认为私生子同样有资格接受洗礼,神职人员有义务将私生子从他们不负责任的父母那里解救出来,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诺克斯神父的宗教观点已经背离那种冷冰冰的加尔文主义 的教条,诺克斯眼中的上帝,是一个和蔼而公平的天主而不应当是一个阴暗的惩罚者。诺克斯神父同时也认为无穷的求知欲正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他对那些能够建构“真理的体系”的人们致以了最高的敬意。[11]
的教条,诺克斯眼中的上帝,是一个和蔼而公平的天主而不应当是一个阴暗的惩罚者。诺克斯神父同时也认为无穷的求知欲正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他对那些能够建构“真理的体系”的人们致以了最高的敬意。[11]
于是,一位有着异乎寻常的建构系统能力的年轻私生子职员走入了他的生活。诺克斯神父一定把他能有如此的好运气去发现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天才当成了一个奇迹。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是何时相遇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父把自己的整个图书馆对这个天才少年开放,鼓励他撰写散文,引导他走向学术之路。就像一个有趣的老伯父一样,诺克斯神父担心汉密尔顿因为压力太大而会过度工作,会太迫切地想去讨回荒废的时光。于是,诺克斯神父经常会提醒汉密尔顿说:“你野心勃勃地想要超越自己,总想竭力在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上尽善尽美,现在的你,已经非常脆弱了。”[12]诺克斯神父的直觉异常的准确,汉密尔顿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尽管他后来仍然承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成就完全超出了他的估计。
除做神父之外,多才多艺的休·诺克斯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医生和药剂师,他还在业余时间兼任《皇家荷属美洲公报》的编辑。或许他和汉密尔顿就是在报馆而不是教堂相识的。当一场可怕的飓风在1772年8月31日的夜晚蹂躏了整个圣·克罗伊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之后,诺克斯神父的这个兼职编辑的身份,让汉密尔顿的一生发生了改变。
据说,这场飓风是百年不遇的。按照《公报》当时所报道的来看,这场飓风是“有史以来人类所遭遇的最可怕的风暴”。它在日落时分突然袭来,“其声如万炮齐鸣,除了中间有过半小时的间断外,它整整肆虐了六个小时……这个曾经美丽的岛屿如今已是满目疮痍,其可怕程度已经完全无法用语言描述了”。[13]这场可怕的飓风将大树连根拔起,将房屋撕成碎片,它掀起的巨浪将港口的船只一扫而光,径直将它们抛向陆地。尼维斯岛的详细记录同样证明了这场风暴的可怕威力,在受灾非常严重的地区,成桶的蔗糖被卷到了350米以外,而一些家具则被发现散落在3公里之外的地方。第二天下午,尼维斯岛还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地震。很可能,尼维斯岛、圣基茨岛、圣·克罗伊岛和邻近的一些岛屿都遭受到一场浪高5米的海啸的袭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西印度群岛的大多数地区,以至于人们需要从北美紧急进口一批粮食来避免预料之中的饥荒。
在9月6日,休·诺克斯将教徒召集到了他的教堂,他为这些仍然在恐惧中瑟瑟发抖的人们做了一次安抚性质的布道,过了几周,他又将这次布道的内容印制成了宣传册在岛上散发。汉密尔顿一定也参加了这次布道,或许是受到诺克斯神父的说教的启发,汉密尔顿回去之后立即给他那离家出走的父亲写了一封冗长但却狂热的信来描述这场可怕的飓风(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在父亲离开圣·克罗伊岛六年后,仍然同其保持着书信往来。而詹姆斯·汉密尔顿并没有遭遇这场风暴,说明他应当是居住在加勒比群岛南部,很可能是在格林纳达岛或是多巴哥岛)。在这封读起来让人感觉如身临其境一般的描写飓风的信中,人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个文采飞扬的年轻人那过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汉密尔顿后来一定也让诺克斯看了这封写给父亲的信,而诺克斯说服他在《皇家荷属美洲公报》上发表这封信。于是,在10月3日,汉密尔顿的这封信就见诸报端了。在很可能就是诺克斯本人给这篇文章所写的前言里,有这样的话:“以下这封信,是由本岛的一位年轻人在飓风肆虐后一周写给他父亲的。这封信的一个副本碰巧落到了一位绅士手中,他在将这封信给数位先生传阅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把这篇文字拿出来给公众分享,那真是太可惜了。”为了不让大家怀疑“无情”的汉密尔顿发表这封信,是想利用人们所经历的灾难来为自己谋取向上爬的资本,诺克斯特地在前言中强调说这位匿名的作者一开始并不同意发表这封信——或许这是汉密尔顿人生中最后一次不情愿让自己的文字见诸报端吧。
汉密尔顿的这封有关风暴的信之所以能让读者们大吃一惊,是因为两个原因。很难想象,一个年仅17岁,完全依靠自学成才的少年,能写出那么雄浑有力的文字,显然,汉密尔顿当时已经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底蕴了:“整个自然界仿佛在这一瞬间分崩离析了。暴风裹挟着巨浪在空中肆虐,炽热的流星划破长空,持续的闪电强光让人眩晕,一栋栋房屋顷刻间轰然倒塌,人们刺耳的尖叫声和哭喊声不绝于耳,就连天使看到这一切也会震惊不已的。”
不过,汉密尔顿在信中的描写更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将这场灾难归因于神对人类的浮华与虚荣的惩戒。在既像是悲壮的内心独白又像是悲天悯人的布道的一段话里,汉密尔顿劝诫自己的同类说:
喔,卑贱的草民哪,这就是你们所自夸的坚韧与刚强吗?你们还能自大自满吗?死神藏身于无尽的黑暗中,吹着胜利的号角悄然来临,他那嗜血的镰刀闪耀着幽光指向你们,正准备给予致命一击……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恶心的样子吧,该到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了……唯有彻底鄙视自己,去全身心地敬畏你们神圣的主,你们方能得救……醒来吧,你们这些在富足中自满的人们,贡献出你们的财富来拯救那些在苦难中呻吟的人们吧,你们在尘世的善行就是你们在天堂中积累的财富。[14]
即便是在一场致命的风暴之后所写下的文字,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来说,汉密尔顿在这封信中所反映出的心态还是异常灰暗的。他那启示录般的语言与悲观的基调让他的世界观显得异常灰暗。在这封信中,他还流露出了些许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他劝告有钱人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和别人分享。
汉密尔顿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让他摆脱了贫困。事实证明,这场自然灾害拯救了汉密尔顿。就连圣·克罗伊岛的总督也开始打听起作者的身份了,当地的商人们决定凑一笔钱把这个前途无量的小伙子送到北美去接受教育。飓风荡平了岛上的房屋,摧毁了人们赖以为生的甘蔗园,扫荡了热火朝天的蒸馏场,让整个圣·克罗伊岛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一片灾难后的萧条时刻,商人的慷慨便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
汉密尔顿最主要的帮助者应该还是那位好心肠的休·诺克斯。后来,他对汉密尔顿说:“我一直暗自为自己能够推荐你去北美,并且把你介绍给我在那里的老朋友而感到自豪。”[15]在赞助汉密尔顿的人中,出钱的或许是他以前和现在的老板尼古拉斯·克鲁格、科尼利厄斯·考特莱特、大卫·比克曼,以及他的监护人托马斯·史蒂文斯和汉密尔顿的表姐安·莱顿·文登(Ann Lytton Venton)。或许是考虑到汉密尔顿曾经对医学很感兴趣(事实上,他一直如此),他的这些赞助人因此想把汉密尔顿培养成一名医生,等他学成归来,就能够为治疗在岛上流行的热带传染病而出一份力。加勒比永远都缺少医生。而此时,汉密尔顿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就正在纽约学医。
按照流行的说法,汉密尔顿在1772年10月乘船前往北美,从此便再也没有踏回西印度群岛半步。不过,在仔细研究《皇家荷属美洲公报》后我们便发现,即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事件依然是疑窦丛生。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一首题为《忧郁时刻》(The Melancholy Hour)的诗歌的真正作者,而这首诗发表在1772年10月11日的公报上。这首诗写道:
为何让这忧伤的沮丧萦绕在我心头,
为何我的内心充满挣扎的叹息?
它所反映的主题,仍然是在宣扬暴风是神对堕落的尘世的惩罚这种调子。10月17日,《公报》又发表了一篇模仿蒲柏风格的,虽然匿名但是显然出自汉密尔顿之手的赞美诗,这首诗在后来还被他的妻子用来证明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首题为《灵魂的升华》(The Soul Ascending into Bliss)的赞美诗充满可爱的神秘主义的冥想,在这首诗中,汉密尔顿仿佛是在看着自己的灵魂在天堂翱翔,他写道:
听啊,听啊!
那天籁之音。
我听到了救主的召唤
……
主啊,我来了,我上来了!
我舞动着翅膀,我飞到了天的尽头。
在1773年2月3日的《公报》上刊登的一篇《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性格》(Christiansted A Character By A. H.)的诗被大多数人忘记了,在这首简短的诗中,汉密尔顿讲述了一个名叫尤金尼奥的机敏的人,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和他所有的朋友都恩断义绝的故事,汉密尔顿写道:
睿智的人不会让怨恨变成恶毒
他也不会为了自己高兴而让朋友受苦![16]
汉密尔顿的这首诗或许是受到了法国作家莫里哀(Molière,)一生中的某桩事件的影响,支持了人们有关他在1772—1773年的冬天仍然住在圣·克罗伊岛的说法,当然,这首诗也有可能是他从北美邮寄给休·诺克斯神父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汉密尔顿一生中的转折点,我们有必要在他的这段令人费解的传奇故事中引入另外一位人物:汉密尔顿的表姐,安·莱顿·文登,即后来的安·米切尔(Ann Mitchell)。她可以说是汉密尔顿一生中亏欠最多的人,在和伯尔决斗的前夜,汉密尔顿回顾自己的一生,对妻子讲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所有的朋友中,我欠的人情最多的,就是米切尔太太,我对她到现在也没有履行完我的责任。”[17]是什么让汉密尔顿对这个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的人物如此耿耿于怀呢?
安·莱顿·文登,比汉密尔顿大12岁,她是汉密尔顿的姨妈安·福塞特·莱顿的长女。像汉密尔顿家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她的一生也同样的命运多舛。在安只有十多岁的时候,她就被嫁给了克里斯蒂安斯特德一个名叫托马斯·豪伍德(Thomas Hallwood)的穷杂货店老板,然后很快就为他生了个儿子。没想到他们结婚后刚刚一年,豪伍德就死掉了。于是,在1759年,安改嫁给了算是殷实人家的约翰·科尔万·文登(John Kirwan Venton),他那个时候经营一个不大的甘蔗种植园。然而,三年后的1762年,文登破产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无论是房子还是金银细软,都被债权人分得干干净净。无奈之下,这对走投无路的夫妻只好跑到了纽约,而把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女儿留在外婆家。然而,文登夫妇在纽约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在1770年搬回了圣·克罗伊岛。此时,安的哥哥彼得已经自杀,而她的父亲詹姆斯·莱顿也已经去世了。如果约翰·科尔万·文登有过染指岳父遗产的想法的话,那么老莱顿无疑让他非常失望。詹姆斯·莱顿把自己遗产的七分之二分给了安,却明确表示禁止文登碰这些遗产一个指头,在老莱顿的眼里,文登是个“干什么事都会导致不幸结果的家伙”。
此时,文登夫妇的婚姻以一种十分讽刺的方式宣告了死亡,一方面,安和她的女儿占据了她去世的兄弟彼得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房子,而约翰·文登却在弗雷德里克斯泰德流浪。飓风之后,约翰·文登再次登记向他的债权人宣告破产。和那个约翰·迈克尔·拉维恩相比,约翰·文登在刻薄方面同样毫不逊色。1773年5月15日,他在公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广告:“约翰·科尔万·文登禁止任何船只带安·文登或者她的女儿离开这个岛。”[18]然而,安·文登根本就不把科尔万的威胁放在眼里,她带着女儿逃到了纽约,这一勇敢的行为一定会唤起汉密尔顿对母亲的回忆,当年蕾切尔也是一样勇敢离开那个令人讨厌的拉维恩的。为了确保她的继承权,安委托当时18岁的汉密尔顿作为自己财产的代理人,授权他收取那些分别会在1773年5月3日、5月26日和6月3日到期的房租。在收到了这些租金之后,汉密尔顿就乘船前往了波士顿,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西印度群岛。或许是出于对汉密尔顿的帮助的感激,也或许仅仅是出于对自己的这个聪明伶俐的表弟的喜爱,安便充当了汉密尔顿的赞助人(她可以说是汉密尔顿最主要的赞助人),替汉密尔顿支付了前往北美的旅费以及接下来的学费。在后来的日子里,知恩图报的汉密尔顿也一直在经济上帮助安。相比其他的赞助人,汉密尔顿对安总是怀有一丝特殊的情谊,很可能,安对汉密尔顿的支持和帮助,远远不只是替他出旅费和学费这么简单。
当汉密尔顿漂洋过海抵达波士顿的时候,陪伴他的是烙在心头难以磨灭的种种创伤,从此之后,他就把童年的所有不快,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再也没有向他人敞开心扉。除了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外,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显然厌倦了热带地区奴隶主统治下的懒洋洋的、毫无生气的社会,从此之后,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思乡之情,也从没有表示出要到出生地看看的意思。两年后,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们总是对故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更是不可能和故乡断绝一切联系,除非,他别无选择。”[19]和其他许多孤儿与移民一样,汉密尔顿决定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同自己的过去彻底划清界限,他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不以出身论英雄的国度,希望自己不再在“私生子”这个头衔的阴影下苟且挣扎。汉密尔顿那摆脱耻辱的动力、对耻辱的恐惧让这个自负的青年的信中充满了对成功的贪婪渴望。这个攻读历史的学生很快就认识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真理,他后来写道:“人的处境总是在发生变化的,现在那些脑满肠肥的富商巨贾的祖先或许一贫如洗,而目前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乞丐,却有可能是名门之后。”[20]汉密尔顿本人就是前一种人,而他的父亲,毫无疑问,就是那挣扎在贫困中的落魄公子。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乘船来到北美开始他一生的冒险时,他那不争气的父亲则陷入了贫困的泥潭,毫无翻身的可能。圣文森特岛的档案记载道,詹姆斯·汉密尔顿后来流浪到了一个位于加勒比群岛最南端靠近南美洲的小岛上。这个名叫贝基亚岛的与世隔绝的小岛,就在圣文森特岛的正南方,当时的不列颠政府正在那里推行一项旨在安置贫困移民的福利项目,詹姆斯·汉密尔顿当时就是这个项目所救助的对象。贝基亚岛位于格林纳达群岛的最北端,面积大约只有18平方千米,岛上遍布着悬崖峭壁和金黄的沙滩。1774年3月14日,詹姆斯·汉密尔顿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无偿授予他位于贝基亚岛东南海湾附近的一片将近10公顷的林地。这个可爱却险象丛生的地方是加勒比地区的土著和逃亡奴隶的聚居地,詹姆斯·汉密尔顿选择的那块地,原来就是被预留用来修建一个镇压叛乱的要塞的。总而言之,贝基亚岛属于那种偏僻而荒芜的地方,只有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搬到这里来。詹姆斯·汉密尔顿得到的那张地契,就默默地讲述着这个现实,它明白地宣称“这块面积为10公顷的土地并不适合建设甘蔗种植园”,因此这块土地是被留出来专门用作建设“贫困移民屋”之用[21]。根据授权书的记载,詹姆斯·汉密尔顿在最初的四年不需要为这块地花一分钱,条件是他必须在贝基亚岛至少住满一年。一份1776年的调查显示,詹姆斯·汉密尔顿和一个名叫辛普的人共有一块29公顷的土地,而他们是在这里的“穷人登记表”上登记的仅有的两个人。詹姆斯·汉密尔顿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相信,自己真的是那个苏格兰领主的第四个儿子,自己真的是一个曾在被雾气环绕的城堡中长大的贵公子。让人惊叹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段内,这对父子一个陷入了贫困的深渊,而另一个则如同一颗新星,在北美冉冉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