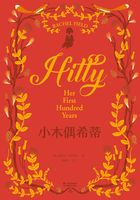
第4章 出海
那天,菲比和我就在“戴安娜·凯特”号尾舱室一张非常顺滑的马鬃毛沙发上过了一夜。之后,人们会在船长的房间给菲比安个铺位。那天我们到得实在突然,大家都忙着起锚,根本顾不上别的事。
“我打算四点起航!”我听见普雷布尔船长对一个被安迪称作大副的男人说,“这样,潮汐就能把我们送出去!”
他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觉得潮汐特别热心。现在想来,那时我对海洋真是一无所知。
整个晚上,菲比和我都在那张马鬃毛沙发上滑上滑下。我听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声响:“丁零哐啷”“咯吱咯吱”。有链条转动的“咔咔”声、靴子踩在木甲板上的“咚咚”声,还有虽然听不太清,却活力十足的吆喝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越来越熟悉这些声音。
第二天清晨,菲比抱着我,顺着陡峭的舱梯爬上甲板后,我们发现“戴安娜·凯特”号正在乘风破浪。方形帆被风吹得鼓鼓的,船头在青绿色的浪花中起起伏伏。这样的景象,我真是头一次见到!
甲板突然晃了一下,菲比差点滑倒。安迪对我们说:“嘿,这可算不上什么。等咱们绕过哈特勒斯角,你才会大开眼界呢!”
“小家伙,你还知道哈特勒斯角啊!”旁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话的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衬衫和洗得发白的蓝裤子。他走到我们身边,对安迪说:“你可是来这干活的,快,去厨房给我们弄点儿喝的!”
安迪立刻飞奔而去,消失在我们刚刚爬上来的舱梯下。不久,海风便送来了咖啡的香味。那个大块头水手把菲比抱到木工台上坐着。台子安在船中央,挨着桅杆之间的一个大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嵌在甲板上的砖砌大坑就是鲸油提炼炉。几个人在旁边干着零活,他们也又黑又壮,就跟刚才那个水手一样。
“嘿,比尔,有女士跟我们同行啦!”其中一人跟我们打起了招呼。他一边会心地冲菲比眨着眼,一边灵巧地在绳子上打了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结。“这下,我们说话可得注意了。”
他们量了菲比的身高,好为她做张新床。而一个叫伊利亚(我们都叫他利哥)的水手也答应为我做张小吊床。这些水手都乐观而友善。海上强烈的阳光照得人非常舒服。船帆涨得鼓鼓的,在彼此身上投下交叠的暗影。看着眼前波澜壮阔的蓝色大海和身后渐渐消失的波士顿,我满心欢喜,一点儿都不后悔上了船。
开头几天,菲比有些晕船,其余人没有半点不适。安迪又是唱歌,又是吹口哨,还大跳船员们教他的角笛舞。就连普雷布尔太太,也逐渐习惯了船上狭窄的厨房,做出一大堆蜜糖饼干,足够大家吃个饱。这在当时的捕鲸船,或任何一艘船上,都是难得的享受。
大家都很照顾我们,只有一两个人嘟嘟囔囔地抱怨,说些让女人上船会招来噩运的话。事实上,菲比·普雷布尔和我很快就跟船员们打成了一片,她妈妈都抱怨说等再回到家,菲比肯定已经野得不成样子了。菲比把我诞生的故事讲给利哥和他的哥们儿鲁本·索姆斯听,说我是用花楸木做的。于是,他俩都坚信我一定会为这次航行带来好运。对此,我真是骄傲极了。
“瞧,她不是跟我们的老戴安娜一样棒么!”鲁本指着船头斜桁下刻着的那尊雕像说。
说实话,我真是吓了一跳,生怕他也提议把我钉到那去。那样的话,任何一个大浪打过来,又咸又涩的海水都会把我淋个透湿。我可不羡慕那位可怜的女士。我受到的所有优待,尤其是利哥为我做的那张小吊床,都让我感激不尽。我还得到了很多其他的礼物,那些男人仿佛在比赛谁更心灵手巧似的,都争先恐后地找各种零碎材料为我做东西。绳头、碎片,甚至小木块,都能被他们利用起来。于是,没过几个星期,除了小吊床,我又有了一个水果篮、一个骨雕脚凳和一个能把我所有宝贝都装起来的水手储物箱。箱子是比尔·巴克尔送给我的,为了做它,巴克尔真是费了好大心思。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十分完美的作品。箱子被漆成漂亮的宝蓝色,每一边都有个精美的拉锁,盖子上还用闪亮的钉头拼出了我名字的首字母。那真是让我无比骄傲的一天。菲比也高兴极了,在船上跑来跑去,把箱子拿给每个人看,甚至差点爬上“乌鸦窝”去展览,幸好被她爸爸及时制止。
一听到有人提“乌鸦窝”,我又一次悲从中来。不用说,那段老松树上的惨痛经历我仍然记忆犹新,着实不想再重温一次。但我很快便发现,自己误解了这个词的意思。它指的其实是那个小小的黑色瞭望台。后来,看船员们轮流爬上绳梯,透过那个“乌鸦窝”搜寻鲸鱼,就成了我最大的乐趣之一。但那时候的我不过在白费功夫,因为要驶过合恩角,进入南太平洋后,我们的捕鲸之旅才算真正开始。
总的来说,第一个月的航行十分顺利。气候温和宜人,海风迅疾而平稳。每天,安迪和船员都轮流到小厨房,给普雷布尔太太打下手。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去“照料茶壶盖儿”。普雷布尔太太已经渐渐习惯船上的生活,一切顺心时,我们会听见她说:除了晚上没有邻居来串门,缺了个像样的洗碗槽,少了供奶的奶牛,世上还是有很多地方比不上这儿。当然,有些时候,比如星期天,想起我们现在离聚会山那么远,她还是会叹气。然后,她便把安迪和菲比叫到跟前,确保他们没有忘记十诫和《圣经》里的二十三首诗篇。
现在,比尔·巴克尔经常来,已经跟我们混得很熟,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水手刀都借给了安迪,还把身上最棒的刺青展示给我们看。船上的男人几乎都有刺青,但谁的刺青都没有比尔身上的精美。他一条胳膊上文着绿色的美人鱼和海蛇,另一条胳膊上文着蓝色的锚和鲸鱼,而他的前胸,则几乎被一艘三色快速帆船占满。安迪十分眼馋那些图案,但当他听到比尔·巴克尔为此花了多少钱后,就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吭了。不过,比尔还是答应一有机会,就替他在胸口文上名字的首字母。菲比觉得受到冷落,吵着也要为我文一个。这可把我吓坏了。好在比尔说他从不赞同女士文身,我才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比尔·巴克尔真好!想到这,眼前不由再次浮现出比尔那双黝黑的大手,直挺挺的黑胡子,以及他遥望大海时,那双浅蓝色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
来自楠塔基特岛的杰里米·福尔杰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因为年轻时从横桅上掉了下来,所以才摔成了驼背。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一点儿也不妨碍他在船上做事。事实上,普雷布尔船长都说,能拥有杰里米这样的船员是他的幸运。因为无论走到哪儿,杰里米都是最棒的鱼叉手之一,目光敏锐,投得又稳又准。有传言说,就算九英里外有鲸鱼喷水(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叫“鲸鱼吐气”),他也能看见。安迪和菲比对此深信不疑。和其他人不一样,杰里米没留胡子,麦色头发被海上强烈的阳光几乎晒成了白色,显得他十分与众不同。直到今天,我都没搞清楚他那会儿到底是快二十,还是快七十了?
一天晚上,我听见普雷布尔船长对他妻子说,现在唯一让他烦恼的,就是“一切都太过顺利”!我已经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说的这话,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碧海蓝天。那些充满咸咸海味的漫长日子如此相似,真是太难区分。不过,我们抵达神秘的合恩角后,“戴安娜·凯特”号便遇上了坏天气。风暴来得非常突然。那是一个傍晚,我们还没来得及固定船帆,封好舱门,船就陷入了风暴之中。我们再也不能悠闲地在甲板上晒太阳、聊天了。接下来的两天两夜,我们都在海浪中翻卷沉浮。那样的撞击和颠簸简直无法用笔墨形容!之前老松树上乌鸦窝里的那点儿摇晃和吵闹,跟这一比真是差远了!
“凯特,待在这,别上去!”临上甲板前,普雷布尔船长环顾了一遍船舱,确保所有的东西都捆结实了,又对妻子说,“海上不可能天天都风平浪静,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也经历过。现在,我要逆风停船,换成空桅,等待风暴过去。”
“好吧,达内尔,多穿双袜子再走,把围巾也拉高点!”虽然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我看得出,她非常担忧。
“换成空桅是什么意思啊?”菲比好奇地问。
“就是说,他要把帆都收起来!”安迪回答,“我想,我也该上去看看。”
“你不能去!”普雷布尔太太连忙大声制止,“只有那些男人才能在甲板上站住脚,要是你,马上就会被大浪给卷走!赶紧跟我去厨房,帮忙把火生好,我们煮点热汤!就算以前都不喝汤,没准儿今晚就想喝了呢!”
虽然离睡觉的时间还早,但他们不仅把菲比和我放进了小床,还用一块旧法兰绒把我们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是不是绑起来更合适?)
这下,菲比不乐意了。“你可不能再掉下床,摔断骨头!”她妈妈说,“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啦!”
尽管周围一片喧闹,根本睡不着,我们还是乖乖地待在床上。外面的主舱挂着一盏油灯。那是暗夜里仅有的一点儿微光,还散发着呛人的烟味儿。船不断颠簸,油灯也疯狂地摇晃着,扯出各种可怖的影子,把菲比都吓哭了。但上面太吵,根本没人听见她的哭声。或者说,就算听见,他们也没空停下来安慰她。最后,她只得一头钻到毯子下,紧紧地抱着我。
“哦,希蒂,”她低声说,“我真没想到出海会是这样的,你也没想到吧?”
那夜是那么漫长,天好像永远都不会亮了。清晨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情况也没好多少。船舱里还是像午夜时一样,喧声震天,漆黑一片。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每次一打开舱门,就会有海水灌进来。即使关着舱门,只要有大浪扑上“戴安娜·凯特”号的船头,咸咸的海水便会成吨地冲过甲板,船舱也会不断渗水。眼看着船舱的积水已经有好几英寸深,绝望的普雷布尔太太只能想尽一切办法,不让炉中的火灭掉。
普雷布尔船长很少下到舱里来。有次下来时,他对妻子说:“你最好也像菲比那样待在床上。我很想派个人下来帮你,但说实话,我真是抽不出人手来了。船的前甲板漏水,光是舀水,就用了四个人。”
“天啊,达内尔!”我听见普雷布尔太太大声喊道,“这已经是最糟的情况了吗?”
“情况的确不怎么乐观。”船长站在舱门边,猛灌普雷布尔太太用锡杯端来的热茶,“问题是,风暴不停,就没法开始补漏洞。要是能熬过这次,船很快就能修补好的。”
我已经不知道那天是怎么熬过去的了。我只记得,“戴安娜·凯特”号每次被浪头打下去,都像要带着我们一起坠入海底似的。每次从浪里钻出来,船身都在剧烈震动,每根横梁都拉得紧紧的。每一次震动,我都以为是最后一次。可紧接着,船身又开始往下沉啊,沉啊,仿佛我们再也爬不出那巨大的漩涡了。
风浪声越来越大,在不断的碰撞和颠簸中,船员们用尽全力的呼喊,也变得几不可闻。巨浪翻卷着向我们袭来,狂风呼啸着掠过桅杆,一副要将它们统统折断的样子。第二天夜里,不仅风暴来得更加猛烈,还发生了一场意外,差点要了我们所有人的命。
那时,因为漏水和不断打过来的巨浪,有一部分船头已经全浸在水里了。之前睡在那的船员只要一进舱,就必定会抓紧时间打个盹儿。其实,船上已经没有一块干爽的地方。但在上方甲板与风雨搏斗时,他们都早已全身湿透,所以根本不在意地上那几英寸的积水。我们也瞥见过一两次杰里米、比尔·巴克尔和其他几个好朋友。但他们都已筋疲力尽,浑身湿漉漉地滴着水,只能冲我们点下头,或笑一笑。的确,那时候,谁都没有心情玩。
几个船员凑在一起,合力拧湿透了的夹克。就在这时,刮来一阵特别强劲的大风。我们都能感觉到“戴安娜·凯特”号的剧烈颤抖,接着便响起一阵恐怖的断裂声。即便现在已经待在安静的古董店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然不寒而栗。随即,甲板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更多的断裂声,以及普雷布尔船长声嘶力竭地指挥声。但在震天的喧嚣声中,船长的声音听起来比蟋蟀大不了多少。
“伙计们,砍掉中帆!”他大吼道,“都砍掉!”
三个本来在船舱里休息的船员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顺着舱梯爬了上去。借着油灯摇曳的微光,我看见菲比的妈妈突然从我们下铺站了起来,脸色苍白如纸。她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菲比,另一只手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怎么了,妈妈!我们要沉下去了吗?”看到妈妈脸上惊恐的表情,菲比哭了起来。
“不会的,你爸爸有办法!”她妈妈虽然这样回答,眼睛却瞪得老大,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正站在没过脚踝的积水中。
“我不相信船会沉!希蒂还在船上呢!”菲比提醒她,“她是花楸木做的,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好运!”
但普雷布尔太太实在太紧张,既顾不上听她讲话,也没空责备她。
仿佛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上面才终于安静下来。船员们回到船舱,船长也下来了一会儿,给妻子报平安。从他口中,我们得知,原来主中桅断成了两截,所以得找几个人爬上去把中帆、横桅、天知道还有什么东西都砍掉。
“是的,”他边说,边甩着胡子和眉毛上的水珠,“它已经偏出船舷了,幸运的是,船没有跟着翻过去。”
“噢,达内尔,”他妻子大声说,“我给你拿件干衬衫换上,好吗?”
可她还没走到箱子前,船长就又走了。
过了一会儿,安迪也下来看望我们。他一直跟舱里那些人在一起,所以听到不少关于我们处境的消息。他爬上床,盘腿坐好,将知道的事一股脑都讲给了菲比听。
“大家都以为我们这次要完蛋了,”他告诉我们,“比尔·巴克尔说,要是杰里米和利哥没有及时砍断中桅,再过五分钟,我们全得“跟鱼儿做伴去”。船长知道那是唯一的办法,但老帕奇还是气得发疯,说什么都不让他们砍。”
帕奇是大副,一头淡茶色头发,背有些驼。自我们上船以来,除了偶尔打个招呼,他再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一直都不喜欢他,现在就更加确定,他肯定对大家都没安好心。
“他一直不同意女人上船,”安迪继续说,“他们说,他想尽办法,要阻止你们上船,但船长终究比他大。现在,他又开始到处宣扬,说就是因为带了你们上船,我们才会遭到这次噩运。比尔·巴克尔虽然不理他那套,但他说有些人还是信了。不过,他没说是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