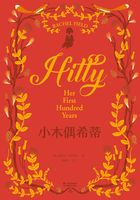
第5章 捕到鲸鱼
好啦,海面终于再次平静下来。雨过天晴后,我觉得海水也比以往更蓝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比那更蓝的海水。此时,我们已经驶入南太平洋。尽管我算不出还要走多少海里,但我们正驶向那个众人皆知的最佳捕鲸地。经历了这场暴风雨,“戴安娜·凯特”号似乎又恢复了神采。漏洞已经补好,安装了新的中桅和中帆。船身不仅重新喷了漆,还彻底整修了一番。铁器上好了油,鱼叉磨得锐利无比,绳子也涂好了焦油。万事俱备,就等瞭望台发现鲸鱼喷水时的那声呼喊了!
这次,菲比·普雷布尔也和船一样形象大变。天气越来越热,她先是脱掉了羊毛衫,又接连脱掉了美利奴羊毛裙、针织长筒袜、法兰绒衬裙,最后连鬈发也剪掉了。全体船员几乎都见证了这场隆重的剪发仪式。他们围在菲比坐的木桶边,监督利哥给她剪头发。船上所有人的头发都是利哥剪的。他使起剪刀来,跟用任何叉鱼工具一样娴熟。等他剪完,菲比的妈妈差点儿没哭出来。
“看看,这就是带她出海的结果!”她痛心地说,“跟刚上船时比,简直就是两个人!”
还有那满脸的雀斑和晒黑的皮肤呢。她爸爸没法反驳,看到妻子不住地摇头,他也只是哈哈一笑。
“涂点儿鲸油就没事了,”他对她说,“现在,她最需要一条马裤。我想,可以让吉姆把安迪那条裤子剪短了给她穿。反正我们还有好几个月才入港,谁会在意她现在啥样!”
于是,尽管她妈妈强烈反对,马裤还是做好了。
我得承认,头一眼看见菲比穿上裤子,我真有些担心,生怕她再也不喜欢木头娃娃了。好在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我,走哪儿都把我带着。所以,我才能这么熟悉那些与鲸鱼有关的术语。对于一个木头娃娃来说,这可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如今,坐在这间古董店里,看着挂在墙上的鲸鱼图片,当年捕鲸的一幕幕,似乎都有点陌生了。每一次,最先传来的,总是上方瞭望台激动人心的叫喊:“鲸鱼喷水啦!”或者,这喊声也可能仅仅是两个字:“喷——啦!”然后,“戴安娜·凯特”号上便忙成一团,我们必须立刻扭转航向,尽量靠近那道喷泉般的白色水柱。与此同时,所有小艇随时待命,只等普雷布尔船长一声令下,就立刻下水捕鲸。有时,进行一次围捕要放出五艘小艇,但更多的时候是三艘。船员们飞快地划着桨,向着那座灰黑色的小山全速前进。看起来,它真像家乡的哈克贝利山,只不过时隐时现,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又出现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位上。
杰里米·福尔杰第一个“叉到”鲸鱼。不过,没人嫉妒他的辉煌战绩。因为他必须要往这头庞然大物身上投好几根鱼叉。受惊的鲸鱼几近发狂,差点掀翻小艇,把他扫进海里。那是头巨大的抹香鲸,足以让任何捕鲸船的船长和船员们垂涎。鲸油大家都有份,所以他们都暗下决心,决不能让这么个大家伙跑了!菲比、安迪和我看着他们放下小艇,迅速驶向目标,溅起阵阵白色浪花。三艘小艇各配五名桨手,他们顶着海上炽热的阳光,整齐划一地划着桨,飞速地离我们而去。
“小伙子们,祝你们交上鲸油运!”普雷布尔船长大喊着,目送他们远去。
我,一个小小的木头娃娃,怎么说得清楚这些事呢!那些小艇比豌豆荚大不了多少。此刻,它们正飞快地划开水面,径直冲向那个灰色的大家伙。鲸鱼时而出现,时而隐没,不仅行踪不定,还时不时喷出一股可怕的冲天水柱!真不敢相信,我居然亲眼看见了那一切!幸运的是,搏斗中的鲸鱼转了好大一个圈,终于游到足以让我们看清大部分过程的地方。安迪紧贴着船舷边的矮栏杆,手搭在额前,竭力分辨小艇上的人影。
“它在那儿!”安迪兴奋地大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菲比也激动得差点把我摔到地上。“看,又喷水啦!快看,那道白色水柱!最前面那艘是杰里米的船,我看到他那件红白衬衫啦!”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菲比紧紧地搂着我,在他身边又蹦又跳。
“那儿,船头那儿。看着吧,他马上就要投叉了!”
桨突然停在半空,稍稍下滑的小艇似乎马上就要消失在那黑亮亮的庞大身躯下。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被迫待在教堂里普雷布尔家坐的长凳下时,那本插图版《圣经》里的画。不知怎的,我竟一直没有把图片上那个巨大的海怪跟眼前这只鲸鱼联系起来。现在我知道了,它们就是同一种生物。而可怜的杰里米,似乎也取代了图片上的那个男人,正被吞进那张可怕的深渊巨口。
但下一刻,我却听到安迪兴奋的高呼:“叉到鲸鱼啦!”
“现在,他们要来个楠塔基特岛雪橇游!”安迪对菲比说,“意思是,一旦鱼叉稳稳地叉在鲸鱼身上,他们只需放出绳子,跟它周旋到底就行啦。”
“可我现在看不到鲸鱼在哪儿了。”菲比抗议道。
“它马上就会上来,”安迪向她保证,“它已经被勾住,跑不远啦!”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那个庞大的黑色身躯又从水里钻了出来。这一次,它拼命挣扎,试图甩掉自己身上的钳制。那巨大的侧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一边喷出更多的水,一边疯狂地摆动尾巴,在海面上搅起圈圈白色漩涡。我已经说不清它到底拖着小艇游了多久,钻进水里、又更加狂躁地冲出水面多少回。不过,当汩汩血水出现在翻卷的白色泡沫中时,“戴安娜·凯特”号上所有的观战者都爆发出一阵欢呼:
“鲸鱼不行啦,它快完蛋了!”
果然,没过多久,鲸鱼的挣扎就渐渐变弱了。接着,人们也都住了手。它那庞大的身躯一点点浮出水面,接着慢慢翻转过去,直到露出锐利的黑色鱼鳍。甲板上的人们又是一阵欢呼,小艇上也接连传来欢呼声。
“很好,我们抓到它啦!”普雷布尔船长转向妻子,满意地说,“你看,能不能准备点儿特别的东西,给我们庆祝庆祝啊!”
切割工作第二天就开始了,我也因此对鲸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即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能清楚地记得鲸鱼摊开在甲板上的样子。第一次围捕后的那个早晨,菲比把我带到甲板上时,船员们正在把一个小平台放下来。然后,他们便拿着长钩、大刀和其他各种锋利无比、让我一看就害怕的工具,站到了台子上。他们用绳子和各种铁链吊起鲸鱼,便像削苹果一样,把鲸脂一片片地剥下来。但鲸鱼毕竟不是苹果,等到把片好的鲸鱼抬上甲板,放进提炼炉,鲸油已经流得满甲板都是。我都开始怀疑,再这么下去还能剩下多少?整艘船都是鲸油的味道,但除了普雷布尔太太,没有一个人在意。她说,她一辈子都没闻过如此难闻的味道,没见过这么油腻的地方。不过,船员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说这就叫“鲸油运”!他们各有分工,一些负责升吊鲸鱼和继续切割,一些忙着把大块的鲸脂切碎、扔进锅里,还有一些则挑出锅里的残渣作燃料,让炉火日夜不熄。
白天,又浓又黑的烟腾起,仿佛一把奇怪的伞,笼罩在我们头顶。到了夜晚,炉子里暗红的火焰让船上变得更加油腻和闷热。船员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中间只轮着休息几个小时。
几天后,普雷布尔船长下来吃晚饭时对我们说:“赶紧弄完这一头,好去捕下一头”。长时间的切割工作,让他的手僵硬得几乎拿不住刀叉。
甚至安迪,都被拉去干切割和搬运的活儿。他像其他人一样光着膀子,卷起裤腿儿,神气活现地跑来跑去。有时,他整张脸都被油烟熏得漆黑。这让他那双蓝眼睛显得十分奇怪,再加上他那头火红的头发,就更奇怪了!菲比和我是决不允许靠近鲸油提炼炉半步的,对此,普雷布尔船长尤为坚决。
“别在这碍事,会被烫伤的。”他对菲比说。
于是,我们便坐到一只旧木桶上。虽然离炼油炉还有几码,但已经足够看清大部分的工作。没离那么近让我松了口气,我可不想跟油脂条一起滑进去,在那样滚烫的油锅里游泳!
这头鲸鱼才刚刚炼完,他们就出发去捕下一头了。有时候,的确能看到一群鲸鱼,他们便会一次猎杀好几头,将它们绑在船后拖着走。看到这些庞大的灰色身躯插着带小旗的铁叉,表明这是我们的财产,感觉可真奇怪。此时,还有两条捕鲸船也到达了这片海域。尽管彼此相隔好几英里,但船与船之间还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船员们开始讨论要不要跟他们来场“联欢”。如今,人们再也听不到这个词了,但在当时,航海的人却经常用到这个词,意思是海上船只之间的友好往来。所有人都恨不得马上开始联欢,只有普雷布尔船长坚持,一定要把船上的鲸鱼切割完才考虑这事儿。于是,有些人开始抱怨,帕奇更是黑着脸,一副他才是船长的派头。他不当值的时候,便常常和几个船员聚在一起说个没完。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准没什么好事。
遗憾的是,最后一头鲸鱼切割完三分之一多一点儿,我们刚把鱼肉放进提炼炉,原本要与我们“联欢”的那艘船招呼都没打一声,就开走了。船长和大副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船员们也迅速分成两派,要辨出谁对谁错。帕奇坚持船员有权请假,去别的船参加“联欢”,而支持船长的人则认为那样停工不仅浪费时间,还可能损失很多鲸脂,最后影响到大家分得的份额。船长镇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模样。但晚上回到舱中,我还是听到他跟妻子谈起这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找帕奇做大副,”他对她说,“他的推荐信特别棒,对这条船的投资又比其他申请人多,我当时还觉得能找到他挺幸运的,但最近他的表现实在让人讨厌!”
“哦,达内尔,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普雷布尔太太回答,“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人不怀好意。我从没见过谁的眼睛像他那样狡猾卑劣、滴溜溜乱转的。但是,也还轮不到我来批评你的手下。”
“他很有本事,”船长继续说,“不可否认,他对结绳掌舵之类的事儿还是挺在行的。不过,要是能快点儿捕到最后一头鲸,装满油桶,早日返航,我一定会十分高兴!”
“我可高兴不起来。”他的妻子叹了口气。
但船长在甲板上的表现还是不偏不倚,谁都猜不透他的心思。
普雷布尔太太尽心尽力地打理着厨房。为了保证曲奇和姜饼的供应,她把桶里的糖浆和蜂蜜都刮得干干净净,并随时做好准备,为船员们煎炸他们捉到的鲜鱼。终于,我们捕到了最后、也是最好的一头抹香鲸。所有小艇都被派了出去,其中两艘还差不多同时到达鲸鱼身边。这时,便出了点岔子。两艘小艇的船员都没服从各自艇上负责人的命令,至少,他们回到“戴安娜·凯特”号上后是这么说的。总之,大家都在争论到底是谁第一个叉中鲸鱼,是杰里米呢,还是另一个人?鉴于第一个叉中鲸鱼的人能多分一份鲸油,争论双方便互不相让。他们扔下手头的工作,吵闹不休。普雷布尔船长听说后,宣布这次谁都不能多分。这下,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
尽管闹得很不愉快,但我们谁都没想到,一场致命的危险会来得这么突然。我更是觉得非常意外,因为我早已把这个木头和帆布组成的世界,当成跟普雷布尔家农舍一样安全的地方。
我想,灾难准是在午夜时分发生的。至少,甲板上传来尖叫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时,外面还是漆黑一片。几乎就在同时,我们听到一声大喊:“所有人都到甲板上来!”尽管猜不透如此平静的夜晚,这片热带海域会出什么事,但这句话还是意味着船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菲比被吵醒了,也想上去看看,却被她妈妈阻止了。普雷布尔太太说她们上去只会添乱。爸爸只要一得空,肯定会下来找她们。于是,我们三个就在闷热的黑暗中,焦急地等待着。
很快,普雷布尔船长出现在门口,双眼通红,还泪汪汪的。
“达内尔,出什么事啦?”普雷布尔太太大声问道。
“船着火了!”他尽量平静地回答,“准是从下面放鲸油的舱里烧起来的,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恐怕火势正在蔓延,但我们一定会尽力扑救!”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船头和中间已经烧着,但暂时还烧不到这儿来。我们已经把湿帆布盖了上去。有时,这样做能灭火。但看这火势,这次恐怕压不住了!”
“而且,船上还到处都是鲸油……”普雷布尔太太猛地拽住他,那一刻,她似乎比在铺位上坐直身子、专心聆听的菲比还小,“噢,达内尔,我们还有机会吗!”
“放心,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决不放弃。”他回答道,“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离开我的船!但若到了最坏最坏的地步,我们还是得乘小艇逃生。凯特,现在,船上还是这里比较安全,所以你别吓得到处乱跑。”
“谁说我要乱跑了!”她一下子又振作起来,“菲比和我都会做好准备,随时等你发话。”
“最好也收拾点东西,”他提醒她,“收拾点你和菲比或许用得着的东西,万一——”他猛地住了口,转身走向门口。即便油灯昏暗,我也看出他那日晒烟熏的脸,有多么憔悴和苍白。不过,他还是挺起胸膛,走上了甲板。随后,我们便听见他在上面大吼着发号施令的声音和船员们服从号令、急促跑开的脚步声。
菲比和妈妈开始穿衣服,然后就忙着收拾东西。普雷布尔太太镇定地在床铺和两只箱子间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包着行李,系好又解开,解开又系好,确保每样东西都捆得结结实实。菲比学着妈妈的样子,也开始收拾我的东西。她先把蓝色水手储物箱、骨雕小凳和我的小吊床都放进了藤条箱,然后便为我穿好衣服,把我也放了进去。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了无数个问题:妈妈,船是不是很快就要被大火烧光了?小艇能装得下所有人吗?如果离开大船,我们还能去哪儿呢?妈妈,你觉得是不是有人故意在鲸油舱放火啊?所有问题,普雷布尔太太也跟菲比一样,什么都不清楚。
不久,安迪下到船舱来,但他也没带来什么好消息。尽管大家全力扑救,火势还是蔓延开了。盖到火上的湿帆布只弄出一股呛人的浓烟,一转眼,火苗又从新的地方钻了出来。
“他们都说船已经没救了。”安迪断言,“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还能在船上待多久,以及还能不能把它开到最容易获救的地方。老帕奇觉得他比船长懂得多,有些人已经站到他那边去了。”
普雷布尔太太静静地听他说完,又收拾起东西来。
她对安迪说:“你把这包东西拿好,跟我走!菲比,要是有什么麻烦,我可不想被困死在这里。”
上去后,我们发现普雷布尔船长和帕奇正拿着海图和地图,在甲板室里吵得不可开交。大部分船员都围在他俩身边。我们站在扶梯升降口,听他们说话。菲比挎着篮子。我躺在篮子里,能清楚地看见大海、天空和船上熟悉的身影。天边已经露出一抹淡淡的粉色,但热带地区的星星仍在头顶闪着惨白的幽光。离地平线最近的几颗,还在水面上扯出了道道银光。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头上的帆也纹丝不动,“戴安娜·凯特”号简直寸步难行。我们看不见火焰,因为上面的湿帆布还没有揭开。但甲板之间不断冒出滚滚浓烟,涌向鲸油提炼炉的方向,熏得人眼泪汪汪,喉咙生疼。我再次发现,当个不用受烟熏之苦的木头娃娃可真好!
我已经记不清船长和帕奇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他们说的很多话我都不懂,只能从他们的表情和声音,看出他们吵得很厉害。显然,弃船已是迟早的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把它开到哪儿,才最有可能被过往船只搭救。帕奇大副确定了一个方向,普雷布尔船长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几乎所有船员都支持帕奇,认为既然情势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他们有权参与决策,尽力拯救自己。普雷布尔船长不是个会轻易妥协的人,另外,他还坚持认为:在船上待得越久,获救的机会就越大。然后才是去那些他刚在海图上标出来的小岛。可帕奇宣称他找的小岛更好。他越吵越激动,赌咒发誓地说普雷布尔船长的计划无异于谋杀,他绝对不会遵从。船员们也开始嘀咕,一个个脸拉得老长,抵触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很快,局势就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有几个人拒绝爬上桅杆,也有人不服从船长的命令。本该好好利用的宝贵时间,就那么被一分一秒地浪费掉了。烟雾仍不停地往上冒,越来越浓,越来越黑。安迪抱怨说甲板都快把他的光脚给烤熟了。普雷布尔太太则一直紧握着菲比的手,一眨不眨地盯着丈夫的脸。
突然,我看见船长合上了手里的海图,一言不发地将它揣进胸前的口袋,然后再次转向帕奇,说:
“你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吧!”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奇怪,我差点儿没听出那是他,“放下小艇逃命去吧,你们这帮讨厌的家伙!我宁愿和我的人葬身海底,也不想再跟你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吵下去!坐上小艇赶紧走,越快越好!”
“哦,达内尔!”我听见他妻子压低声音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啊!”
但她并没有大声反对,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帕奇和其他几个船员匆匆去放小艇。
“凯特,跟我待在这儿别动!”我听见船长发号施令,仿佛他的家人也成了船员,“安迪,菲比,你俩也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准离开!”
我们聚在甲板室旁,周围尽是跑来跑去要弃船逃生的人。但杰里米、鲁本和比尔·巴克尔还是留下来,站到了船长这一边。
“我们听您的,船长。”他们说,“只要横梁不断,我们就不下船!”
太阳像火球般从海面上升起。等到五艘小艇都下了水,它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但这一次,大船上没有欢呼声,小艇上也没有应答的高喊声。我们无声地伫立着,看着他们渐行渐远。普雷布尔太太的嘴唇不住地颤抖,很像菲比要哭之前的样子。每艘小艇都张开了帆,在蔚蓝大海的映衬下,它们就像一张张白色的三角纸片。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次分别,忘不了离开时,那些人脸上冷漠的表情。他们头也不回地走了,其中还有很多是我们的朋友。我常常想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是过得比我们好,还是像船长认为的那样,已经遭遇不测?
没有任何一支笔,至少没有任何一支握在木头娃娃手中的笔,能描述出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在船尾一个临时搭起的帆布帐篷里等着,以躲避迅速蔓延的浓烟和热浪。与此同时,杰里米他们三个和船长一起,使出浑身解数,驾驶着船往西南方开,寻找船长所说的那片群岛。让一艘着火的船不沉下去已经很不容易,还要让它驶向既定的方向就更难了。普雷布尔船长和他们三个拼尽了全力,最终还是放弃了。
最后,船长说:“噢,凯特,赶紧和菲比做好准备。”他脸上全是一道道烟尘和汗水,“船尾还有几艘船。比尔,下去把他们留下的食物和水拿来。”
他们放下一架绳梯。杰里米翻过船舷爬上去时,绳梯晃动得非常厉害。
“天哪!”菲比的妈妈沮丧地喊道,“这我可爬不下去!”
一时间,仿佛那梯子比大火还可怕。她满怀希望地看了眼那艘还没被放下去的小艇,但杰里米对她说,坐那艘大点儿的小艇会更舒服一点。
“抓住我,夫人!”他说,“我来帮你翻过船舷。把裙子提起来,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礼节啦!”
船长也过来鼓励她。于是,她先伸出一只手,接着是另一只,终于翻了过去。杰里米护在前方,以免她掉下水。
安迪和比尔·巴克尔拿了几桶水和食物上来,普雷布尔船长拿了他的小罗盘、灯笼,几样工具和航海日志。他的面色比以往都要凝重,双眼又红又肿,一道长长的煤渍像伤疤一样划过他半边脸颊。
“比尔,”他发出了离船前的最后一道命令,“你跟杰里米带上安迪和剩余物资坐那艘小艇。鲁本和我照顾女士们。”尽管身处险境,但听到我能同菲比和普雷布尔太太在一起,我还是很高兴。“你们要尽量靠近我们,”他叮嘱道,“如果我料得没错,天黑前,我们应该就能看到一座小岛。”
说话间,菲比把盛着我的篮子往一个装腌肉的大木桶上一放,就要跑回去找一块她刚才落下的鲸鱼骨雕。显然,她爸爸怕她走近火线,连忙跟上去把她抱回来,然后挤到船边,把她递给杰里米,放上了小艇。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仿佛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不过,那时“戴安娜·凯特”号上的人已经连眨眼的心情都没有了。没能跟菲比一起走让我很失望,但我想,自己正坐在一个装补给的桶上,所以肯定会被搬上另一艘小艇。坦白说,我等得很是焦躁不安,毕竟,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有一次,我似乎听见菲比在下面大声叫唤,但其他人要么在忙着放下第二艘小艇,要么就是噪音太大,根本没人没听见她的喊话。我知道她一定是在找我,但这也并没有让我感觉好受些。
我听见船长仍在发号施令,然后比尔·巴克尔就开始往第二艘小艇上装东西。我时刻盼望着快点儿轮到我,可这一刻永远都不会来了。因为他正要回来拿我坐着的这个桶和另外一个甚至还要大一些的桶时,下面传来喊声,叫他快点儿下去,否则就来不及了。火焰,比人还高的火焰猛地从鲸油提炼炉两侧腾起,瞬间就吞没了旁边的桅杆。剩下的人也飞快地撤离了。看着他们消失在船舷那头,我知道,自己最后一丝获救的希望也破灭了。
简直不敢相信,我就这样被抛下了!然而,两艘小艇已经越划越远。我甚至还能辨认出上面的人影:穿着蓝衬衫的是安迪,穿着红白衬衫的是杰里米,那个带着灰色海狸帽的是普雷布尔太太,她肯定舍不下那顶帽子。有一次,我确定自己看见菲比用手指着大船,我知道她在找我。那一刻,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然而,小艇还是继续往前划着,没有回头。很快,船上的浓烟便完全遮住了我的视线。这下,我真觉得死亡就在眼前了。还有什么力量,能在熊熊大火中拯救一块木头呢?即便是花楸木,也难以幸免啊!
“戴安娜·凯特”号正在迅速变成一个火炉。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火舌瞬间便爬上了桅杆,速度简直比任何一名船员都快。尽管很害怕,但看着那些熊熊燃烧的桅杆,我竟觉得,它们跟秋天波特兰大道两旁那些树一样明艳。燃烧的噼啪声和木头的断裂声比热浪还吓人,我听到了下面横梁的断裂声,甚至我身上的钉子,都感觉到了那种震颤——天哪,一块结实的木头就这样完了!尽管被雕成娃娃的样子,还穿上了漂亮的衣服,但我也是块木头啊!面对这个共同的敌人,我怎么逃得出它的魔掌!
我努力去想凉爽、快乐的事——普雷布尔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松树上亮晶晶的雪花;开满花的丁香树和苹果树;聚会山顶。餐具架上蓝白相间的瓷器,还有那些蟋蟀长鸣的凉爽秋夜。现在,我真羡慕它们啊,冻死总比烧成灰强!要是能转过身,不去看那越逼越近的火舌,说不定我还能好受些。但菲比把篮子放得太满了,卡得我一动也不能动。
“现在,只有奇迹才能救我了。”我对自己说。
我曾经听别人说过这话,但看起来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船都逃不过这一劫,我一个木头娃娃还奢望什么!不过,我只能自我安慰:我好歹是花楸木做的,“戴安娜·凯特”号可不是!
就在我脸上的油彩快要滋滋地燃起来时,船身猛地倾斜了一下。我想,肯定是哪儿的支柱被烧断了。不管怎样,船疯狂地倒向一边,巨大的冲力猛地掀翻了我坐的这个木桶。我从篮子里飞了出来,像块从弹弓里射出去的鹅卵石般,越过横栏,掉进了水里。
“好吧,”我记得,栽进水里的一刹那,我还在想,“至少不会被烧成灰了。对木头来说,水总比火好。我还听说,盐是很不错的防腐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