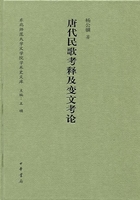
第九篇 贫穷实可怜
贫穷实可怜,
饥寒肚露地,
户役一概差①,
不辨(办)棒下死②。
宁可出头坐(走),
谁肯被鞭耻(笞)③;
何为 (拋)宅走?
(拋)宅走?
良由不得止(已)④。
〔考释〕
①“户役一概差”
“户役”,按户派的赋役。唐时,户分九等,按等分派赋役名为“户役”。
《唐会要》卷八十五:
“武德九年(625),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有差科,先从高等。”
《唐律疏议》第十三:
“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
但实际上,定户等第是不均平的。开元时,地主及富商大多与官府交结(考释见本类第七篇《富饶田舍儿》),被定为下等户;而贫户反而成为赋役的主要负担者。
《唐会要》卷八十五: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
由此可知,唐玄宗时,户口籍帐不实,富人定下等,而穷人却定高等。因此,虽然诗作者已贫穷到“饥寒肚露地”的地步,但仍要担负“户役一概差”。
②“不办棒下死”
“办”为“承办”、“承担”。“不办棒下死”,意为“如不能承担户役一概差,则免不了死于官府的大棒之下”。
“棒”即“杆棒”、“棍”,古时称作“殳”,汉时又名“金吾”(两端有铜箍的杆棒),原是兵器之一种。
《诗经·伯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案:古之丈二约合于今之七尺二寸。)
《说文解字》:
“殳,以杸殊人也。……建于兵车,车旅贲以先驱。”
崔豹《古今注舆服》:
“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之金吾。”
《三国志》钟会传:
“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以次棒杀。”
《周书》王罴传:
“(王罴)镇华州。(齐神武派人袭城,罴不觉,闻外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
《抱朴子》:
“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乃多作劲木白棒,选异力精卒五千人……”
《新唐书》李嗣业传:
“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宋史》张威传:
“(威)临阵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每战不操他兵(器),有木棒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
由此可知,古之“棒”乃是兵器,并非“刑具”。但从魏晋之后,各朝统治阶级本于“乱世用严刑”,往往用军用棒拷打人民。隋初,文帝曾下诏禁止官府使用“棒罚”。唐太宗所制定的“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其中并无“棒刑”。虽然如此,但自则天朝之后,贪官酷吏仍常常使用“大棒”拷打人民。
《三国志》武帝纪注: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隋书》刑法志:
“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文宣于是令守宰各设棒,以诛属请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轨奏曰:‘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
“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至是尽除苛惨之法。”
《唐律疏议》卷一:
“五刑:笞、杖、徒、流、死。”(案:笞刑,古用竹,唐时用荊条;杖刑,即汉时之鞭刑,隋唐时改用荊木。)
卷二十九
“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疏〕议曰:……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朝野佥载》:
“周侍御史侯思止,凡推勘,杀戮甚众,……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知,所谓“棒打”乃是“法外酷刑”;诗所说“棒下死”,意为“非刑拷打致死”。
据“大唐律令”,“户役课税之物违限不克者”,“户主笞四十”。“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刑;“笞四十”是“笞刑五等”中的第四等。
《唐律疏议》卷十三:
“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疏〕议曰:‘输课税之物’谓租、调及庸,地租,杂税之类。物有头数,输有期限,而违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假有当里之内,征百石物,十斛不充笞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
由此看来,“不办”“户役一概差”也并不是犯了什么大罪。然而本诗却说“户役一概差,不办棒下死”。
据“大唐律令”,州县官员断罪皆须遵循律令正文,“违者笞三十”;如“因公事捶人致死”,则从“过失杀人罪”。此外,“大唐律”明文规定,严禁“用棒拷打”人犯,官员违者“杖一百”;“致人死者,徒二年”。
《唐律疏议》卷二十九: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疏〕议曰:‘临统案验之官,情不挟私,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各依过失杀人法,各征铜一百二十斤入死家。”
“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徒二年。〔疏〕议曰:‘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谓拷囚于法杖(笞与杖)之外,或以绳悬缚,或用棒拷打……犯者合杖一百……致死者,徒二年。”
不难看出,虽然“大唐律”中规定的条文很严格,文字明确并无“但书”,但当时官僚却并未受到约束。本篇民歌反映了这点:当时官僚并不“遵循律令格式正文断罪”,该处“笞刑”的,却施用“非刑拷打”;该处轻刑“笞四十”的,却用“棒拷打致死”,“擅自捶杀人命”。
由此可知,本篇民歌揭露了唐封建社会法律的伪善,可供那些称赞“大唐律”的“法学家”参考。
③“谁肯被鞭笞”
“笞”是唐时“五刑”之一。
唐前期“税制”是与“授田制”结合并行的。这就是“有丁即有田,有丁口即有户籍,有户籍即有赋役”,但到玄宗即位前后,由于土地兼并,情况大变。
《新唐书》食货志二: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由此可知,自开元以后,富升贫降,贫苦农民失去田地,但由于“户籍久未更造”,因此户籍“籍帐”上仍挂有丁名,仍须向官家交纳“庸调”。
《文献通考》卷三:
“(唐)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买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按籍(户籍计帐)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
籍帐有名而无地的农民无法完纳赋税,于是从武则天朝之后,官府便以鞭笞酷刑“比限催科”。
《新唐书》狄仁杰传:
“调发烦重,伤破家产,剔屋卖田。……又官吏侵渔,州县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
“自数年已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杨崇礼(开元中)为太府卿,清严善勾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转输纳欠,折沽渍损,必令征送。天下州县征财帛,四时不止。”
本篇所写的便是一个贫穷农民,他没有生产资料(田地),但户籍计帐上却有名,因此不得不负担“户役一概差”。他无力应付,便要“被鞭笞”,甚至“棒下死”。于是,“宁可出头走”,他不得不“拋宅”逃亡。所谓“抛宅走”,也正说明他已无田地,只有“宅”可抛了。
不论贫富和有无田地,只根据户籍计帐上的丁额征派赋役,是开元、天宝时的暴政之一。杜甫《咏怀五百字》中所说的“鞭挞有夫家,聚敛贡城阙”,也正是指没有田产只挂丁名(有夫家)的贫穷人而言。
天宝之后,唐朝廷不得不改变税法,废除以“户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税法,改行田亩所得税(两税制):“人无(不论)丁中(壮丁、中男),以贫富为差。”
④“何为拋宅走,良由不得已”
武后朝后期,人民已经不断逃亡。到玄宗即位之后,逃亡日益严重,“禁逃亡”和“招逃户”成为当时官府的主要工作,并将这一工作作为官员考课的主要项目。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开元后,赋役繁重,豪猾兼并,……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间,十一二矣(十分之一、二):盖汉魏以来浮户流人之类也。(天宝时)……客户倍于往时。”
据史载,开元十二年前后,全国户数为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其中逃户有八十余万户。这说明,当时近八分之一的人在逃亡。从当时人柳芳的记述中看来,开元十二年以来,逃亡不是减少,而是逐渐增加。
本诗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