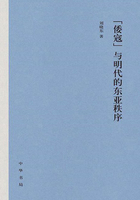
序言
作为一股横行于东亚沿海地区的海盗走私力量,“倭寇”曾在14—16世纪间给相关国家和区域带去过不少亦不小的劫掠。它不但构成了元末及明代中国政权与日本进行正常经贸交往的破坏性因素,也成为朝鲜民众至今难以平复的历史痛点。惟此,不仅批判性的个案梳理和综合研究早已车载斗量,某些站位超然且试图将东亚经贸史放到全球脉络中进行重新考察的所谓“近代契机”说,也风靡经年,不一而足。然而,就历史源头而言,有文字记载的“倭”人外侵行动最早应发生在4世纪末,所以有人主张,“倭寇”的概念当始现于5世纪初高句丽“好太王碑”(广开土王碑),所谓“倭以辛卯年来渡海”和“倭寇溃败”等碑文是也。到了后来,才先后滋生有高丽时代、洪武时期、朝鲜时代、嘉靖时期的“倭寇”以及蔓延到吕宋岛和南洋等地者不一。问题是,作为海上“非组织力量”的“倭寇”,是如何与“日本”国本身划上等号的?“倭寇”的构成者当中果真只有日本人和中国人吗?而进一步的追问是,以往对“倭寇”充满情绪色彩的研究,是否已拥有了与之相关者都不难接受的客观属性?
刘晓东教授的新作《“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下简称“刘著”),将由中华书局梓行。这是一部不积多年之功无法完成的力作,而且倘因应以上设问来观察这部书,那么至少在现阶段,我以为刘著已代表了中国大陆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新深度和新高度。
对“倭寇=日本”的自明般等式问题,以往鲜有中国学者能真正沉下心来去认真研究之。这至少受限于两大缺乏:一是对于明代的对日本对朝鲜交涉过程缺乏系统的爬梳和细心的检视,二是对日本和朝鲜内部的分合变化和官民差异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去做长期的史志阅读、内外甄别和规律抽取。刘著显然做到了这一点。知己知彼之所以能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因为作者深谙明史的典要实录,又熟稔日本和朝鲜的相关记载。于是,其对“倭寇”的审视,便既有对元末明初的邻交困局交代,又有对同时代日本和朝鲜的内情把握,既甄别了民间与官方的不同维度,也厘清了经济和政治的各自动机。与此同时,洪武期的倭·日齐观、永乐期的倭·日分视以及嘉靖、万历期的倭·日混一等,也都在如此脉络上逼近了中方体验下的历史认识本然。它整理了“倭寇”由事实到符号的演变经纬,也揭橥了“倭寇”由“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的展开过程。
刘著的“倭寇”定义——“由一部分明朝、日本及朝鲜人所组成的海上劫掠与走私群体”,确证了从事如此活动的“濒海之民”当中,其实还有朝鲜人这一事实。这项工作,不但还原了“倭寇”现象在前近代东亚区域普遍存在的真相,也暗示朝韩学者对朝鲜人介入海盗问题一向讳莫如深的态度其实并无必要。一俟回到历史现场便不难发现,三国“倭寇”现象固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东亚区域秩序体系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但东亚诸国围绕该问题所展开的各类文武交涉,也同时反映了三国政权在认同与维护区域秩序上所做出的各自努力。
然而重要的还是回到核心概念本身。在东亚历史上,“倭寇”概念其实内含有强烈的恩怨情仇色彩。尽管1592—1597年发生在三国间的那场战争可以被明朝官方冷静地记录为“万历朝鲜之役”,但学界和民间的私下称谓却是与朝鲜“壬辰丁酉倭乱”鲜有二致的“壬辰倭乱”。这意味着,倘继续用情绪性笔法来处理已成静物的历史事件,研究者便极有可能会重蹈以态度叙事来代替结论观点的学术大忌,并由此而失去史学应有的理性和客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刘著的学术贡献或许更在于,经由其细密的资料比对和大数据处理后的“倭寇”,已首次从一个情绪性概念上升为学术性概念。于是,在通过前近代东亚秩序结构来审视“倭乱”问题时,刘著并没有因壬辰战争中的驰援对象国是朝鲜就对其倭情遮蔽行为所导致的被动战局给予过些许回护,也没有把永乐帝当年所谓“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等对日赞许,因后来的敌对关系便刻意抹杀。如此研究站位,应该潜藏着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壬辰战争”中丰臣秀吉的军队是否可以被视为“倭寇”的问题,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如果我们把“倭寇”限定为“由一部分明朝、日本及朝鲜人所组成的海上劫掠与走私群体”,那么,丰臣军队中并无明、朝兵弁以及其行动目的远不止于“劫掠走私”等事实,表明该阶段明朝对“倭·日”的等量齐观,还未能褪去笼而统之的情绪化色彩。同样,时间晚于“壬辰战争”近三十年的江户人士山鹿素行对“倭寇”的相关界定与指陈,似乎也并非是丰臣所动员的“官兵”:“外朝之海防,唯以倭寇为要。倭寇者何?乃西州边民掠彼者,非官兵之寇也。”这些,或许可以为“倭寇”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某种新的认识维度亦未可知。
私以为,学有所成,莫非用心一也。且未有经年之披检,谅亦难成此书。结稿后,晓东乃征余小序。我初习明史,本无格忝侧,又不敢以不敏辞,故踯躅再三,方惴惴然续貂于后。倘识者能阶此以入堂奥,则作者幸甚,学界幸甚。
韩东育
2018年1月8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