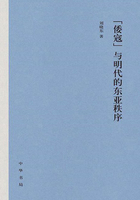
前言
近年来,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注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实现这一愿景,除却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整备与融接外,历史文化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发生于16世纪前后的“倭寇”问题,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面向未来,都是东亚各国难以逾越的一个历史话题。
对“倭寇”问题的研究,20世纪初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直至今天仍是一个热点,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日本的山根幸夫、三田村泰助、田中健夫,韩国的李铉淙、韩文钟、李领,中国台湾的郑樑生、王仪,以及大陆的陈懋恒、李光璧、林仁川、戴裔瑄、汪向荣、范中义等 。不过,由于诸种因素的限制,以往的研究也着实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方面。
。不过,由于诸种因素的限制,以往的研究也着实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方面。
(一)何谓“倭寇”
所谓“倭寇”,字面而言是指日本海盗。但16世纪前后“倭寇”的内涵却并非如此简单。就其实质而言,主要是由一部分明朝、日本及朝鲜人组成的海上劫掠与走私群体。正如嘉靖年间的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所云:“夫海贼称乱,起于缘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这一问题历经学界多年探讨,已基本得以解明。
这一问题历经学界多年探讨,已基本得以解明。
但由于受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念的过度影响,各国研究者仍大多出于自我防御心态,常常表现出一种封闭式的自我表述。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令我们极大忽视了16世纪前后“倭寇”形成的复杂性,及隐含其下的东亚社会难以割断的内在关联性。于是,我们常将“倭寇”置于某一国的视阈内予以关注,而忽略了其活动场域——海洋的相对开放性;或者过度强调海洋的开放性,将倭寇看作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境界人”(边际人) ,而多少忽视了海洋故事多是陆地问题的一种延伸。就像王直(又作“汪直”)那样自称为“徽王”的海上巨魁,无论是将其单纯看作中国东南沿海海商的代表,还是日本封建大名的附庸,或者是独立的海上劫掠势力,无疑都过于简单化了。至少在接受明政府招安这件事情上,他的“自我意识”显然是屈从了他的“国家认知”的。事实上,所谓东亚地区“境界人”国家意识的转换,往往发生在对陆地国家的“归化”之后。
,而多少忽视了海洋故事多是陆地问题的一种延伸。就像王直(又作“汪直”)那样自称为“徽王”的海上巨魁,无论是将其单纯看作中国东南沿海海商的代表,还是日本封建大名的附庸,或者是独立的海上劫掠势力,无疑都过于简单化了。至少在接受明政府招安这件事情上,他的“自我意识”显然是屈从了他的“国家认知”的。事实上,所谓东亚地区“境界人”国家意识的转换,往往发生在对陆地国家的“归化”之后。
从东亚整体的视角来看,“倭寇”既非脱离了国家理念而呈现出极强“自我意识”的具有较强政治诉求的社会群体,也非从属于某一单独国度的海上势力集团。而是在东亚各国自身社会变迁及其交互影响的促动下,一部分来自明朝、日本、朝鲜的濒海之民,为谋求经济利益连接而成的以海洋为舞台、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的民间劫掠与走私群体。因而“倭寇”不能简单与“日本”等量齐观,更非国家之间的一种对立形态。不过,他们的共同行动,确实给东亚诸国的国家关系以及东亚政治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与挑战。
从这一角度来说,对“倭寇”问题的理解,也需要从民间和官方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思考,前者侧重于经济,后者侧重于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清“倭寇”与“国家”、“朝贡贸易”与“民间私贸”的联系与区别。尤其在我们已将两者关联过久,诸如过度强调“朝贡贸易”与“民间私贸”的经济共性而忽视其政治差异性的时候,适当将两者分离开来,放置于不同的范畴予以观察,或许另有一番意义所在。就像嘉靖二十七年入驻宁波嘉宾馆的日本策彦周良朝贡使团,与盘踞港外不远处双屿港的“倭寇”,其历史角色与内涵显然是不相同的。至少,策彦周良在面对朱纨的诘问时,毫不犹豫地否决了那些“倭寇”与日本国王及自身的关联性。而朱纨对双屿港的“倭寇”进行了彻底剿灭,却将日本贡使送到了北京面圣。
(二)明代的“倭寇”认知与记忆
16世纪前后,尤其是嘉靖年间,大倭寇常被视为明朝与日本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但通过对《明实录》这一颇具代表性的官方文书中关于“倭寇”相关语汇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至少从明代官方的角度来看,“倭寇”等同于“日本”的认识理念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洪武时期基于重构东亚封贡体制及宣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朱元璋在最初的对日诏书中,采取了将“倭寇”与“日本”相关联的督促策略。随着双方交涉的逐渐展开,尤其是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与日本“封贡”关系的日渐确立,明朝官方意识形态中基本采取了“倭寇”与“日本”两分的看法。嘉靖初年的“宁波争贡”事件,及后来“大倭寇”的兴起,对明代官方“日本观”的转化产生了较大促动,但还未从根本上将“倭寇”与“日本”全然等同视之。万历时期,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及其对东亚区域秩序的挑战,使明朝君臣不得不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来思考对日关系,此时的官方语境中,也基本确立起了“倭寇”=“日本”的理念。
事实上,嘉靖时期的抗倭名臣唐顺之,在其所作《日本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晚明士林对“北虏”与“南倭”的情绪差异,也多少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点。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晚明士人的日本观虽不乏“趋恶”的一面,但基本尚处于可接受的华夷层级秩序的维度之内。不过,基于战争的矛盾体悟,一部分晚明士人理解日本的视点已开始超越了传统的“同文”层面,而关注到了“武”的层面,并促发了晚明重新认识日本思潮的兴起。
万历时期“壬辰之役”的发生,则对明代士人的日本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通过对嘉靖时期“旧倭”的梳理以应对万历时期“新倭”的挑战,成为此时期士林日本研究热潮兴起的重要推动力。《虔台倭纂》一书的形成,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倭寇”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的转化,就是这种背景下的认识产物。于此之中,“旧倭”与“新倭”被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并被赋予了更强的国家与民族对立的色彩,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晚明士人“日本”与“倭寇”认知的根本性转化。
恐怕也正是因为如此,检诸南明士人关于隆武朝周崔芝“乞师”日本的种种史载,不难发现对于是否乞师日本,南明政权内部确实有所争论,但这些争论几乎都回避了“倭寇”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换言之,在南明士人关于乞师日本的历史叙事中,对“倭寇”问题几乎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性的失忆。这种刻意式的“失忆”,无疑源于“倭寇”记忆给南明士人带来的道德紧张感。
的确,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嘉靖“大倭寇”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因而也有一些海外学者主张用“和寇”“海盗”等语汇取代“倭寇”一词。但若从历史认知与历史记忆的层面思考,这种复杂性恰恰说明了“倭寇”这一语汇深刻的历史内涵及其不可改变性。因为“倭寇”这一历史语汇及其历史记忆的演变,本身就是东亚区域交互认知的重要历史。
(三)“倭寇”问题与东亚交涉
近代之前的东亚地区,至迟在14世纪便已形成了一个以“华夷理念”为基础、“宗藩体制”为表象、“朝贡贸易”为载体的区域社会秩序体系。“倭寇”正是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与体系下,并集中凸现了16世纪东亚地区所面临的秩序整合问题的特殊历史现象。“倭寇”问题的产生,着实从一个层面揭示出了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结构缺陷,及其渐趋解体的历史趋向。但却并不能由此而简单否定前近代东亚区域秩序的历史合理性及其伦理性。
事实上,早在明朝建国伊始,便确立起了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理念。围绕“禁倭”问题展开,而以“申交”为目的的明朝与日本之间的最初交涉,实际上就是体现洪武君臣践行这一理念的一个微观侧面。也正因为如此,从国家政治的层面来看,16世纪前后的“倭寇”,不仅是明朝也是朝鲜、日本政府为维系区域社会秩序,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并做出了许多共同性的努力。明朝与朝鲜政府在打击“倭寇”的同时,就曾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日本,寻求日本官方的支持。而明朝沿海倭患的渐次平息,除却明朝军民的抗倭斗争与“海禁”政策的废止外,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颁行,也是有着极大的关联。即便是嘉靖二年的“宁波争贡”事件,明朝虽然表现出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袁琎被掳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并于此之中共同完成了对“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使之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性描述。
嘉靖二十六年策彦周良使团的入明,也是“宁波之役”延长线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围绕日本入贡使团的处置问题,明朝政府着力维系与日本正常“封贡”体制的基调并未发生改变。嘉靖君臣所关心的实际上并非如何坚守“十年一贡”的原则,而是在不失国家“大信”的基础上,以“纳贡”为基本前提,如何有效处理相关违制问题,并最终通过“候风便”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可以说,无论是策彦周良使团费尽周折地入明朝贡,还是明朝政府耗尽心机地处置应对,虽然双方的利益需求各有不同,但都表达出了对东亚区域秩序的期待与维护。
因此,16世纪前后的“倭寇”,对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无疑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从东亚诸国围绕“倭寇”问题所展开的诸种交涉来看,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对东亚区域秩序的认同与维护。可以说,“倭寇”源于旧有区域社会秩序的破坏,平息于东亚诸国共同努力下区域秩序体系的相对修复。“倭寇”问题的解决,及围绕这一问题而日渐展开的东亚邻交关系的多样性演化(如明与朝鲜“封贡”关系下的朝、日“通信使”交往等),也体现出了这一秩序体系“合而不同、协和万邦”的韧性与张力,及其对东亚区域秩序稳定的历史意义。
不过,“倭寇”问题也从另一层面揭示出了这种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结构缺陷。“一个中心”(以中华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多少降低了这一体系的平衡性与柔韧性,这也是日本在“倭寇”问题影响下,开始游离出这一秩序体系的重要因素。而对“倭寇”的认知与记忆,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日渐脱离实像,被赋予了更多民族与国家的内涵,则展现出了在这种结构缺陷的诱导下,东亚各国“自民族中心主义”与“自我防卫”意识的强化,以及由斯所致的这一秩序体系的解构趋向。
(四)本书的研究理念与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多少突破“民族国家”的相对狭隘性,回归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前东亚区域社会秩序的本源,来重新审视16世纪前后的“倭寇”问题,注重对中、日、朝鲜三方历史资料的借鉴与比较,无疑会使我们的解读更具客观性。而围绕“倭寇”问题展开的,近世东亚区域社会秩序的调整与演变,也能为我们今天的区域世界认识及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未来性启示。
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理念,力图重新审视明朝的“倭寇”问题及其对东亚区域秩序演变的影响。鉴于目前海内外学界对“倭寇”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倭寇”背景下的东亚邻交,以及“倭寇”认知与“倭寇”记忆方面。同时,为避免研究主线过于分散,在稽核中、日、韩三方史料的基础上,侧重从明朝,即中国的角度重点考察“倭寇”问题对东亚区域秩序演变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含这样几个部分:
1. 上篇:“倭寇”认知与“倭寇”记忆
主要以《明实录》中的相关语汇为中心,考察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认识及其与“日本”的关联性问题。以唐顺之及其《日本刀歌》为中心,考察嘉靖“倭患”背景下的晚明士人的日本认知状况。通过对《虔台倭纂》成书过程的梳理,探究“倭寇”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的转化脉络及影响。通过对南明隆武朝周崔芝乞师日本之争事件的考察,梳理明末清初“日本乞师”叙事中的“倭寇”记忆问题,及其所反映的东亚区域秩序的演变趋向。
2. 下篇:“倭寇”问题与东亚交涉
“倭寇”作为影响东亚地区邻交关系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关的“倭寇”问题也成为影响明、日本、朝鲜等东亚诸国交往的重要问题。以洪武初对外诏书为中心,探究明太祖对日交涉的真实目的。以明朝指挥袁琎被掳事件为中心,深入梳理宁波之役对东亚区域秩序演变的影响。通过对嘉靖“大倭寇”背景下,策彦周良入明处置经纬、嘉靖三十七年琉球册封“密使”吴时来等事件的深入考察,进行相对具化的梳理、分析与比照,从更为微观的层面解明此时期东亚邻交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所反映出的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3. 最后的附篇部分,则收录了东北师范大学东亚史学团队成员的一组笔谈《“万历朝鲜之役”四百二十年祭》,内含《“扶危字小”与万历出兵朝鲜》、《朝鲜对日本“假道入明”的应对》、《“壬辰倭乱”与明廷的“朝鲜保全”》3篇短文,这既是我们对“倭寇”问题研究从嘉靖“旧倭”向万历“新倭”的一种拓展,也蕴含了我们对“倭寇”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思考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