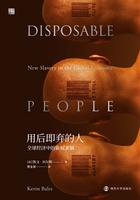
你能够用皮鞭打倒我
当我开始努力做研究、写作时,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出自这本书的故事,坦白说,我不会相信。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能够谦虚而带有一丝谨慎地讲,它似乎也已经改变了其他人的生命。当然,带给人们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野是重要主题,但当我把它写到纸上时,我难以想象它将如何完成。
本书的写作悄然来临,最早的刺激来自一份传单,我在伦敦进行户外活动时捡到它,上面写道,“当今世界尚有百万奴隶”。那是1993年,我是一位大学讲师。我承认自己在应对这样大胆的标题时,产生了一种傲慢与自大的不堪混合。作为一个多年参与人权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学者,我当时想:“如果连我都不知道这些,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心灵和头脑花了好长时间才跟上。
我把传单塞到口袋里,在回家的路上阅读。里面全是些逸事:一个斯里兰卡的孩子被奴役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骆驼骑师的故事;一个东欧妇女被贩卖为妓女的故事;关于一个印度农村家庭陷入世袭债务质役的描述。这都是些感人的故事,但是那数百万的奴隶在哪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想要的不仅仅是逸事,而是证据、数据。我差点把传单扔掉,因为我认为这些不过是狂妄的指控。但是有些事开始在我心里犯嘀咕,如果是真的呢?如果真的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奴隶制下又怎么办?如果真的只是我们所有人——政府、人权组织、媒体、公众——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真的可能会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奴隶制下而公众一无所知吗?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奴隶制已经在19世纪结束了,可能这些只是血汗工厂中薪资低廉的工人,他们重新被贴上奴隶的标签,以此夸大自己的悲惨处境。如果真有数百万人在奴隶制中,它怎么可能会如此隐蔽,我们又能做什么来解放他们?数百万隐藏的奴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挥之不去的想法是,如果真有这么多人仍在奴隶制中,那么找到他们就是像我一样的社会研究者的任务了。
我在大学图书馆,以“奴隶制”为关键词在学术文献中检索。顷刻便得到超过3000篇期刊文章的题目和摘要,远超我的预料。我坐在那儿与它们打了个持久战,在一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数千篇文章都是研究历史上的奴隶制的,只有两篇涉及当代奴隶制。它们都没能回答我的问题,数百万的奴隶究竟在哪里?
我开始广泛撒网,寻找更多信息来源,人权组织、政府报告、联合国、“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等,后者在1993年只是过去宏大反奴隶运动的残余,坐落在一个老建筑潮湿而阴暗的地下室。这些信息源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案例,我按照国家和奴隶制的类型将它们组织起来。由于信息源一个接一个,我把学生们拉进来帮助挖掘和筛选信息,同时聘请一位研究员,以便能够看得更长远些。一个模糊的全球奴隶制分布图逐渐浮现,而我也开始理解为何它会隐藏起来。
奴隶制隐藏在无知的厚幕之下,被奴隶制已经灭亡的常识假定遮蔽。由于奴隶制在每个国家都属违法,犯罪的奴隶主们将其行为隐藏。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都非常确信,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既然每个人都知道奴隶制仅仅存在于过去,任何不这么认为的人便会被视为怪人。公众如此确信以致“奴隶制”一词迅速丧失它的含义。有人声称乱伦是奴隶制,还有人认为房贷是一种奴隶制的形式,更有人说监狱里的人都是奴隶。在美国,右翼政客则鼓吹税收是奴隶制。随着真实情况被假定远去,甚至词义几经偷换,真正的奴隶制遁入无形。
现在,很奇怪的是,我不得不妥协于另一件和奴隶制同样严重的事情——人们总是一边说“人人都知道它不存在”,一边离(我)这个明显的疯子远一点。甚至当在大学研讨课上摆出证据时,我也从未能够带着听众越过关于奴隶制界定的知识混战阶段。不久,我便停止了这样的尝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通过思考得出一个工作定义来组织我的研究,并且暂时保密。
在我建立起奴隶制的图景后,每一组新的事实会产生新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是必须的。然后,在一次长途汽车旅行中,金尼·鲍曼(Ginny Baumann)和我试着写下所有理解当下奴隶制必须回答的问题。(1)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现代奴隶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