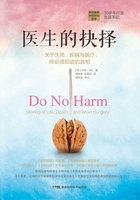
风险平衡,医生的困境
“叫患者进手术室了吗?”周一早晨,我刚走进手术室就问道。
“没有,”助理麻醉师吴娜(协助麻醉师的手术小组成员)回答,“现在没有血浆。”
“但患者已经在医院里等两天了。”我说。
吴娜是个开朗的韩国人,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什么也没说。
“今天早晨6点又派人去取血浆了。”麻醉师一进门就说,“他们必须重做一遍,昨天的血浆是在旧ERP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做的,这个系统不知为什么崩溃了,新的电脑系统今天才启用。这位患者会有新编码,从昨天发布的结果中找不到验血报告。”
“那手术什么时候开始?”我问道。想到要等很久,我很不高兴,因为这例手术危险性很高,也很棘手。总之,准时开始、按部就班,无菌手术单按要求放置、仪器设备井井有条地摆放,这对于缓解神经外科手术时医生的紧张情绪十分必要。“至少还要等几个小时。”
我平淡地说,楼下布告上写着新的iClip(individual-nucleotide resolution UV cross-link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免疫共沉淀法)电脑系统最多只会让患者等几分钟而已。
麻醉师也只是笑了笑。我走出手术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几年前,我肯定会暴跳如雷,叫嚷着必须采取措施,但现在怒火已经被极度的失望浇灭。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就像一名医生面对着一所现代化大型医院全新的电脑系统时束手无策一样。
我看见初级医生都在手术室的走廊里围着前台,一个小伙子坐在接待员的电脑前,脸上的笑容很尴尬。他戴着一个白色的PVC(Polyvinyl chloride,聚氯乙烯)牌,正反两面都印着蓝字“iClip系统管理员”。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我的高级注册医生菲奥娜。
“我们让他找脑瘤患者的验血报告,他说找不到。”菲奥娜告诉我。
“我应该向那个可怜的患者道歉。”我叹了一口气。事实上,我不喜欢在手术的当天早晨与患者交流。然而,我不想让他们再次意识到人性的尊严与恐惧,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也很紧张。
“我已经告诉他了。”菲奥娜的话令我备感宽慰。
离开那群初级医生回到办公室,我的秘书盖尔和病床主管朱莉正忙得不可开交。朱莉是高级护士,负责为患者安排病床,这是份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医院经常床位紧缺,她每天都在打电话与其他病床主管调换患者,或从神经外科病房接回患者,这样才能保证新收治的患者有床位。
“你看!”盖尔指着刚打开的iClip欢迎界面。上面有许多奇怪的名字,如“太平间注销”“死亡撤销”和“出生修改”,每项的后面都有对应颜色的小图标,当鼠标滚过的时候会闪亮。
“以后无论什么工作,都要从这个疯狂的列表中选择。”盖尔说。
我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整理文件,让她自己在这些怪异的图标中仔细选择。这时,电话通知我们患者已经到达麻醉室。
我上楼换了衣服,然后和菲奥娜一起进入了手术室。患者麻醉之后失去了意识,随后被推进手术室。随行的有两个麻醉师、两个担架工,助理麻醉师吴娜推着输液架和监控仪器,手推车后悬着许多管子和线缆。患者脸上盖着大片橡皮膏以保护眼睛,同时也保持麻醉气体管道和脸部肌肉监控线处于合适的位置。这种从人到物的转变也反映了我的心态变化。恐惧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关注与兴奋。
由于肿瘤位于大脑底部,而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失血过多的情况,所以我决定采取坐姿进行手术。失去意识的患者头部系在头枕销上,头枕销则固定在手术台旁的一个亮闪闪的金属架上。手术台被一分为二,前半部可以摇起,以帮助患者坐直。如此一来,手术时既可降低失血的概率,也更易接近肿瘤,但麻醉时稍有风险,因为患者直坐时头部的静脉血压低于室内气压。如果医生意外拉伤其中一条大静脉,空气很可能进入心脏,这将引起可怕的后果。在所有的手术中,如何平衡风险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一项复杂的技术、一种经验、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运气。手术中,两个麻醉师一组,手术室担架工和吴娜一组,我和菲奥娜一组,力求将患者摆好位置。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成功地让患者失去知觉的上身保持直立、头部向前低,确保最易出现褥疮的四肢上无压力点,身上的线缆和导管全都处于没有羁绊束缚或拉伸状态之中。
“好了,我们开始吧。”我吩咐道。
手术过程中手术部位几乎没有失血。在脑瘤手术中,只有这种瘤必须全部、一次性切除,因为一旦接近肿瘤,将立刻面对一场大出血。对于其他肿瘤,只需一点一点地“拆卸”,吸住后将内部切除,其余部分会自行皱缩、与大脑脱离,这种治疗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大脑的损伤。固态血管母细胞瘤的处理方式则与其他肿瘤大相径庭,首先必须找出肿瘤和大脑间的界面:轻轻分开大脑和肿瘤表面,形成一个几毫米的缝隙。将大脑表面上的血管和肿瘤表面分开时,止血是必备程序,在此过程中千万不可伤到大脑。这一切都是在高倍显微镜的帮助下完成的,尽管血管很细小,但出血量惊人。毕竟,每分钟心脏就会泵出一夸脱的血液供给大脑。思考需要大量的能量。
如果一切顺利,最终肿瘤将与大脑分离,医生会将它从患者脑中取出。
“全部取出!”我兴奋地朝手术台另一端的麻醉师大叫,手中挥动着解剖钳,它的末端就夹着那颗邋遢的鲜红色小肿瘤,它只有我大拇指指尖一般大小。我们为之紧张焦虑,付出诸多辛苦,似乎看来都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