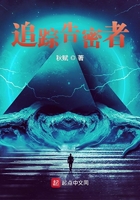
第27章 ????七块黑斑
提早回到家中,我泡好一杯醉红,开始继续整理卷宗。
消痩的脸蛋,胡子拉碴,熊猫式的黑眼圈,当我出现在张乎面前时,一向不修边幅的他,也觉得我换了个人:
“生意谈得这么辛苦,不行就先回部里报道吧?还是跟着我写汇报材料吧?”
我觉得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经商的局面刚刚打开,我找到了后山的茶农,他们还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么大的订单,要不明年机关的福利茶叶也交给我做,我算了一下,连交上特产税,价格也不高。”
不到一个月,我俨然成为当地茶农的代言人,进城与城里人谈生意,还把西部地区的红茶销售让龙龙全部拿下,我还没有透露:
我借了龙的龙公司,在当地把醉红的商标给注册了。
张乎非常意外:
“没想到你喜欢做生意?还真没看出来,部领导也就是要求年青人去体验一下经商与下海的感受,当作是学习,你不会当真吧?”
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我还在学习中,好在有一年的时间,才过去一个月,要是等一年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回来。这不,也可以顺便帮你找到当年案子的真相。”我找了个理由。
我把下海的好处与他的案子联系在一起,得到张乎的支持与庇护,可以帮我省掉很多麻烦。
王主任也让我去办公室汇报这一个多月来的思想情况,我如实汇报了与茶农同吃同住,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愿意更好地利用目前政策放开,经济搞活的好时机,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想法。
王主任满意地説:
“这个月部里的账号里,就你卖的茶叶款收回来了,给大家平均每人发了二十元的奖金,但是不能单独表扬你,因为其它同志还没有业绩,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压力。你理解就好。”
王主任一方面表扬我有生意头脑,完成了任务,一方面又提醒我,不要干得太猛了,避免与其它人产生落差,这是机关最忌讳的事。
我感谢他的提醒,然后建议:
“我认为,之所以成功,和王总经理找到胡大的代销点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应该把头功算到王经理那儿。”
王主任点点头:
“还真是那么回事。”
他马上拿起电话:
“王总,这个月的报表出来的,经过胡大店里的销售,你们办的公司获利很大,部领导表示满意,你立了头功。”
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王主任暗示我可以回去了。
我交上了书面的思想汇报,他点点头让我做好一年后,入党的准备。
我在山上的理发店,把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处理干净了,理发师老李説:
“小子,再不回来,头发上要长虫子了,个人卫生还是要讲究。”
我给他送了一包烟:
“在山里哪有您的手艺好,这不就是等着回来让您老给收拾吗?”
到部里的图书室,把关于杭州的书全部借了出来。
管理员高大姐説:
“这又是要到杭州做生意吗?好地方啊。”
我説是学习一下历史知识,准备将来去哪儿旅行。
第二天小王给我打电话:
“你老弟回来怎么不打电话,等着给你送牧云满月的红鸡蛋呢。怎么你老弟要旅行结婚了?嫂嫂在哪儿高就?”
我哭笑不得,一定是高大姐给我满处宣传的结果。
李敏芬喜出望外地看见我在她的教室外面等她,自从在殡仪馆一别,再也没有看到她。
我给她送了一袋梅菜烧饼,她的脸都红了:
“怎么好意思让宋老师给送礼?”
“叫小宋就好,要是庄老师在,还没你的份。怎么样?她交给你的作曲任务开始了吗?”
“太难了,刚刚开始,我找不到感觉,是悲伤的,又太直露了,我不知道风格怎么处理。”
我耐心地启发她:
“这是一段往事,应该是比较凝重的风格,它是揭露,但更多的是反思,你从这个方面想想基调吧。”
然后我又问她:
“她的骨灰还放在殡仪馆吗?”
她点点头。
我换了一身黑色的服装,在山上绿化办的院子里,采了一支菊花,当时还没有鲜花业务。
我手捧菊花,坐着公交车,摇摇晃晃来到殡仪馆。
阴冷的风,夹着落叶,在地上旋转。
我找到她的骨灰编号,服务人员给我拿了出来:
一个红色的木盒子。
不忍打开。
我问服务员能否把它带走?
她説可以,需要直系亲属的证明。
我说她是孤儿,没有亲人。
服务员惊讶地问: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赶紧説:
“同事关系。”
“开个单位介绍信,你可以领走。”
我详细问了介绍信的格式,她让我抄一份下来,説只要有介绍信,组织上保证,就可以领走,毕竟没有人会假冒亲人领走别人的骨灰吧。
我和王主任怎么説?説我知道庞红梅希望能在杭州她的老家落户?你们什么关系?
我连张乎都不能告诉,就更不能和师范学校去谈。
我借着将去上海谈生意,要开个介绍信,假装写错了一页,把空白的撕下收好,好在秘书在打电话并没在意,给我在写好的介绍信上盖上公章。
现在,我手里有一份空白介绍信,我怎么把公章盖上呢?
如果偷着盖,将来被发现后,秘书会受到处理,肯定不能这么做。
我给小王打电话,他的业余爱好就是篆刻。
小王被我的想法给吓着了:
“伪造公章,那是要被开除的,老弟你的胆子也太肥了。”
我拿出那份上海的介绍信説:
“我写错了,本来是要去香格里拉看龙龙,写成了上海,要是再改写的话,谁都知道我投资了龙龙,怕我假公济私,要是开不出介绍信,去雪区怕是旅馆都住不上,更不要説买车票。”
小王将信将疑,还是偷偷地把章刻了,看着我盖上后,立刻把章收回。再也不提我去看牧云的事。
我想通过这件事,他彻底意识到,我们不是一类人。
他是那种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的人,而我和龙龙是一类人:天生的冒险家。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不再适合待在机关了。
我带着李敏芳去殡仪馆,説真的我一个人去,心里也是慌张,万一要是遇到熟人,问我为啥一个人来殡仪馆,怎么回答?
那不是一个想来就来的地方。
我和李敏芬商量好,要是有人问,就説是你表姐。
我交出介绍信后,很顺利地把庞红梅的骨灰盒取了出来。
一路上她担心地问:
“要是明年清明节,学校派人来祭奠怎么办?”
我冷笑:
“不会有这样的事,非亲非故的,谁会想起她?”
李敏芬疑惑起来。
我解释道:
“其实学校一直怀疑她是自杀,为了保护学校的声誉,才説是煤气中毒。谁会主动再提这事呢?”
李敏芬哭了。
我摸着她的头説:
“等你再长大一点,我告诉你。现在集中全力,学好文化课,纪念她最好的方式,就是完成她的心愿。”
李敏芬点了点头。
我第一次学会了安慰一个女孩。
我把庞红梅的死亡证明和骨灰盒交给李明明时,她颤抖地接过,然后放在正屋的神台上,让甘阿姨找到一个香炉,点上香。
现在,庞红梅和韦凌云他们三人终于在一起了。
她指着楼上説:
“他一直睡着,越来越不好了。”
“带他去上海看看吧。听説刚刚有一台国产的CT机,可以扫瞄脑部,看看到底怎么治。”
我把庞红梅的骨灰带回来,获得了她的极大的信任。她马上联系上海的同学。
一周后,上海的同学説排到了队,可以带他们去看病,我把介绍信给了她,让她买二等船舱的票,后山的茶农开始一家一户地和我签约,我不能陪她一起去。
第二天我跟着拂晓去报社,她向老总推荐了我可以替代她完成副刊的编辑工作,等于找了个临时工。
用了两天时间,她把编好的稿子交给我,又划好了版面,如果交付副总编时,有任何调整,我可以帮她改。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通讯非常困难,这一走音讯全无。
两周后,她回到了家里。
甘阿姨急得到客栈找到我,让我劝劝她:
“这一回来,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饭也吃不下。”
她把几张黑色的胶片交给我,我对着光看了看,什么也看不明白。
她指着那些黑斑説:
“好几处,医生説都是陈旧性伤痕,来得太晚了,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一块黑斑,就是一次外力打击,我数了数,有七处之多。
历史可以掩盖,胶片揭开了历史最狰狞的面目,伤痕无情地还原了那场案件的真实情景,而这一切,拂晓更坚定是自己父母的错。
拂晓震惊的是,她原来只认为父母的告密,抓走了韦凌云,并没有想到作为主犯的他,因拒不交待而受到了非人的手段。
我不能告诉她这些,那样只会加深她的负疚感。
我坚信会有另外的人,出卖了他们。
我要了一张胶片想保存,找时间写一首纪念的诗。
我交给张乎,让他和我一样,坚信韦凌云的团队,无一人出卖过朋友。
张乎反问:
“那出卖他们的,除了庞红梅的父母,还有谁呢?”
这不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