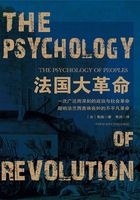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一、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心理状态分类
如果不进行分类,科学研究就无从谈起;而要分类就必须将那些连贯的过程分开来看,因此分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但是,既然连贯的过程只有在分解后才能被理解,分类就是必要的。
要想对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大致区分,显然需要将那些纷繁复杂、相互交错的要素剥离出来,这些要素原来或是混杂在一起或是叠合在一起。我们接下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为了获得一个淸晰的认识,我们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精确性。前一章末尾列举的基本类型,以及我们将在本章中加以描述的这些类型,共同构成了一个类群,如果我们打算面面俱到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的分析恐怕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们已经证明,人类是受不同逻辑支配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逻辑的存在是平行的,它们之间不会发生相互影响;但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它们可能会产生冲突,它们之间最小的差异在个人和社会发生巨变时通常会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正如我们不久将要考察的那样,神秘主义逻辑在雅各宾主义心理状态中起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其他的逻辑形式——情感逻辑、集体逻辑和理性逻辑也可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占据主导地位。
二、神秘主义心理
我们姑且将情感逻辑、集体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影响放在一边,而只考虑神秘主义因素的重大影响,神秘主义的因素在许多革命中极为盛行,法国大革命尤其如此。
神秘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为那些超人格的存在或力量赋予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些超人格的存在或力量常常表现为偶像、崇拜物、文字、口号等形式。
神秘主义精神是所有宗教和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祛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作为基础的神秘主义因素,这些信仰通常就要土崩瓦解。
神秘主义逻辑常常嫁接在感情和激情的冲动之上,它是大型群众运动的力量源泉。如果说愿意为崇高理性而牺牲自己的人寥寥无几,那么,时刻准备为自己崇拜的神秘偶像而献身的人则比比皆是。
大革命的信条很快就激发了一股神秘主义的狂潮,这与此前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激发的狂热没有什么两样。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状态的发展方向。
因此,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表现出的野蛮狂热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神秘主义精神丝毫不亚于宗教改革时代的新教徒们。雅各宾恐怖专政时期的主角——库通、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等——就是大革命的使徒。就像波利提斯为了宣传他的信仰而捣毁异教的祭坛一样,这些人梦想着改造世界;将他们的激情撒播于整个地球。他们坚信,自己那些无与伦比的信条足以颠覆一切君主,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欧洲的国王们宣战。坚强的信仰远胜于那些让人疑窦丛生的说教,激励着他们在与整个欧洲的战争中屡战屡捷。
大革命领袖们的神秘主义精神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露出了蛛丝马迹。罗伯斯庇尔本人就坚信他得到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支持。在一次演讲中,他试图让听众们相信上帝“在开天辟地之初就已经颁布圣令,要实行共和政体”。他还扮演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角色,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一条法令,宣布“法国人民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在最高主宰节仪式上,罗伯斯庇尔巍然高居在王座上,进行冗长的布道。
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最后承担了一个政务委员会的所有功能。马克西米利安在那里宣布了“最高主宰”的观念,他“垂怜关爱着那些受到压迫的无辜者,审判惩罚那些不可一世的罪人”。
所有批评雅各宾正统派的异端都将被革出教门,也就是说,他们将被送上革命法庭,等待他们的将是断头台。
以罗伯斯庇尔为典型代表的神秘主义心理并没有随着罗伯斯庇尔之死而销声匿迹,具有同样心理状态的人在今天法国的政治家中并不罕见。旧的宗教信仰已经不再支配他们的思想,但罗伯斯庇尔式的心理却阴魂不散,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将自己的政治信条强加于人。如果杀戮能够传播他们的信仰的话,他们通常会在所不惜。这些政治家一旦成为掌权者,其布道的方法就会同一切时代中运用的神秘主义方法如出一辙。
因此,罗伯斯庇尔至今仍有众多的信徒也就不足为奇了,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并没有同他本人一道殒命断头台,类似的思维模式在数以千计的人身上再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罗伯斯庇尔式的思维及其最后的信徒就不会消失。
长期以来,一切革命中的神秘主义方面都被大部分历史学家忽略,时至今日他们仍然试图借助于理性逻辑来解释大量与理性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在我前面已经引述过的一个段落中,拉维斯先生和朗博先生认为,宗教改革是“个人自由反省的结果,它向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极为虔诚的良心和一种大胆勇敢的理性”。
诸如此类的运动,永远不会被那些认为它们起源于理性的人理解。曾经震撼世界的那些信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规律。它们的形成与理性无关,甚至可以说是与理性完全相反的因素塑造了它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巫术、雅各宾主义、唯灵论等等,看起来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信仰形式,但我有必要再重申一遍,它们具有相同的神秘主义和情感基础,并遵循着与理性毫不相干的逻辑形式。它们的力量恰恰就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理性既不能创造信仰,也不可能改造信仰。
在我们当代的政治中,使徒式的神秘主义心理状态也不罕见,在一篇与我们最近的一位大臣有关的文章当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现在,我就从杂志上摘录以下一段:
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学校中立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竭尽所能对学校实行管制,哪怕因此成为教育自由的敌人。”如果说他还没有建议埋好火刑架、堆起柴堆的话,那也仅仅是出于礼貌上的需要,不管他愿意与否,对于这一点他还是得加以考虑。不过,即使他已经不能任意对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但他依然可以调动世俗的权力来对他人的学说宣判死刑。这正是宗教大法官们的立场。他对思想发起了同样猛烈的攻击,这个自由的思想者拥有如此自由的精神,所以他拒绝接受一切哲学。在他看来,那些哲学不仅是荒谬怪诞,而且是罪恶的。他自诩只有他自己才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他在这一点上如此自负,因此在他看来,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是可憎的怪物和人民的公敌。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个人的观点可能仅仅是出于臆测;也没有怀疑过自己这样考虑问题是不是更加可笑:只是因为别人否认神性就断定他们是想获得神圣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充其量是假借否定神性,而实质上以另一种方式重建神性——这只能够让人们更加怀念过去的神。某先生可以说是理性女神的一个信徒,他制造了一个摩洛神,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神,他需要拿人做祭祀品。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同道之外,任何人都不配享有思想自由;这就是某先生的自由思想。这一见解的前景确实吸引人,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为了实现,它已经打碎了太多太多的偶像。
为了自由的缘故,让我们来祈祷吧,千万别叫那些令人沮丧的狂热者最后成了我们的统治者。
假设理性的无声力量可以胜过神秘主义的信仰,讨论革命思想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就会毫无意义,但人们依然对此津津乐道。让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们的影响,至于说假想的人类平等、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通过法律的手段重建社会的可能性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是否已经被观察和经验揭穿,那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么说,这些空洞的幻想却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有力的行为动机。
三、雅各宾心理
虽然“雅各宾心理”这一术语并不严格属于正式的分类,但我对它还是情有独钟,因为它概括了一种得到明确界定的精神集合,足以形成一种真正的心理类别。
这种心理状态主导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但这并不是他们独有的特征,时至今日它还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要素。
我们前面已经考察过的神秘主义心理是雅各宾心理的一项实质性要素,但它还不足以单独构成雅各宾心理,现在我们就来考察其他那些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雅各宾党人对于自己的神秘主义心理浑然不觉;恰好相反,他们一直标榜自己是以纯粹理性为指导。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他们不断强调理性,视理性为自己行动的唯一指南。
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雅各宾党人的精神状态都采用了这种唯理主义的观点,甚至连泰纳也落入了这一窠臼,他在探究雅各宾党人大部分行为的根源时,都误用了理性。不过,在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著述中,也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并且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些见解非常出色,这里我摘录其中最重要的段落:
在对泰纳的描述表示钦佩之余,我想他并没有准确抓住雅各宾党人的心理。
无论是在大革命期间,还是在今天,雅各宾党人的真实心理都是诸种要素的集合,如果我们想理解它的功能的话,就必须先分析一下它的构成要素。
这一分析将首先向我们揭示,雅各宾党人并不是理性主义者,而是信仰至上者。他的信仰远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性不过是他用来掩饰其信仰的面具而已,虽然他的言论中充斥着理性主义的陈词滥调,但在他的思想和行动当中却见不到一丝理性的影子。
如果一个雅各宾党人真像有人指责的那样运用其理性的话,有时倒确实可以听到理性的声音,但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从大革命开始直到今天,雅各宾党人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理性的影响,但也正因为此,他才拥有了如此神奇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雅各宾党人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视野过于狭隘,从而使他无力抗拒强烈的冲动,只好任其支配。
当然,仅仅由于理性不足而激情有余这两个因素,还不能构成雅各宾心理,这里面肯定另有原因。
激情只能够支持信念,而不能创造信念。既然真正的雅各宾主义者拥有强烈的信念,那又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些信念呢?这里,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的神秘主义因素就派上用场了。雅各宾党人是神秘主义者,他们借助语言和口号的魔力,用新的神祇取代了旧的上帝。为了侍奉这些严厉的神祇,哪怕是采取最激烈的措施,他们也在所不惜。我们当代的那些雅各宾主义者通过的法律不就是为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吗?
雅各宾心理具有一种极端狭隘而又狂热的特征;事实上,它代表着一种狭隘僵化的心灵,拒绝接受任何批评,除了信仰之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神秘主义要素和情感因素占据了雅各宾主义者的心灵,从而使他们的头脑变得极为简单。他们只抓住事物之间的表面联系,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们分清什么是异想天开的幻觉,什么是现实的存在。他们对于事物的因果关系熟视无睹,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梦想当中,难以自拔。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雅各宾主义者并没有超出其逻辑理性的发展,因为他们对这种逻辑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常常变得十分危险。雅各宾主义者的那点微弱理性早已被他们的冲动制服,在有识之士视为畏途、不敢贸然前行的地方,他们满不在乎地走了过去。
因此,虽然雅各宾主义者都是一些能言善辩之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受理性引导的。当他们假想自己在接受理性引导时,实际上支配他们的恰恰是他们的激情和神秘主义。同所有那些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疑,从而被信仰之墙幽闭的人一样,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画地为牢的困境。
一个真正好斗的空想家,与我们前文描绘的加尔文教信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受到自己信仰的蛊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所有那些与他们的教义相背离的人都应该被处死。加尔文教徒与这些激动人心的演说家实在太相似了,他们像雅各宾主义者一样,对引导自己的神秘主义力量一无所知,相信理性是自己的唯一指南,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奴隶。
真正信奉理性主义的雅各宾党人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雅各宾党人被视为理性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只能为理性感到悲哀;而另一方面,充满激情和神秘主义色彩的雅各宾党人则非常容易理解。
极为微弱的理性力量、强烈的激情和浓厚的神秘主义,正是构成雅各宾精神的三种心理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