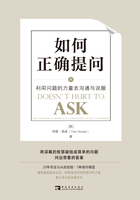
从法庭到国会
16年公诉律师的职业生涯,不仅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律师,也让我更了解我的同胞,知道如何与他们沟通并说服他们,用直接证据引导他们,解构不可靠的证据。法庭就像文化和人类学的培养皿,人性的各方面在此测试、分析和审判。正因如此,法庭上奏效的,也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
如果你把司法制度中的程序搬到客厅或会议室,很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法庭。”伊莱贾·卡明斯生前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后来在国会任职期间也成绩显赫。他在一次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揶揄我:“这是法庭吗?我们要在这里使用联邦证据规则吗?”美国国家税务局前局长约翰·科斯基宁私下里与我交情很好,他曾经在回答问题时反问道:“这是审判吗?有人在此受审吗?”不,听证会不是法庭,也不遵守法庭证据、程序规则,但或许应该遵守。我们司法体系中使用的政策、规范、程序、规则,并不因为在法庭上运用过就顺理成章是“正确”的。之所以它们在法庭上使用,是因为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我们总体上认为它们是阐明真相的最佳工具。换句话说,并不是在法庭上运用过就正确——之所以在法庭上使用,是因为其本身是正确的,而正确才是首要的。
尽管我热爱正义、公平,追求真理和说服陪审团,但我离开了法庭,原因是我无法回答关于法庭之外的问题。从精神信仰上来说,我无法接受每天的种种见闻。有些人对自己的同胞越来越不人道,无辜的人经受苦难,有人杀死了自己口口声声说爱的人,弱势群体遭受不公,甚至充斥着无端的暴力、堕落和恶意。
在现实世界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友好、良善、守法、乐于助人的,但在司法系统中,这并不是你所看到的,甚至最终让你觉得许多人都是坏人。法庭上不应该对好人审判,审判的应是杀人犯、强奸犯和入室盗窃犯等坏人。每天与这些人打交道,很容易对人产生偏见。当你满眼所见皆是邪恶时,你会不自觉地认为生活也是充满邪恶的。
怀疑与日俱增,但我又常常想起基督教的格言(大致引用《圣经》的经训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让人得益处。”如果你生活在传统深厚的基督教地区,那么你一定经常听到这句话。
万事,嗯?那些脸被烟头烫伤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那些被性侵的孩子呢?那对被锤子打死的无辜夫妇呢?被生父强奸,伤口被缝起来的3个月大的孩子呢?麦亚呢?这就是你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让人得益处”吗?
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出色。几乎在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只要需要,我就能说服面前的12个人放弃合理的怀疑。16年的时间里,我可以让12位完全陌生的人走到一起,达成一致。说服我的同胞或法官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每天晚上下班后,从法院开车回家,问题开始快速在脑海里浮现,却来不及找到答案。
一天结束时,看着白昼输掉了与黑暗的战斗,我挣扎着不去想犯罪现场照片中的画面。家人熟睡,而我毫无困意,努力将外面的风声与试图进入我内心的邪恶和堕落的声音区分开来。我曾经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于我最珍贵的人也如此。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女儿会把枕头和毯子拖进我们的卧室,放在我的那一侧床边的地板上,虽然知道妈妈会让她回房间,但爸爸不会。我甚至试着找上帝解决此问题,小时候每每感到不安或焦虑,我都会向上帝倾诉,但上帝既不听我说话,也不跟我交流。
击败我的不是被告律师或法庭上的陪审团,而是我脑子里的律师和陪审团。
我无法说服自己,怎么会允许一个孩子被烧死、打死,或者被自己的父亲强暴;我无法说服自己,怎么会允许一个脑瘫儿被自己妈妈的男朋友杀死;我无法说服自己,万事最终让人受益,而结局对许多无辜的人来说是死亡,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妥协,也没有说服的死亡。那些幸存者将一生陷入痛苦、恐惧和不信任,他们的问题总好过我的答案。我可以告诉他们是谁,但无法有十足的把握告诉他们原因。
所以我离开了法庭,只剩下最微弱的信仰。我只带着一丝闪烁的光亮愤世嫉俗般地离开了,趁着问题尚未变成愤怒,愤怒还没有变成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我勉强离开了。
这次又是什么?当法庭不再是一种选择时,喜欢说服的人会去哪里呢?也许是更大的陪审团队伍,也许是政界,也许是国会。
也许什么都不是。
奇怪的是,尽管我离开国会时对人类的看法确实比我离开法庭时更积极,但我还是离开了。我离开法庭是因为问题比答案更好;我离开国会是因为这些问题在美国政治上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华盛顿,几乎每个人都早已下定决心。即使在华盛顿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些问题下定了决心。政治永远存在,每一天都是微型选举日,似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有政治色彩。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比赛被政治化,音乐和电影颁奖典礼受到政治影响,飓风和病毒掺杂了政治因素,甚至在厨房的餐桌上,也潜伏着试图插手的政治。
我不记得在国会的8年时间里,有谁的想法在委员会或大会辩论中被改变过。说服需要开放的心态,你无法打动不愿被打动的人,也无法说服不愿被说服的人。从本质上说,陪审员愿意被说服。国会议员,至少在现代政治环境中,要么不能被说服,要么不承认自己已被说服。
在国会任职8年后,我开始相信这些问题无关紧要,因为除了我自己,几乎没有机会说服任何人。奇怪的是,在国会工作期间,我变得更愿意被说服。原因不是现场的演讲,也不是委员会听证会,而是那些聪明、可信的人,他们以事实为中心,努力被倾听、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愿意听取和理解我的意见。
华盛顿的那段时间让我明白,在谈判桌前,每个人的观点都会受各自经历的影响。我同意与否,并不重要。每个人都应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每个人都为了成功说服,带着同样的工具和知识来到谈判桌前,那么争论就会变成对话,对话就会变成认真的问题,问题就会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力。
正是在国会大厦的大理石地板上,我意识到说服并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而是可以有效和高效地为你心中的真相进行宣传。说服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方法,你向别人提出一组正确的问题,他们就会自发地接受你的观点。说服是理解别人的信念以及背后的原因,并利用这些来批判或肯定他们的立场。说服是微妙、循序渐进和深思熟虑的,它有可能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