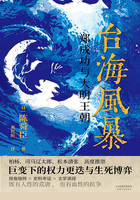
告别金陵
据长崎荷兰商馆日志记载,涉嫌《圣经》一案的唐船于1644年9月16日驶入长崎港,其所属者是郑芝龙。在日志的寥寥数语之中,荷兰人丝毫不掩饰他们对这起案件的窃喜。因为郑家船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船队从大明直接采购生丝运往长崎的买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荷兰商人在日志里这样记载:他们(涉案唐船的相关者)纷纷表示后悔没在台湾囤货。台湾对外商持友好态度,再加上从大陆往返日本之间的航程是从台湾往返日本的四倍且更加危险。
涉案商船被扣押了足足两个月,直至同年11月18日才得以返航。日志里提及这天有五艘巨型唐船出港。上述日期出自荷兰人的日志,采用公元纪年。若是按照大明或日本采用的农历,涉案商船出港的日期是十月十九。
统太郎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其中一艘船。这类唐船又俗称“泉州船”。泉州府隶下有晋江、南安、同安、惠安、安溪、永春六县,知府在晋江。郑芝龙的家乡南安就在其西北不远处。此时,郑芝龙已接受南明[1]朝廷册封福建总镇。他在晋安的安平镇建筑城池,常驻于此。按计划,统太郎一行将在安平上岸,吉井随阿兰在此处换船前往台湾。
“这艘船经停安平城,从那里上岸,你就离福松不远了。和他久别重逢,你有没有很期待?”在船上,阿兰和统太郎用汉语交谈。尽管有些蹩脚,但他们在唐船上都尽量用汉语交谈。这也是为登岸做些准备。“当年分别时,他不过是个七岁稚童……一转眼都十四载了,不知道他变成了什么模样。”统太郎蹲坐在甲板上道。阿兰没回话。她从方才起一直虚抚着琴弦,眺望远方的琉球群岛。
“福松!”统太郎在心中再度呐喊那熟悉的名字。这呐喊马上就能得到真正的回应了。然而好事多磨,统太郎没能如愿在安平城和好友重逢,只见到了其父郑芝龙。郑芝龙青年时便是貌比潘安的美男子,如今他正值龙虎之年,眉目端正的面庞上更是多了一分不怒自威的气势。“福松?噢噢,你指的森?他不叫福松多年了,现在叫森,在南京求学……你也知道现在形势严峻。我已派人催他赶紧回福建,恐怕小兄弟你要在寒舍等一阵子了。”郑芝龙用流利的日语道。他接手颜思齐船队之后,曾数度往返日本,顺道还给福松添了个弟弟。
福松七岁到福建后便改名为森。他年纪轻轻便考上生员[1],被推举到南京太学读书,更得南京名士钱谦益赐字大木。他获得“成功”之名要在重返福建之后了。故而,此刻还没有郑成功,只有郑森,字大木。他虽然刚过弱冠之年,却已成婚多年,育有一子。
明太祖朱元璋一统中原,定都南京,传位给皇太孙朱允炆。燕王朱棣夺建文帝位,迁都至他的封地北京。明朝在北京、南京各设“国子监”。之后,在南京保留的机构大都是空壳,只有国子监还是名副其实的太学。能在南京国子监中深造的郑森,毋庸置疑是指日可待的出将入相的人才。
郑森慵懒地倚在国子监的栏杆上,远眺南方。他的好友陈方策也以同样的姿势眺望着:“此美景,果真百看不腻。”
“是啊,只有风光犹在……”郑森答道。
“风光犹在,风光犹在呀……”陈方策重复道,面浮苦笑。
两人同是血气方刚的弱冠青年,也是敏感细腻的秀才郎。
“‘国破山河在’……我方才翻阅杜甫诗集,随手一翻便是这句。这可不是好兆头。”
“北有鞑子铁蹄将至,南有党争钩心斗角……”陈方策冷哼道。没人能阻止热血青年义愤填膺,正如没人能阻拦明朝走向衰亡。身处这般国将不国的乱世,太学的青年自然义愤填膺。弊政,甚至可以说是暴政,使得大明各地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转眼间数十年已经过去了。起初,起义者鱼龙混杂,很难有大作为。驿卒李自成联合各路势力,将原本的乌合之众塑造成了正规的起义军。这数年来,他的势力逐渐占据了大明版图的西部,对京师虎视眈眈。
如果说李自成的起义军只是内忧,那么北方的后金则是名副其实的外患。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统率下,于萨尔浒大破明军。
泱泱大明英雄辈出,却无一人能力挽狂澜,解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朝廷内部派系复杂、明争暗斗,但凡一人立下显赫战功,都会遭到反对派嫉妒和谋害,不得善终。位极人臣者家破人亡是常事。救国的英雄还未登场,便已经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然而祸不单行,如此乱世,在位君主又偏偏是大明王朝十六个皇帝里最生性多疑的崇祯。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率部从山西出征。三月十七,兵临京师城下。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登上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以长发覆面,自缢身亡。煤山是一座人造山丘,现名“景山”。崇祯皇帝留下遗诏:“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京师沦陷前,朝廷曾四方求援。抵御八旗铁蹄的猛将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得到急报,当即率援军星夜奔赴京师,但随后便传来了京师沦陷的噩耗。然而最让吴三桂震怒的,不是京师失守、君王自缢,而是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霸占。羞愤让他失去了理智,为了夺回陈圆圆,他不惜乞援于清廷。
吴三桂的乞援对清廷而言无异于天降福音,毕竟清兵再骁勇,也难以攻下山海关这道铜墙铁壁。如今山海关的守将主动打开关门,清军兵不血刃地入关,不费吹灰之力便击溃了李自成主力,入主京师。全族皆兵的女真人早在奉天修造了皇宫,国势渐威。此时在位的是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其叔父多尔衮战功赫赫,担任摄政王。
再看南面,噩耗传来,在南京的明朝遗臣就着手择出新帝,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主流派想即刻扶持福王(万历皇帝之孙)登基继位,此举遭到东林党[1]和复社文人[2]的抗议。江南的派系之争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风光不晓人愁,春去秋来,萧萧瑟瑟……”郑森不忍去看那泛黄的树叶,叹道,“鞑子一路西进山西,将李自成赶到了陕西,另一路侵占了山东,南侵迫在眉睫……这紧要关头,朝廷竟在忙于选秀?”陈方策应和着也发出一声叹息。他比郑森更痛心疾首。
“李国辅那阉官去苏杭选秀女,惹得民间人心惶惶。荒谬,荒谬!”郑森皱眉道。
皇帝下旨严禁民间在选秀期间进行婚配:天下美女,当由天子先选。先帝自缢于煤山不到半年,朱由崧新登基便开始搜罗天下美女了,民心与南京弘光政权渐行渐远。
“放眼不是前线战败,就是这等荒谬事,真叫人忍无可忍。”陈方策显得十分焦躁。
“你在家乡苏州可有相好?”郑森话锋一转,问道。
“我在家乡的红颜知己何止数十人?”陈方策自嘲道。
选秀旨意一出,官府会在当地有适龄女子的家宅门上贴一道黄色的封条,以此杜绝民间藏匿女儿。官府未必对家家户户的女眷了如指掌,但邻里就不同了。若某家分明有适龄女眷,宅门上却无黄纸,就是犯了藏匿之罪,告发到官府可获得不菲的赏钱。此等选秀,不仅把寻常有女儿的人家搅得鸡犬不宁,更害得无数少年郎战战兢兢,担忧于失去意中人。
血气方刚的陈方策就是这些少年郎中的一个。哪个少年不想有保家卫国、护得意中人周全的力量呢?既愤慨于国之危难,又无奈于个人境遇的无力,让他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
“要不要出去散散心?”郑森问友人。
“我正好心里苦闷,走吧。”陈方策言罢,兀自向前走了;郑森赶紧跟了上去。
“去哪里散心?”
“除了曲中,还能去哪里?”
曲中是秦淮河畔的寻欢街。早在明初,便有富贵院等众多大名鼎鼎的销金窟聚集于此,故而周边又被当地人称作旧院。洪武帝[1]定都南京后,在曲中建十六楼,将官妓安置于此。据明清文人余怀《板桥杂记》所载,此处聚集了无数美妓、歌妓,极尽美貌才华,令世间男子为之倾倒。其中,名妓花魁不仅能歌善舞,还擅长诗词歌赋。
地处曲中的妓院大多在秦淮河沿岸,故又被统称作水楼。
秋日的暮色洒在淡蓝的丝绸帘子上,将屋内染成翠绿。“是啊,解忧非旧院莫属……”郑森笑道。
二人抵达妓院门前,陈方策忽然调侃道:“大木兄,你流连这等寻欢地,怎对得起千里之外在福建的新婚娇妻?”
“新婚娇妻?我已有一子,新从何来?”郑森豁达大笑。
“那,你是否思念自己的骨肉?”
“无一日不思念。”郑森坦然道。
“身世显贵,有家有室,羡煞旁人。”陈方策虽是正经官宦之后,但家世平平,难称富贵,和豪强一方的郑家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
“唉,不提这个了。”陈方策话锋一转,笑道,“你打算怎样安排少珠?”张少珠是两人经常光顾的名妓,在郑森来南京之前本是陈方策的相好,谁知竟被郑森夺得了佳人芳心。陈方策大度,便退让了。
“难办,我正烦恼。”郑森答道。
“烦恼什么?以你的家世,多娶几房妻妾回去又何妨?你该给她落籍了,莫耽误了人家青春年华。”
“我起初是有此打算的……”
“怎么,你现在改主意了?”
“再三斟酌下,这怕是行不通……少珠必须照料体弱多病的母亲,不可能离开金陵。”
“尽孝道,这是必然,她为何要离开家乡?”陈方策一时没反应过来对方的话中意,“难道说大木兄要回福建?”
“这些烦心事,改日再聊。不是来解忧消愁的吗?”郑森言罢,推开了半掩的院门。
数声犬吠之后,满脸媚笑的老鸨迎了上来。金陵的妓院都会养一只看门犬,用来告知有客上门。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谈国事,一旦谈论必遭人侧目。郑成功与陈方策二人都是风月场的老手,懂得规矩,熟门熟路地登厅堂、喊姑娘、叫茶围。郑森把玩着酒杯,不禁低声吟诵了几段白乐天的诗作。即便这隔绝乱世的温柔乡也无法让两人纵情酒色,忘却心中烦恼。
“大木公子,今日怎有空来看奴家?”张少珠给郑森斟酒,“大木公子”的称呼方式表明两人不一般的关系。
“时日无多,自然想日日相见。”郑森答道。
“明日你莫邀我,坏了你二人独处。”陈方策冷漠道。好友显然先把归乡之事告知了姑娘。他心里有些不痛快,转念一想,若换作自己也会先向红颜知己倾诉。酒过三巡,众人还未尽兴,郑森却落杯道:“备画舫。”
画舫,顾名思义是以画装饰的小舟。寻欢客和妓女可在画舫上共度良宵。
张少珠唤丫鬟去准备画舫,郑森却语出惊人:“方策,你也随我上船。”
“你这闹的是哪一出?”陈方策猝不及防;只见姑娘面色不变,看来郑森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有些话,要单独和你说。”
“好吧……”陈方策不再推辞。他猜测,郑森想说的八成是寻欢所里禁忌的国事。
烛火通明的画舫不仅是水上的温柔乡,还是密谈的好场所。唐代杜牧有诗云“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足以佐证早在盛唐,秦淮两岸便已是灯红酒绿。从四方而来的画舫驶进同一条河道,俨然就是一列看不见尽头的船队;从远处眺望,便是一条遍体通红的火龙。夜幕降临,河面上管弦交鸣,热闹非凡。
“说吧,到底是什么事?”陈方策打破短暂的沉默。
“我求方策兄……关照少珠。”郑森道。
“好算盘,你回福建逍遥快活,却让我来照顾她?”
“确实如此……她若遇上了烦心事,还望你照顾她。”
“哈哈,你不怕我乘虚而入?”
“这世间缘起缘灭,没到最后,谁猜得到结果……”
“我懂了……好你个郑森,你是厌弃了这南京的种种丑陋,想逃回家乡享福去!”
“非也!你方才说这乱世之中,凭实力说话。就凭我俩的两对手脚,赤手空拳岂能救国于危亡?我在南京是一介书生,回福建,依附我南安郑家的权势,就有兵有船,有了实力!”
“戏言而已,莫较真……据说,朝廷赐封令尊南安伯?令尊真乃乱世英雄……但郑森你有能力继承这家业吗?”陈方策注视郑森道。
南明朝廷派钦差陈谦赴南安赐郑芝龙南安伯爵位。相传:当时,南明朝廷根本没把地处福建南陲的南安放在眼里,只当是边陲小城。钦差陈谦持赐封文书到了南安,竟误以为自己走错了道,掉马回头。
“我正有此意。”郑森坚定地点点头,“家父年仅二十便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但对船队没有绝对的统帅权。之后二十余年,他不断巩固权力,这努力的成败就在当下了。如今,南海众头领名目仍在,若一招不慎,就会顷刻分裂。我这般匆忙回乡,为的是在紧要关头辅佐父亲。”
“你家里是否有兄弟?”陈方策问道。
“有四个异母的弟弟,尚年幼。”郑芝龙将郑森生母留在了平户,回乡又娶了一房颜氏,育有四子。他不顾郑森年幼便安排他回国,无异于对外宣告其继承人的地位。郑家拥天下五斗之财,谁不觊觎郑家的巨额财富?但郑森不甘只做这富有四海的财主。
前任首领颜思齐暴毙,众人推举资历最浅的郑芝龙继位。这是防止权力垄断的良策。郑芝龙上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集团的大权由陈衷纪牢牢掌控。其后,集团分裂成了“招安派”和“台湾派”。以郑芝龙为首领的招安派归顺了朝廷。陈衷纪则率领台湾派留在了台湾,开垦贸易。然而这分裂却是集团的计策,毕竟历朝历代对海盗都毫不容情。故而他们佯装分裂,留一半人在台湾作为保障。郑、陈二人之间的联络从未中断过,郑芝龙仍遵从陈衷纪的命令。到了崇祯元年(1628),陈衷纪在海上遭同行李魁奇杀害。翌年,郑芝龙在金门湾捕获李魁奇,替陈报仇。崇祯八年(1635),郑芝龙全歼海盗刘香船队才算获得真正的统帅权。迄今为止,郑芝龙以官兵的名义,不断讨伐海盗,收编败者,以扩充实力。
集团的原头领在郑芝龙帐下做幕僚、长老,地位崇高。然而随着集团吸纳各方势力,不断壮大,长老的权威渐渐减弱,又在无形中提高了郑家的权威。除此之外,郑芝龙极具经商天赋,一官船贸易所带来的财富,使得他的地位更加稳固。南安伯的爵位意味着郑家势力步入鼎盛。
“方策呀,方策……”郑森悠悠叹道,“我本想在金陵学有所成,入朝为官,经世济民,奉此一生。纵故乡有万贯家财又与我何干?朝廷俸禄足以温饱,余财悉数赠予家弟。然而事与愿违。现今国难当头,我郑家势力便是救国之力!故而,我绝不能让这力量落入旁人手中。福建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回去。”郑森正说到激情处,一艘笛鼓喧闹的画舫从一旁经过,摇晃的只有船上青年的忧国之心。
陈方策动容道:“郑森,你回乡吧。这南京确实已烂到骨子里。”
“朝有奸佞,上有……”郑森本想趁喧闹吐出“昏君”二字。崇祯帝自缢的噩耗从京师传来,南京朝野动荡,就新君人选展开了明争暗斗。那时,在南京周边避难的皇族只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二人。福王乃万历之孙,若按血统,当立福王。潞王是隆庆帝之孙,血统稍逊福王,却胜在贤明。选血统,还是要贤明?郑、陈二人之师钱谦益坚持国难当头,当以贤明立君,但最终还是败给了以马士英为首的福王派系。
这福王是“了不得”的人物。昏君的潜质——贪财、好色、嗜酒、不孝、残暴,他一样没落下。但越是这样的昏君,对马士英等人而言就越容易左右。
福王的登基可谓疑点重重。崇祯帝自缢后,太子下落不明,据说是李自成逃亡时将其掳走。即便如此,崇祯帝除了皇储之外,还有众多皇嗣不知所踪。按惯例,先帝皇嗣尚生死不明,理应由监国代理国政。然而马士英等奸党不顾礼制,强行扶植福王登基继位,并改元弘光。
明朝的皇帝有各自的年号,民间也习惯以年号称呼皇帝。但唯独这福王,没人愿称他“弘光帝”。且不提继位的合法性,单看福王的秉性就难以服众。正史的《明史》记载明朝国祚终于崇祯皇帝,南明数位帝王无一计入正史。不出所料,福王刚继位,便一展昏君本色,办起了先前提到的选秀。
关于福王还有一段后世相传的轶事。某日,福王眉头紧锁,怏怏不乐;臣子还以为其忧心国家社稷,关切问道:“陛下因何事烦忧,臣等愿粉身碎骨,为陛下分忧。”
“爱卿深知朕意!朕正为宫廷梨园无名角而忧愁。传朕旨意,搜罗天下名角入宫!”国难当头,福王不思富国强兵,倒关心起梨园来了。
马士英等奸佞利用君上昏愚,排挤忠臣良将,一时间权势滔天。而驻守江北的四镇将军各怀鬼胎,不思御敌,只热衷于圈地割据。正如陈方策所言,南明已是穷途末路了。
“我若有你那般的家世背景,早就回乡继承衣钵去了。你打算何时动身?”陈方策问道。
“后日一早便动身。”
“耽搁到后日?你不是已经归心似箭了吗?”
“若不出意外,明日我家使者抵京,和他商议后再启程不迟。”
“也好,你对南京总有些难以割舍,比如说这少珠姑娘……”陈方策本想调侃,郑森却不接话茬儿,只是痴痴地注视着水面。
离京前夕,郑森拜访孝陵。
南京紫金山因远眺呈紫金色而得名。明朝的永乐帝迁都北京,其后帝陵便都选在了北京城郊,即明十三陵。相传建文帝死于战乱,却不见尸首,故无从下葬。所以南京的明皇陵只有太祖洪武帝的孝陵。
孝陵附近没有外人,除了郑森,便只有从福建远道而来的使者,姓甘名辉,是郑氏水师麾下勇冠三军的猛将。郑森本想邀请甘辉一同参拜太祖,但他停下脚步,婉拒道:“森少爷,末将在此恭候。”为何不愿同往参拜太祖?郑森的疑惑呼之欲出,但见对方一脸严肃不愿多答的样子,便作罢了。反倒是甘辉邀请道:“森少爷可有雅兴陪末将登上这紫金山?”
“正有此意。”郑森点头。
紫金山虽不是高峰,从其山顶可以睥睨金陵全域。
“金陵倚靠长江天险,该如何攻略?”甘辉自言自语道。郑森语塞,他似乎能理解对方为何拒绝参拜了。如今情势,金陵沦陷是迟早之事,夺回南京之战不可避免。毕竟在长江以南,能和清军角力的便只有郑家了。
郑森紧盯南京城池,不敢挪开视线。他这些年寒窗苦读,只为出入朝堂,寻求经世济民之道。如今看来,迄今所学皆化泡影,要复兴大明,只能仰仗沙场浴血、刀兵弓马。入相不能图强,出将却能救国。沙场不念伤感,只有胜负。身为武将,眼里只有一兵一卒、一攻一守,兵来将挡……多愁善感怎能领兵?参拜太祖陵寝或许能一吐悲愤伤感,但真要挽救金陵,还是得登上这紫金山,寻求御敌方略。
“我明白将军的用意了。”郑森叹道。
“请牢记眼前的一山一河、一城一郭,切忌仰赖地图。”甘辉的声音毫无感情。
“铭记于心,永世不忘。”郑森答道。
两人在山顶上逗留了一炷香工夫,天色渐暗。
“下山吧,明日还得早起。”甘辉言罢,转身便走。
“明日在哪个渡口上船?”郑森问道。
“桃叶渡。”甘辉加快了脚步。
来日重返金陵,此处必当化为修罗场。想到此处,郑森心中感伤,酸苦难耐:无忧无虑的求学生涯今日便要画上句号。这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十来年,称得上他这辈子的黄金期。郑森在心中默默起誓:愿天下人都有属于自己无忧无虑的黄金期!这便是他毕生追求的心愿。掐指算来,郑森的南京游学生涯不满一载,但这短暂的时光,便是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了。
“末将已将启程时刻和地点告知陈方策公子。”无愧于南安郑家的智谋之名,甘辉已对郑森的社交圈了如指掌。
“感激不尽。”郑森道谢。
“末将还顺道知会了少珠小姐。”甘辉语气不变,似乎在道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启程那日,陈方策和张少珠前来送行。情郎惜别,少珠的神情明显不自然。“奴……等郎归来。”言罢,泪珠已默默划过面颊。
“保重,我一定来看你……”佳人梨花带雨,郑森只能这般回应,“我一定会回来!”他不由加重了语气。
“少爷,该登船了。”甘辉语气不变,似乎眼前的依依惜别不存在一般。郑森登船,船静静地离岸远去。
“人生如梦……”郑森遥望渡口,陈方策和少珠仍伫立原地挥手告别。郑森茫然地挥手回应。他心中感慨万千:南京游学、邂逅佳人、皇上自缢……这一切,是梦吗?
“众人都翘首以盼少爷归来。”甘辉道。
“劳长辈们挂念。”
晨雾缭绕的紫金山之上,郑森仿佛看见长自己一年的妻子的娇颜若隐若现,幼子的容颜却久久没能浮现,只隐约听闻婴儿在耳边啼哭。
“还有一事要向少爷禀报,一名叫作统太郎的青年投奔您府上,说是从东瀛平户而来,是少爷的儿时好友。”
“统太郎?噢噢,是林田家的……”这让郑森有些意外。他已经不记得这位儿时玩伴的模样,不过见了便知。不知母亲是否安好……提起东瀛,郑森难免想起远在异国的生母,鼻子隐隐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