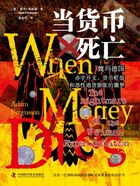
序言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不再是安全感的源泉,当通货膨胀成为整个民族的忧虑时,人们自然会向有过这种最悲惨、最令人不安的经历的那些国家去寻求信息和指引。然而,查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战败的同盟国(the Central Powers)有关战后命运的各种文献——不论是经济、军事、社会、历史、政治还是传记,会发现缺少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一方面是当时的经济分析(出于经济学家都知道的原因,他们有时倾向于通货膨胀是财政政策的一种蓄意行为)忽略了人为因素,以及对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和奥地利革命后时代的军事和政治因素的忽略;另一方面是历史叙述,这些叙述尽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旁征博引和独特见解,但忽略了——或至少是大大低估了——通货膨胀是他们所述的动荡的最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尽管原始资料和记录对于从人的方面去评估通货膨胀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这些原始资料和记录往往不尽如人意,要么视野太窄——从不同的炮弹坑看到的战斗可能会大不相同;要么回顾方式过于笼统,对于多年灾难的高潮和前奏——1923年的金融怪相——过于轻描淡写了。
通货膨胀带来的痛苦,无论持续时间有多长,都与急性疼痛有些相似——当它发作时,会令人不能自拔;当它消失的时候,不管它可能给精神或身体留下了什么伤痕,都会被遗忘或无视。这样的解释或许显得有点奇怪,但魏玛通货膨胀这一重大事件完全适用于这一说法。然而,考虑到那场危机的持久、广泛和可怕,以及它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提及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么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反之亦然,除了最片面的经济论文或个人回忆,要想客观地说明那个时期德国的通货膨胀,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政治力量的角力、军队的动荡、德国与法国的争端、战争赔偿问题以及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同时发生的超级通胀。如果不与当时的政治事件放到一起,人们无法准确评估通货膨胀的政治意义和判断通货膨胀在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产生和失控的情况。
1923年的德国既是鲁登道夫(Ludendorff)的德国,也是施廷内斯(Stinnes)的德国,既是哈芬施泰因(Havenstein)的德国,也是希特勒(Hitler)的德国。他们分别代表了军队、工业、金融和政治四大领域,这四个当时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和戏剧中的反派角色并无二致:鲁登道夫,毫无灵魂和幽默感的前军需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托尔和奥丁[1]的崇拜者,反动势力的号召者和操控者;施廷内斯,只效忠于金钱的财阀奸商;哈芬施泰因,疯狂的银行家,他唯一的目标是用钞票使整个国家陷入泥沼;希特勒,嗜权如命的煽动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唤起了人性中所有的邪恶。单就哈芬施泰因而言,尽管对他的上述评价有失公允,但实际上,这位头脑敏捷的财政官员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不存在真正的反派角色,这些人不过都是在后台候场的演员,只要发出上场的提示,他们就会登台亮相,扮演由形势支配的角色。当然,当时也有许多和那些反派扮演者一样不负责任的人,也应受到谴责。最终德国人民成为受害者。正如一位幸存下来的人描述的那样,这场战争让人们感到茫然和震惊。人们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打败他们的敌人又是谁。
本书不光介绍了一些新揭露的事实,还呈现了许多被遗忘的和迄今未公开发表的观点——这些资料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都来自那些能够客观观察各种事件的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健康和安全都没有受到他们所目睹的事件影响。这些丰富的资料来源于英国外交部(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的档案,最初由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提供,它的负责人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大使之一,达伯农勋爵(Lord D’Abernon)。达伯农的资料不仅来自德国各大城市的领事馆,也包括了与协约国(the Allied)赔偿或裁军委员会的个别成员的报告。除了是比较容易获得的文件,英国国家档案局(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文件,也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这不仅是因为达伯农任职期间的英国大使馆(the British Embassy)一直与德国的高级政客保持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因为美国在1923年年初撤走了派驻人员,以及柏林和巴黎之间早已几乎完全中断的任何沟通,使得本来可能具有比较价值的信息变得零散又浅显。因此,对于关于同时期德国的资料补充,我毫不犹豫地充分参考了这些文件。
我尽量使这些行动、反应和交流保持原有的历史先后顺序,希望本书中这种也许显而易见的顺序能有新意和启发性,并能更好地揭示一些重要但很少被注意到的关联性。在梳理整个事件历史的过程中,我一直遵循,而且有时不得不牢牢地抓紧一条将奥地利、匈牙利、苏联、波兰和法国串联在一起的特殊线索。这是一条大人物们有时似乎已经遗忘了的线索:通货膨胀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应对办法。
然而,我并不敢凭借本书中的讨论,就对人性和通货膨胀做出生硬的结论,因为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更不敢据此细述任何经济方面的教训,或沉溺于对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中。本书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做经济研究。但是,通货膨胀既与钱有关,也与人有关,要想再现那段历史,就不得不反复地提到数字,有时甚至是庞大的数字。中欧人民多年来饱受庞大的数字的困扰和折磨,直至崩溃。1922-1923年马克的价值让人们记忆犹新,但谁能真正理解一个数字后面跟着12个零意味着什么呢?
1923年10月,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提到,一英镑能兑换的马克数等于地球到太阳之间的码数(1码等于0.9144米)。德国国家货币专员(Germany’s National Currency Commissioner)沙赫特(Schacht)博士解释说,一战结束时,理论上人们可以购买500000000000个鸡蛋的货币,在五年后只能买到一个鸡蛋。当恢复稳定后,购买一个金马克所需的纸马克[2]的数量恰好等于将一平方公里换算成平方毫米的数值。我不确定这样的计算是否有助于大家理解当时的情况,这只是为了让不擅长数学的读者能更有信心继续阅读此书。
由于各国对巨大数字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我尽量避免使用十亿和万亿这样的表示方法,因为这些说法的使用习惯差异相当令人困惑。当我不得不这样做时,我会给出适当的说明。
在写作过程中,想用简洁而又不重复的形容词来描述当时德国人民所遭受的一连串持续恶化的不幸,是比较困难的。劳埃德·乔治先生(Lloyd George)在1932年的文章中提到了这种困难,他说,诸如“灾难”“毁灭”和“困境”这样的词已经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不再能激发人们任何真正的忧虑感。灾难本身被低估了:在当时的文件中,灾难这个词被年复一年地用来描述比上一次糟糕得多的情况。当马克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整个德国满目疮痍时,仍然可以听到德国人在预测未来的灾难。
因此,我试图将文中的灾难、崩溃、大灾变、垮塌和困境等词的使用数量以及危机和混乱的使用程度,限制在可理解的范围内,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在脑海中补充更多的内容。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读者还须独立判断。为了说明马克贬值的幅度,书中经常需要将所涉及的马克金额换算成20世纪20年代的英镑或美元。遍及西方各国的持续通胀过程,使得将当时马克换算为现今的价值毫无意义。为了能减少换算量,我仍然使用了12便士兑换1先令和20先令兑换1英镑的英国旧币制。由于年代久远,生活费用的比较是相当无用的;但是,如果需要计算的话,将1920年的英镑乘大约15倍才能得到与1975年中期差不多等值的金额。因此,1919年200英镑的工资今天可能价值3000英镑;10先令今天价值约7~8英镑。如果是美元,乘6倍或8倍就足够了。如果说1913年的1马克在1975年可以买到约1英镑的商品和服务(显然,有些商品要贵得多;其他商品如劳动力的实际价格要比现在便宜得多),那么,对于英国读者来说,可以想象花148000000英镑去买一张邮票,不管这种想象是饶有趣味还是令人苦恼,一个简单粗暴的换算方法是直接把马克当成英镑就行了。
要准确地理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后期阶段,没有固定的经验法则。在1921年秋季之前,马克在德国国内的贬值速度有时远远落后于国外,这使得德国成了外国游客的天堂。后来(从1922年初开始),随着公众对马克信心的消退,国内价格随着美元汇率迅速上调,到最后大家甚至对马克的下跌有着坚定的预期。这严重混淆了当时问题的另一个现象,并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引发了经济学家的兴趣。
我相信,本书讲述的是一个道德故事。这个故事深刻证明了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想摧毁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摧毁它的货币。因此,健全的货币制度必须是一个社会自我防御的第一道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