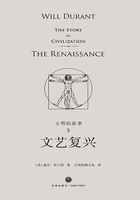
第二章 | 阿维尼翁的教皇(1309—1377)
巴比伦之囚
1309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把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他的提升应归功于法王菲利普四世,他不但把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 Ⅷ)逮捕、侮辱,而且几乎将其饿死。在对菲利普王的粗野无礼表示愤恨的罗马,克莱门特的生命是不安全的。此外,在神圣学院里,法籍的红衣主教已构成大多数,并拒绝将自己信托给意大利。因此克莱门特在里昂和普瓦捷(Poitiers)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为了避免在普罗旺斯伯爵菲利普的领土中的臣属关系,他定居于阿维尼翁,刚好与14世纪的法国隔罗讷河相对。
从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到博尼费斯八世,要使国王臣属教皇而构成欧洲的世界城邦的努力终归失败,民族主义已胜过神权政治的联邦主义。即使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两共和国,伦巴底的城邦和那不勒斯王国也拒受教会的控制;在罗马,共和国两次推选领袖;在其他的教皇国中,军事冒险家和封建大人物——巴格廖尼(Baglioni)、本蒂沃利(Bentivogli)、马拉泰斯塔(Malatestas)、曼弗雷迪(Manfredi)、斯福尔扎(Sforzas)等——以其虚张声势的权威,取代了教皇的代理人。在罗马的教廷已握有几百年的特权,各国人对其致敬,并缴纳税金;但由数位法籍教皇所组成的教廷(1305—1378年),几为法王所禁锢,并借巨款给法王以从事战争,对于德国、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英国而言,教廷成了对立方或法国君主在心理上的武器。这些国家越来越不理会教廷的破门律和停止教权令,只是勉强地给予日渐衰微的敬意。
克莱门特五世很有耐心地和这些困难对抗——若称不上坚毅不屈的话。他尽可能不向菲利普四世屈服。菲利普四世以对博尼费斯八世验尸来调查其私人行为和信仰来恐吓他。为募集资金,教皇出卖教俸职位给最高价的投标者;但他对赞同安吉斯(Angers)市长和门德(Mende)主教把教会道德和教会改革的建议提交威尼斯会议(1311年)的言论,却予默认。他自己过着光明正大、节俭朴实的生活,而且表现出喜怒不形于色的虔诚。他保护伟大医生及教会批评家阿诺德(Arnold of Villanova),使他不致因异端而受到迫害;他重组在蒙彼利埃有关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医学的研究,尝试在各大学设立希伯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讲座,但失败了。除了事务上的麻烦之外,他又增了一种痛苦的病症——狼疮(lupulus),可能是瘘(fistula)——使得他避开社会,并于1314年死去。若能在较好的环境里,他可能是为教会添光彩的人。
随之而来的混乱期,暴露了时代的弊端。但丁曾写信给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促其支持一位意籍教皇并回到罗马去。但是在23位红衣主教中,只有6位是意大利人。当红衣主教团(选教皇的秘密会议)在靠近阿维尼翁的加本脱拉的一个被锁着的房间 开会时,被另一群来自法国的加斯康(Gascon)的居民包围,他们喊着:“将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弄死!”这些高僧的房子被攻击和摧毁。群众纵火焚烧安置红衣主教团的房子。红衣主教们破墙而逃,四散逃逸。两年之久没有再选教皇。最后在里昂,在法军的保护之下,红衣主教向教廷推举一位已经72岁的老人,人们可能很自然地预料他不久就会死,但他却以坦白的热诚、不知足的贪欲和帝国的意愿,注定统治教会18年之久。约翰二十二世,一个补鞋匠之子,在法国南部的卡奥尔(Cahors)诞生了。有权威的教会相当民主,使一个补鞋匠之子升到基督教国的最高位,这是第二次——乌尔班四世即以此出身当选教皇的。约翰曾被延聘为那不勒斯法籍国王之子的教师,他研究民法和教会法颇有成果,因此颇受该王宠幸。由于该王的推荐,博尼费斯八世任命他为弗雷瑞斯(Fréjus)的主教,而克莱门特五世则提升他任职于阿维尼翁教区。在加本脱拉,那不勒斯的罗伯特王的金子压制了意籍红衣主教的爱国心,这位补鞋匠的儿子也成为教皇中最为坚强的一位。
开会时,被另一群来自法国的加斯康(Gascon)的居民包围,他们喊着:“将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弄死!”这些高僧的房子被攻击和摧毁。群众纵火焚烧安置红衣主教团的房子。红衣主教们破墙而逃,四散逃逸。两年之久没有再选教皇。最后在里昂,在法军的保护之下,红衣主教向教廷推举一位已经72岁的老人,人们可能很自然地预料他不久就会死,但他却以坦白的热诚、不知足的贪欲和帝国的意愿,注定统治教会18年之久。约翰二十二世,一个补鞋匠之子,在法国南部的卡奥尔(Cahors)诞生了。有权威的教会相当民主,使一个补鞋匠之子升到基督教国的最高位,这是第二次——乌尔班四世即以此出身当选教皇的。约翰曾被延聘为那不勒斯法籍国王之子的教师,他研究民法和教会法颇有成果,因此颇受该王宠幸。由于该王的推荐,博尼费斯八世任命他为弗雷瑞斯(Fréjus)的主教,而克莱门特五世则提升他任职于阿维尼翁教区。在加本脱拉,那不勒斯的罗伯特王的金子压制了意籍红衣主教的爱国心,这位补鞋匠的儿子也成为教皇中最为坚强的一位。
他表现了极罕有的综合才艺:学术上的研究和行政上的技能。在他的领导下,阿维尼翁教廷发展成能干的官僚组织和强有力的财政部,而欧洲各国大臣对教廷收集税收的能力,既震惊又羡妒。因为募款,约翰遭受到12次重要抗议;和他的先辈一样,他也出卖教俸职位,一点都不羞赧;用种种技巧,这位卡奥尔银行城的子弟充实了教廷的财富,到他死时教廷已拥有1800万弗罗林和价值700万美元的金银器皿和珠宝。他解释说罗马教廷已失去来自意大利的收入,且必须重建官员、职员队伍和海陆军。约翰似乎认为,他能赢得财神爷的眷顾,使它站在自己这边,这样才能为上帝提供最佳的服务。他个人的习惯则趋向于有节制的淳朴。
同时,他赞助学术,参与佩鲁贾和卡奥尔的医事学校的建立,在亚美尼亚创立拉丁学院,资助大学,鼓励东方语言的研究,对抗炼金术和魔术,日夜研究神学,以至被猜疑为异端的神学家。也许为了抑制主张直接与上帝接触的神秘学说的传播,他冒险地教训说无人——即使是上帝的母亲——能达到快乐的幻景。抗议的风暴在末世学人士中掀起:巴黎大学公开指责教皇的观点,在温森斯(Vincennes)召开的宗教会议谴责其为异端,而法国的菲利普六世命令他更改其神学说。这位狡猾的90高龄教皇以死来规避他们所有的人(1334年)。
约翰的后继者是脾气更温和的人。贝尼狄克特十二世教皇,为面包商之子,他试着想要成为基督徒和教皇;他拒绝将职位分授给亲戚;他因颁教俸职给有功而非行贿的人,而招致敌意;在教会行政的各分支机构中,他压制贿赂和腐化的行为;他以命令托钵僧改革来没收其神职;他以不在战争中残酷和流血闻名。所有腐化的力量都因他的早死而快乐(1342年)。
利穆赞(Limousin)贵族出身的克莱门特六世,习惯于奢侈、逸乐和艺术,不明白在教廷的财富充裕时何以教皇应该朴素。几乎所有到他那儿求一官半职的人都得到了,他说没有一个人离他而去时会不满意。他宣布任何一个穷教士在以后两个月内来找他的,均可分享其富裕;一个目击者推算有10万人到来。他赠厚礼给艺术家和诗人;维持一种马场,足以与基督教国家内任一种马相匹敌;允许妇女自由进出教皇宫,欣赏她们的妩媚,而以高卢式的殷勤和她们厮混在一起。特里尼(Turenne)的女伯爵与他如此亲近,以致她毫无顾忌地公开出卖教会的高职。听到克莱门特的好脾气,罗马人派使节邀他进驻罗马。他不喜欢这个邀请,但他以宣布嘉年会——博尼费斯八世在1300年所创,每100年一次——改为半世纪庆祝一次来使他们满足。罗马人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把里恩佐废了,在政治上又重新归顺教皇。
在克莱门特六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不但成为宗教的首都,而且成为拉丁世界在政治、文化、享乐和腐化方面的首都。现在教会的行政机构已成固定的形式:一个罗马教皇议事厅(Apostolic Chamber)——主管财政,以地位仅次于教皇之教皇会计员(Papal Chamberlain)为首;一个罗马教皇法庭(Papal Chancery)——其七位教皇代理人由一位红衣主教副首席大法官指挥,掌理罗马教廷的信件;一个罗马教皇司法部(Papal Judiciary)——由高位教士和教外擅长教会法的人组成,并包括一宗教法庭——由教皇和红衣主教组成,充当上诉法庭;一个罗马教皇宗教裁判所(Apostolic Penitentiary)——一所处理婚姻的赦免、开除教籍和教权停止的教士学院,并听取教皇赦免者的忏悔。
为了安置教皇及其助手,这些阁员和代理人,他们的职员和仆人,新建了广阔的教皇皇宫。它集哥特式建筑的大成——起居室、议事厅、小礼拜堂、办公室——围绕着两个宫院,而其本身则为强大的防御物所围绕。该建筑物的高度、宽度和高大之塔,暗示着一旦教皇被围,也不必靠奇迹来保护他们。贝尼狄克特十二世邀乔托来装饰皇宫和邻近的天主教堂;乔托计划要来,却死了。1338年,贝尼狄克特从锡耶纳召来马蒂尼,其壁画现已湮没,当时却是阿维尼翁绘画的最高象征。在这个皇宫的四周,在次要的宫院、大厦、住宅区和茅舍里,聚集了高位教士、使节、律师、商人、艺术家、诗人、仆人、军人、乞丐及从有教化的高级妓女到酒店妓女的每一阶级的娼妓,这些构成了庞大的人口。在此,住着很多主教,他们的教区已陷入非基督徒手中。
习惯于巨大数字的我们,能够想象到,用以支持这一复杂的行政机构及其周围的人所需的金钱数量。几个收入的来源近乎干涸:被教廷所弃的意大利,几乎无法送任何钱来;与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不睦的德国,只送往常之贡的半数;几乎把教廷掌握在其统治中的法国,把法国教会岁入的大部分拨作世俗用途,而且从教廷借巨款来支付百年战争;英国则严限金钱流入事实上是法国联军的教廷。为了应付这一情况,阿维尼翁的教廷被迫增加岁入。每位主教或修道院长,不管是由教皇或世俗的领主任命,须将未来一年收入的1/3转送给教皇,以作为就职费,且须付日益骤增的报酬,给曾支持他被任命的居间人。若他成为大主教,他就必须为大主教的白羊毛大披肩(白羊毛的圆形带,穿在十字褡上,作为其职务的标志)付出为数可观的费用。当一位新教皇被选出时,每个有教会的教俸职位者,须付第一年岁入的全数给教皇,以后则每年付其岁入的1/10,额外的自动贡献当然更好。任何一位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长死时,其个人所有物及动产均归教廷。而在此死亡和新受任命者的安置过渡期内,教皇接受教俸职的岁入,及教区收入,而教皇们常被控以有意延长这个期限。教会中每个新受任命者对其前任未付之费(税),有偿付之责。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长往往还拥有国王的封地,他们必须向他进贡,并供他以军队,因此他们有许多人被迫要承担这一由教会和世俗所结合而成的义务。因为教皇索取的税比城邦索取的更加严苛,我们发现僧侣有时支持国王来反对教皇。阿维尼翁的教皇几乎忽视选主教的天主教士团会议或选修道院长的修道院会议的传统权力,此举使愤恨日益累积。在教廷司法部所审判的案件,常须花很多钱请律师帮忙。律师则须付年税,以获得在教廷法庭辩护的执照。每年审判或得自教廷的恩宠,都期望因感激而送礼,甚至任圣职的许可权也必须用钱买。欧洲世俗的政府,以敬畏和愤恨的眼光看待教皇的财政机构。
抗议在每个地区兴起,教会内部也不鲜见。西班牙高僧佩拉尤(Alvaro Pelayo)虽然完全忠于教廷,也写了《教会的哀歌》(On the Lamentation of the Church),在此文中他哀悼:“无论何时,当我进入教廷的房间,我都发现掮客和教士正在称量计算着堆在他们面前的钱……狼控制着教会,而且吃着基督徒羊群之血。”红衣主教奥西尼(Napoleone Orsini)发现,几乎所有意大利主教区皆成为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交换品或王族阴谋的对象,他因此深感困扰不安。擅长于征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提醒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说:“使徒的继任者是被委派去引导主的羊群到牧场去,而非剪其毛的。”英国国会通过几个法规来阻止教皇在英国的征税权。在德国,教皇的收税员被追捕,被押于狱,被弄成残废,或被处绞刑。1372年,科隆、波恩、克森腾(Xanten)、美因茨等地的教士立誓不付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所要求的什一税。在法国,许多圣俸因战争、黑死病、土匪的抢劫和教皇收税员的强索等因素而遭破坏,许多本堂牧师放弃了他们的教区。
对这样的抱怨,教皇们的答复是教会的管理需要大量的钱财,不腐化的代理人难以发现,而他们自己也处在困难的大海中。可能是在受威胁之下,克莱门特六世借59.2万弗罗林给法王菲利普六世,借351.7万弗罗林给法国的约翰二世,征服失去的意大利教皇城邦也需要大量的开销。尽管有这些税收,教皇们仍饱受财政赤字之苦。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从自己的资产中拨出44万弗罗林才挽救了教皇财政的危机;英诺森六世则变卖他自己的银盘、珠宝和艺术品;乌尔班五世则必须自其红衣主教中借3万弗罗林;格列高利十一世死时尚欠债12万法郎。
批评家反驳说,赤字的产生,不在于合法的开销,而在于教廷及其食客世俗方面的奢侈。克莱门特六世的四周是穿着珍贵质料衣服和皮衣的男女亲戚;还有国王所羡慕的武士、乡绅、卫士、牧师、管家、音乐家、诗人、艺术家、医生、科学家、裁缝师、哲学家和厨师等——总计有400人左右,全由过度慷慨的教皇来供吃、穿、住和付给薪俸。克莱门特自认为自己是这样的统治者:使臣民敬畏,并以追随国王的习尚而使“耗费引人注目”来加深大使们的印象。而红衣主教们,以城邦的皇家议员和教会的领主自居,必须使许多机构维持到与其尊严和权力相衬;他们的随从、装备、宴飨成为城市居民的谈资。也许红衣主教卡沃斯的伯纳德做得过分了,他租了51处住屋安置他的门客;红衣主教班哈克的彼得10个马房中的5个既舒适又不失时尚品位,蓄养了39匹骏马。即使主教也陷入这一习尚中,不顾来自各省的宗教会议的抗议,而保有富丽的机构,有弄臣、鹰、狗为伴。
阿维尼翁现在渐渐取代教廷在道德和礼仪方面的地位。贪污事件是恶名昭彰的,门德的主教都兰德(Guillaume Durand)曾在维也纳宗教会议中报告说:
若罗马教会以从本身除去恶例来开始改革,则整个教会可能得以被改革……因该恶例,人们受到侮辱,而整个民族似乎感染到……因在所有的地方……上帝的神圣教会,尤其是罗马教会,是在恶名中;所有的人呼叫而且在外宣扬说,在教会的胸中,所有的人,从最伟大的到最渺小的人,都已把心放置在贪婪的事物上……所有基督徒学习教士暴食的恶例是显然而恶名昭彰的,因为该教会人士比领主和国王宴飨更加奢侈丰盛。
而文辞大师彼特拉克,搜尽诽谤词汇,把阿维尼翁教皇所在地侮辱为:
这不虔诚的巴比伦,地球上的地狱,罪恶的渊薮,世界的阴沟。在此既无信仰,也无仁爱、宗教、对上帝的敬畏……世上所有的丑行和邪恶,荟萃于此……老年人热烈而轻率地沉溺于维纳斯的手臂中,忘其年龄、尊严和权力,他们对羞愧之事,趋之若鹜,好像他们的荣耀不在耶稣的十字架,而在宴乐、酗酒、不贞……教皇游戏的猥亵之逸乐是血亲相奸、强奸和通奸。
这样的证言,出自于从未脱离正教的目击者,不能完全地不予采信,但它不无夸张和个人愤恨之鸣。它必须打折扣,因为那是恨阿维尼翁把教廷自意大利攫取来的人所发出的呼声;他曾向阿维尼翁教皇乞求教俸职,接受了很多教奉职,却要求更多;他同意跟善于杀人和反教皇的威斯孔蒂住在一起,自己也有两个私生子。彼特拉克曾不断请求教皇回到罗马,当时罗马的道德,除了贫穷有助于其贞洁之外,在当时并不比阿维尼翁好。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在描写阿维尼翁时不如彼特拉克那么生动,但她告诉格列高利十一世,在教廷,“她的鼻子受到地狱的气味的攻击”。
在道德的衰微中,许多高僧有资格担任其职位,而他们也偏爱耶稣的道德甚于当时的道德。我们不能把集在阿维尼翁的罪恶都归由教皇来负责,在七位阿维尼翁教皇中,只有一位过着世俗的享乐生活;而约翰二十二世尽管贪婪而严苛,却把自己训练到苦行而严肃的境地;格列高利十一世虽然在战争中残忍,平时却是一位在道德和虔诚上可做典型的人物;而另三位——贝尼狄克特十二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几乎是过着圣徒般的生活。罪恶的原因是财富,而许多其他时代也因之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尼禄时代的罗马,利奥十世时代的罗马,及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而且就像在上面提过的城市一样,我们可以理解到,大部分男女都过着正经的生活,惯做适当的恶习,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到,即使在阿维尼翁,好色之徒和高等娼妓,贪食者和窃贼,行为不正的律师和不诚实的法官,世俗的红衣主教和不忠实的牧师,只不过是因被教廷考察出来,有时受到赦免,而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显得突出而已。
丑闻案和教皇从罗马逃亡到阿维尼翁,一同腐蚀了教会的声望和权威。好像是要证实人们对他们的猜疑——他们不再是世界的权力中心,而只是法国的工具,阿维尼翁教廷任命了113名(总数134人)法籍红衣主教到主教学院。英政府在威克利夫(Wyclif)毫不妥协地攻击教廷,他们却假装听不见。德国的选帝侯在选国王和皇帝时,拒绝受到教皇的任何干涉。1372年,科隆大监督区的修道院长们,在拒付什一税给格列高利十一世时,曾公开宣称:“教廷已陷入如此的侮辱中,天主教的信仰在这些地方似乎已受到严重的损害。俗人轻蔑地提到教会,因为她远不若往昔派出牧师或改革者,反而派一些狡猾、自私、贪婪的人,事情已到此形势,很少人是真基督徒,只是徒具虚名而已。”
这就是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的巴比伦之囚和随之而来的教皇分裂,这为宗教改革做了准备。而他们回到罗马,恢复他们的特权,也将此大灾延后了一个世纪。
通往罗马之路
教会的地位在意大利最低。1342年,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二世,削弱反叛的巴伐利亚的路易,巩固了伦巴底诸城独裁者违抗帝国要求的权威。为了报复,巴伐利亚的路易赋予占领教皇城邦的独裁者以帝国的许可。米兰公开嘲弄教皇。当乌尔班五世派遣两位使节到米兰,带着开除威斯孔蒂王族教籍的训谕(1362年),贝尔纳博(Bernabò)强迫他们把该训谕——羊皮纸文件、丝带、铅印——吃下去。西西里自从“晚祷”事件 (Vespers)以来,已公开对教皇的敌意。
(Vespers)以来,已公开对教皇的敌意。
克莱门特六世组织军队,要重夺回教皇城邦。但是直到其后继者英诺森六世才使这些城邦短暂地归顺。英诺森几乎是模范教皇。在姑息几个亲戚的任命之后,他决定终止族阀主义和腐化的流行。他结束了教廷享乐派的显赫和浪费的开销,解雇了曾服侍克莱门特六世的大群仆人,遣散大群职位的寻求者,命令每个牧师住在其教俸区,而他自己则过着诚笃而中庸的生活。他看出,教会的权威只有从法国权力中解放和回到罗马中恢复。但一个为法国所疏远的教会,没有以前从教皇城邦而来的岁入,几乎很难自行维持下去。和平的英诺森断定这些只有从战争中才可重新求得。
他把这项工作托付给一个人,此人有西班牙人的热诚信仰,有圣多米尼克的精力,有卡斯蒂尔大公的侠义精神。阿布诺佐(Carrillo de Albornoz),曾在卡斯蒂尔的阿方索十一世部下当兵,而且在成为托莱多(Toledo)大主教时仍未放弃战争。他劝说佛罗伦萨共和国——它惧怕围绕其四周的独裁者和强盗——预付他一笔款项以组织军队。以机敏而光荣的协议,而非用武力,他逐一废除占领教皇城邦的卑鄙暴军。他颁给这些城邦以《埃吉迪安宪法》(Egidian),该宪法使他们的基本法律维持到19世纪,而且提供了在自治政府和归顺教廷之间一种可实行的妥协。他哄骗了著名的英国冒险家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加以俘虏,而使这位雇佣兵队长陷入害怕教皇使节的境遇中。他从反叛的大主教手中恢复了博洛尼亚,他劝说米兰与教会媾和。现在路已敞开,只待教皇返回意大利。
乌尔班五世继续英诺森六世的苦修和改革。他尽力恢复教士团和教廷的清规及诚实,不支持红衣主教的奢侈,阻止律师的狡猾手段和高利贷者之敲诈,惩罚圣职买卖,因而赢得德行、心智俱优者为他服务。他以自己的资产维持在大学的1000名学生,在蒙彼利埃新创一学院,资助许多著名学者。为了教皇一职之加冕,他决心把教廷恢复到罗马。红衣主教对此表示惊异。他们大多数已在法国生根,建立了感情,而为意大利所憎恨。他们乞求他不要理会圣凯瑟琳的请求或彼特拉克的口才。乌尔班向他们指出法国的混乱情况——国王为英国俘虏,军队破碎不堪,英国已征服其南部各省,而且进逼阿维尼翁。胜利的英国会如何对付一向服侍并资助法国的教廷呢?
因此,1367年4月30日,他从马赛起航,由意大利的大木船护送。10月16日,他在百姓、教士团、贵族的狂呼中,进入罗马;意大利的领主们握着他所骑之骡的缰辔;彼特拉克对这位法籍教皇敢驻意大利,倾吐忠言,表示感谢。那是荒凉却快乐的罗马:由于和教廷长久分离而赤贫,教堂一半被弃或衰颓,圣保罗教堂在毁坏中,圣彼得教堂好像随时有倾倒之虞,拉提朗宫(Lateran Palace)最近毁于大火,皇宫与住宅区都已倒塌,曾经的住宅之地现成为沼泽,住宅区和街道上满是没有收拾的垃圾。乌尔班下命令并分配基金以重建皇宫。因为不愿看到罗马的悲惨景象,他住在蒙提费阿松(Montefiascone)。但即使在那里,每当回想到阿维尼翁的奢华和法国的可爱,他不禁悲从中来。彼特拉克听说他有犹豫之意,便力促他坚忍不屈;瑞典的圣伯里吉特(St. Bridget)预言,他若离开意大利,将很快死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为了使他坚强,许可他恢复中意大利,很谦虚地到罗马来(1368年),引导教皇的马从圣安杰洛教堂到圣彼得教堂,在弥撒时服侍他,而且在典礼中接受他的加冕,这似乎能很快地治愈帝国和教廷之间的旧争。然后,1370年9月5日,也许是屈服于法籍的红衣主教,或者是为了促使英国和法国讲和,乌尔班乘船前往马赛。9月27日,他到达阿维尼翁,就在那里,他于12月19日去世。依圣本笃僧人的习惯穿着,他躺在一张可怜的椅子上,而且死前曾命令所有愿进来者均可进入,人们得以见到这一最高贵者的显赫是如何的虚幻和短暂。
格列高利十一世在18岁时,已被和蔼的克莱门特六世任命为红衣主教;1370年12月29日,他被封为牧师;12月30日,39岁的他,被选为教皇。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喜欢西塞罗的作品。命运使他成为爱战争的人,而在暴烈的反叛中,他的教皇职位被取消了。乌尔班五世担心法籍的教皇尚不能信任意大利人,因为曾任命很多法国人为总督去统治教廷城邦,却发现他们在对其有敌意的环境中,建立碉堡以抗人民,并征来无数法国助手,对人民征课以重税,而且宁采暴政而不用圆通的手段。在佩鲁贾,一位总督的侄子追求一位已婚妇女,她为了逃避他,竟跳楼自杀。当代表团要求惩罚此人时,该总督回答:“何必小题大做?你认为法国人是宦官吗?”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总督们招来同样的仇恨,以致在1375年许多城邦以一连串的革命群起反抗。圣凯瑟琳自己成为意大利的发言人,力促格列高利除去这些“毒害并蹂躏教会花园的坏牧师”。一向是教皇盟友的佛罗伦萨,却领导此次运动,展开一面绣有金色字“自由”的红旗。1375年初,64座城邦曾承认教皇为民间和精神的领袖;1376年,只有一座仍效忠于他。阿布诺佐的努力似乎因此破灭,意大利中部又从教廷脱离了。
格列高利受到法籍红衣主教的鼓励,控告佛罗伦萨人为反叛的领袖,并命令他们顺从教皇的总督。当他们拒绝时,他开除他们的教籍,禁止他们在城内做宗教礼拜,并宣布所有的佛罗伦萨人为罪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均可侵占其货物,奴役其人民。整个佛罗伦萨城的商业和财政结构受到崩溃的威胁。英国和法国立即搜捕境内的佛罗伦萨人,并掠夺其财产。佛罗伦萨则报之以没收境内所有教会的财产,摧毁宗教裁判所的建筑物,关闭教会法庭,把顽固的牧师下狱——有时施以绞刑,并派人向罗马人民呼吁加入革命,而且终止教会在意大利所有的世俗权力。当罗马犹豫不决时,格列高利派人告诉罗马,若仍效忠于他,他将郑重地答应将教廷迁回罗马。罗马人民接受这一保证,保持和平。
同时,教皇已派遣了一支由“凶猛的”日内瓦的罗伯特红衣主教所指挥的“野蛮的不列颠雇佣兵”到意大利。总督以难以置信的野蛮方式作战,被占领的西斯纳已蒙大赦,他却把全城男女、孩子都杀了。领导雇佣兵为教会服务的约翰·霍克伍德在法恩扎杀了4000人,因为他猜疑此城有意加入反叛。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对这些残暴的行为——相互没收财产,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为此中断宗教礼拜——感到震惊不已。她写信给格列高利:
你的确有义务赢回从教会中失去的领土,但你更有义务赢回真正属于教会财宝的所有羔羊,而其损失将会真正使教会赤贫……你应以善良、爱情与和平的武器来攻击人,那么你的所得将甚于用战争为武器。当我探询上帝,你的解救,你的恢复教会,及整个世界,其至善之策是什么时,除了和平并无其他的回答!和平!为了背上十字架的救主,和平!
佛罗伦萨邀她一起会见格列高利的特使。她去了,并借此机会谴责阿维尼翁的道德。她太坦率,许多人要求逮捕她,但格列高利保护她。此行的任务并没有立即生效。但当他听说除非他亲自来,否则罗马将加入反叛,格列高利——也许是被凯瑟琳的请求所感动了——从马赛出发,于1377年1月17日到达罗马。他并没有受到全体一致的欢迎,佛罗伦萨的呼吁已激起老共和国人在退化的城里的回忆,而格列高利被警告说他的生命在基督教国的古都里是不安全的。5月,他退居到阿纳尼。
现在,似乎终于屈服于凯瑟琳,他从战争转向外交。他的代理人鼓励各城邦的百姓——他们渴望与教会和平相处——去推翻其反叛的政府。对所有归顺于他的城邦,他答应在他们自己所选的教皇代理人统治之下组织自治政府。一城接一城地,这一条件被接受。1377年,佛罗伦萨城与格列高利同意让贝尔纳博·威斯孔蒂调停争端。贝尔纳博已经劝服教皇把其可能向佛罗伦萨强索的罚款的半数给他,他让佛罗伦萨付80万弗罗林的赔偿给教廷。由于被其盟友所弃,佛罗伦萨愤怒地服从,但教皇乌尔班六世却把给贝尔纳博的钱减少到25万弗罗林。
格列高利并未活着看到他的胜利。1377年11月7日,他回到罗马。他在阿维尼翁时已是一个病人,而在中意大利时并没有很好地度过冬天。他感到死神的来临,惧怕法国和意大利争夺教廷的冲突可能会把教会搞得支离破碎。1378年3月19日,他迅速地安排继任人选。8天后,他死了,渴望着法国的美丽故乡。
基督徒的生活
把人民信仰和教士团道德这方面的事情延到下一章去考虑,现在让我们先注意14世纪意大利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对应的特征:宗教裁判所和圣徒。公正需要我们记得:当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相信上帝的儿子已把教会建立,而且已把基本教条立下;因此,不管其人类的职员可能有何过失,试图推翻教会的任何活动都是反叛神圣的权威和背叛由教会为其道德武力之世俗城邦。唯有在心理上有此思想,我们才能了解教会和俗人联合压制诺瓦拉的多西诺(Dolcino of Novara)及其美丽的姐妹玛格丽塔(Margherita)所传播之异说(约为1303年)的那种残忍行为。
像弗罗拉的约阿基姆(Joachim of Flora),诺瓦拉的多西诺把历史分成几个时期,其中的第三期从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ylvester I)到1280年,可以见到教会由于世俗的财富而渐渐腐化;从西尔维斯特以来(多亚诺说),除了教皇西里斯廷(Celestine)五世以外,所有的教皇均不忠于耶稣;圣本笃、圣方济各、圣多米尼克曾很高贵地试图把教会从财神手中赢回到上帝手中,但失败了;而现在的教廷,在博尼费斯八世和克莱门特五世的统治之下,成为《启示》(Apocalypse)里的大淫妇。多西诺使自己成为新同宗会——帕尔马使徒同宗会(Apostolic Brethren of Parma)——的领袖,他不接受教皇的权威,而从帕塔林斯(Patarines)、韦尔多教派和弗朗西斯科圣灵派(Spiritual Franciscans)继承了一种混合的教条。他们承认绝对的贞洁,但他们每一人都和一个被称为其姐妹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克莱门特五世命令宗教裁判所去调查他们,他们拒绝出现于裁判所;相反,他们武装自己,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皮德蒙特(Piedmontese Alps)山脚下的阵地。那些调查者带领军队来镇压他们,血战因之而起。同宗会员退守山隘,在那儿他们被封锁并忍受饥饿,吃鼠、狗、马和草;最后,他们的山上要塞受到猛攻,1000人陷入战争中,数千人被烧死(1304年)。当玛格丽塔被带去接受火烙之刑时,她仍如此美丽,尽管有些憔悴。只要她肯发誓否定异说,她将被赦免。她拒绝了,因而被慢慢地烧死。多西诺及其同志隆基诺(Longino)被留活口,以作特别处理。他们被押送到马车上,到韦尔切利遍游全市之街道。在游行中,他们的肉被热钳一撮一撮地撕裂,他们的肢体和生殖器被从身上扭取掉,最后才被杀死。
同一世纪,我们见到阿维尼翁的灾难和腐化,也见到像科维诺(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和波第诺(Oderic of Pordenone)的传教士,他们设法使印度人和中国人改变信仰。很明显,这些传教士对宗教上之贡献远不如地理上的贡献。
终其一生,圣凯瑟琳待在现在仍供游客瞻仰的朴素房间里。在这里,她帮助教廷,而且使意大利的虔诚复活。15岁时,她参加圣多米尼克的忏悔仪式。这是一种“第三会员”的组织,并非由僧尼组成,而是由过着世俗生活的男女组成,但他们尽可能献身于宗教工作和过贞洁的生活。凯瑟琳和其父母住在一起,但她使自己的房间几乎成为隐遁者的密室,陷于祈祷和神秘的沉思中,除了上教堂外几乎足不出户。她对宗教的狂热很令其父母为她的健康担心。他们课她以最繁重的家务工作,她毫无怨言地做了。她说:“我的心很少角落是和耶稣分开的。”她保持孩童般的宁静。其他女孩子可从渎神的爱中得到的乐趣、怀疑和狂喜,凯瑟琳则在对耶稣的奉献中发现快乐。在这种孤独沉思的日渐增强状态中,她想到、提到耶稣,把他当作天上的爱人,她和他心心相印,在异象(vision)中她看到自己和他结婚。像圣方济各那样,她对这位被钉上十字架者的五个伤口想得如此之久,以致她感到好像那些伤口就在自己的手、脚和肋旁似的。当撒旦的诡计要使她从全神贯注的爱中撤退时,她拒绝了肉体的诱惑。
在近乎3年孤独的虔诚岁月之后,她感觉到能很安全地冒险去过都市的生活。就像她能把女德奉献给耶稣一样,她把母性的温柔献给锡耶纳的病人和穷人。她和时疫牺牲者相处到最后一刻,以精神上的安慰站在受罚的罪犯身旁,直到他们上刑的时刻到来。她父母死后,留给她一份不太多的财产,她全都分给了穷人。虽然她因天花而破相,但她的脸对于所有看过她的人而言,都是一种祝福。年轻人听到她的话,放弃了平日渎神的行为,老年人听到她那单纯可信的哲学,把怀疑熔化了。她以为人类生活中所有的罪恶都是人类不道德的结果;但人类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耶稣之爱的海洋中,被吞掉而消失;世上所有的罪恶,若人能被劝服而实践基督教之爱,则都可被治愈。许多人相信她,蒙特普西亚诺(Montepulciano)城请她来调停其世仇的家族,比萨和卢卡城的人向她请教,佛罗伦萨城邀她共同出使阿维尼翁。渐渐地,她被带进世俗世界中。
她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很恐怖:罗马污秽而荒凉,意大利和已逃往法境的教会(教廷)脱离关系,教士团过着世俗的生活而丧失俗人的尊敬,法国已因战争而成半毁状态。她对自己的神圣使命有信心,她当面斥责高僧和教皇,而且告诉他们唯有回到罗马和恢复庄重,才能拯救教会。她自己不能写,她——26岁的女子——用单纯而有韵律的意大利文口授严厉而仁慈的信,给教皇、领主和政治家;几乎在每一页上均出现预言式的字——改革。政治家无视她的呼吁,可人民却成就了她。当教皇乌尔班五世到罗马来时,她高兴;当他离去时,她悲伤;当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来时,她欣慰;她进忠言给乌尔班六世,却因他的残忍而震惊;当教廷分裂把基督教国分成两部分时,她本身即是这种不可信的冲突所酿成的灾难之一。她已把食量减少到只吃几口,传说她苦行的程度已达到其唯一的滋养品是从她的自治区所收到的被供奉的圣饼。她失去抵抗疾病的所有力量;教廷的分裂使她丧失生存的意志;在教廷分立两年后,她死了,时年33岁。对于这个时代,她的爱是仅次于耶稣和教会的意大利至善的一种力量。
她死的那一年(1380年),圣贝尔纳迪诺(St. Bernardino)出生了。凯瑟琳的传统铸成了他的性格,1400年的瘟疫中,他日夜照顾病人。这时他已加入圣方济各教团,他立下了遵守修道会严格规律的典型。许多僧侣遵从他,他跟这些人一起创立(1405年)了严修会方济各派(Observantine Franciscans),或称严修会同宗派(Brethren of the Strict Observance)。在他死前,有300个僧侣团体接受其教规。其生活的纯净与崇高赋予其传道不可抗拒的雄辩。即使在罗马——其人民较欧洲任何其他都市的人更为无法无天——他也能使罪犯忏悔,罪人悔改,宿怨和解。在佛罗伦萨城的异教神被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所烧毁的70年以前,圣贝尔纳迪诺劝服罗马的男女把他们的赌牌、骰子、奖券、假发、猥亵的书、画,甚至乐器投入朱庇特神殿前的火葬堆里(1424年)。三天后,一个被控以巫术蛊人的年轻妇女也被烧于同一广场,所有的罗马人蜂拥而至。圣贝尔纳迪诺说他自己是“最有良心的异教迫害者”。
因此,善与恶,美丽与恐怖,混合在基督徒生活的变迁和混乱中。意大利朴实的人们,满足于保持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而中、上阶级的人被长久存于地窖的古典文化之酒醺得半醉,以创造文艺复兴和现代人高贵的热情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