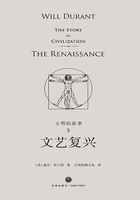
第三章 | 美第奇的兴起(1378—1464)
背景
意大利人称呼这个时代的来临为“再生”,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古典精神被野蛮人打断了千年之后的一大复活。 意大利人觉得,古典世界已在3至5世纪日耳曼和匈奴的入侵中死亡。哥特人的巨掌又粉碎了行将枯萎却风韵犹存的罗马艺术与生活。哥特艺术入侵意大利,带来了形式不稳、装饰古怪的建筑及粗糙、阴郁的先知和圣哲雕像。现在,感谢时间的考验,那些留须的哥特人和长髯的伦巴底人已被意大利人同化;感谢建筑家维特鲁维亚和罗马法庭废墟的影响,古典的廊柱和横梁再度构成了冷静、端庄的神庙和宫殿;感谢彼特拉克和百位意大利学者的努力,新发现的古典作品才能使意大利恢复西塞罗散文的纯粹精简和维吉尔诗篇的成熟音律。意大利精神的阳光即将穿透北方的浓雾。无论男女都从中世纪的恐惧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仰慕各种形式的美,使空气中充满复活的喜悦。意大利眼看就要再度年轻起来。
意大利人觉得,古典世界已在3至5世纪日耳曼和匈奴的入侵中死亡。哥特人的巨掌又粉碎了行将枯萎却风韵犹存的罗马艺术与生活。哥特艺术入侵意大利,带来了形式不稳、装饰古怪的建筑及粗糙、阴郁的先知和圣哲雕像。现在,感谢时间的考验,那些留须的哥特人和长髯的伦巴底人已被意大利人同化;感谢建筑家维特鲁维亚和罗马法庭废墟的影响,古典的廊柱和横梁再度构成了冷静、端庄的神庙和宫殿;感谢彼特拉克和百位意大利学者的努力,新发现的古典作品才能使意大利恢复西塞罗散文的纯粹精简和维吉尔诗篇的成熟音律。意大利精神的阳光即将穿透北方的浓雾。无论男女都从中世纪的恐惧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仰慕各种形式的美,使空气中充满复活的喜悦。意大利眼看就要再度年轻起来。
发表上述宣言的人距离文艺复兴太近,而不能从历史的时距中和它分歧的内容中看清“再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只是古典的恢复而已。首先它得花钱——中产阶级的钱:这些财富来自娴熟的经理和低薪的工人,来自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而作的危险的东方航程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辛苦穿越,来自小心的计算、投资、贷款,来自累积的利息和分红。直到盈余足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足够买下议院、政府、情妇而有余,他们便聘请一位米开朗基罗或提香,把金钱幻化成美,使财产带着艺术的芳香。钱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商人、银行家和教会付款买下了古典再生所需的书稿。但解放文艺复兴时代心灵和理性的也并非那些书稿,而是因中产阶级兴起所造成的现世主义,大学、知识和哲学的发展,研究法律所造成的现实心灵的敏锐,广泛认识世界所造成的心灵的开阔,如此等等。意大利学者怀疑教会的教条,不再害怕地狱。教职人员被看成享乐者和俗人,不再受知识和伦理的限制,他那解放的感官毫不羞赧地欣赏男女艺术等美的化身。在自由使人毁于道德的混乱、分崩的个人主义和国家的奴役之前,新自由让人创造了一个惊人的世纪(1434—1534年)。两个严苛时代之间的插曲便是文艺复兴。
为什么北意大利最先经历复苏的春天呢?该地的古罗马世界尚未完全毁灭,城中还保有古老的建筑和回忆,现在更重新修订了罗马法律。古典艺术仍残存于罗马、维罗纳、曼图亚、帕多瓦等地;万神殿虽然已有1400年的历史,仍是大家礼拜的地方;而西塞罗和恺撒为喀提林(Catiline)命运辩论之声在罗马法庭仍依稀可闻。拉丁语仍是一种活的语言,意大利语只是它的和谐变调而已。异教的神祇、神话和仪式在多数人心中盘旋(或者以基督教的形式出现)。意大利横跨地中海,统领着这个古典文明和贸易的海湾。北意大利比欧洲其他地区更都市化、工业化,只有佛兰德斯可望其项背。它从未遭遇过完全的封建制度,贵族反而臣属于都市和商人阶级。它是意大利其他各地与阿尔卑斯山彼侧的欧洲之间,也是西欧与地中海沿岸之间的贸易通道,工商业已使它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庶的地区。这里勇敢的商人遍及各地,从法国的市集到黑海最远的港口,无处不至。他们已习惯和希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及中国人交易。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教条,也为意大利知识分子带来不重教规的思想。这种情况和19世纪欧洲与异国信仰广泛接触所造成的结果相同。然而,商人的智慧,加上国家传统、个性和自尊使意大利甚至在异教化的时候,也保存了天主教组织。罗马教皇的经费从20个基督教领地沿着千条通道流向罗马。罗马教廷的教产也遍及意大利。教会为了报答意大利人的忠诚,慷慨地宽恕他们肉体的罪恶,和蔼地容忍(1545年的特伦特会议之前)那些自制的、尚未损坏人们虔诚的异教哲学家。就这样,意大利在财富、艺术和思想方面领先欧洲其他地区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已在意大利枯萎,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才开出复兴的花朵。文艺复兴不是时间上的一个段落,而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经过商业、战争的影响从意大利传遍全欧。
它最初的发源地是佛罗伦萨,正如北意大利孕育了它。经过工业的组织、商业的拓展、财政家的经营,“花之都”佛罗伦萨成为14世纪半岛上除威尼斯以外最富庶的城市。当时的威尼斯人将所有精力用于快乐和财产的追求;佛罗伦萨人也许受了狂烈的半民主政体的刺激,发展出敏锐的心智及一切艺术的技巧,使该城被公认为意大利的文化之都。党派的争执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热度,敌对的家族不只竞求权势,也争相作为艺术的赞助人。最后的刺激——不是最初的——则是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Medici)贡献出自己的机智、财产和宫殿以招待佛罗伦萨会议(1439年)的代表。那些前来讨论东西基督教重聚的希腊教士与学者关于希腊文学的知识远非任何佛罗伦萨人可比,部分学者在佛罗伦萨演讲,城中的精英纷纷前去受教。后来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手中,很多希腊人逃离该地,移居到14年前他们曾受款待的城市。有人带来古典教本的书稿,有人演讲希腊语言、诗和哲学。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成为意大利的雅典。
物质基础
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一个城邦,统治着佛罗伦萨城、普拉托、皮斯托亚、比萨、沃尔泰拉、科托那、阿雷佐等城市及附近的农业腹地。农夫不是农奴,一部分是小地主,大部分是佃农。他们住在粗糙的水泥石屋里,自选乡村官员来治理地方事务。马基雅维利并不以结交这些辛苦的田野、果园、葡萄园斗士为耻。但是负责管理货物销售的城市长官,为了安抚多事的劳动阶级,将食物价格定得很低,以致影响了农夫的生活。因此,除了城市中的阶级仇恨外,还有自古以来的乡村、城市之争。
根据吉尔瓦尼·维拉里的记载,佛罗伦萨城在1343年约有9.15万人。至于文艺复兴后期的人口,我们无法找到同样可靠的记录,不过我们可以断言,商业拓展和工业繁荣会使人口增加。大约1/4的城市居民是工人,13世纪仅纺织界即有200个工厂,雇用了3万名工人。1300年,奥利西拉里(Federigo Oricellarii)从东方带来一种用青苔提炼紫色染料的方法,由此得到奥利西拉里这个名字(Orchella,意为紫染料)。这个技巧改革了染料工业,使某些羊毛制造商成为今日所谓的百万富翁。1300年,佛罗伦萨在纺织方面已达到大量投资、原料机械由中心供应、劳工系统分配及资本家控制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1407年一件羊毛外衣的生产要经过30道工序,每一工序都由精于该步骤的工人操作。
为了销售产品,佛罗伦萨鼓励商人与地中海所有港口城市,及远达布鲁日的大西洋海岸保持贸易关系。意大利、巴利阿里(Baleares)、佛兰德斯、埃及、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波斯、印度、中国等国家(或地区)都设有领事,以保护并促进佛罗伦萨贸易。比萨被征服作为佛罗伦萨货物出海的必要通路,热那亚商船则受雇载运货品。和佛罗伦萨厂商竞争的外国产品,在商人和财政家所组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下,一一被赶出佛罗伦萨市场。
为了供应工商及其他行业的经费,佛罗伦萨的80个银行家族——主要有巴蒂、佩鲁兹、斯特罗齐、比蒂(Pitti)和美第奇——将他们储户的资金投资在各业之中。他们兑现支票波利兹(polizze),发行信用券(lettere di pagamenti),交换商品和账目,供应政府谈和或打仗的基金。部分佛罗伦萨商行曾借出136.5万弗罗林给英王爱德华三世,但被他的赖账拖垮(1345年)。虽然遭此灾祸,佛罗伦萨仍是13到15世纪欧洲的财政中心,欧洲货币的交换率就是在该地确立的。远在1300年即有一种保险制度存在,以保护航程中的意大利货船——这种预防政策直到1543年才被英国沿用。1382年佛罗伦萨账本已有复记法(double-entry)出现,这种账法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也许已有百年的历史。1345年佛罗伦萨政府发行可转嫁的换金券,利息很低,利率5%,这证明政府在商业繁荣方面的信用和廉正。1400年,政府的岁收超过伊丽莎白全盛时期的英国。
欧洲的银行家、商人、制造商、专业人员、技术工人都有同业公会的组织。在佛罗伦萨有7种行业属于大公会(greater guilds):衣物制造商、羊毛制造商、丝织品制造商、皮毛商人、金融家、医生和药剂师及商人、法官、公证人合组的公会。佛罗伦萨其余24个公会属于小行业(minor trades):衣商、袜商、屠夫、面包师、葡萄酒商、采石工、马鞍商、甲胄商、铁匠、锁匠、木匠、客栈主人、泥水匠、切石匠及油商、猪肉商和绳匠合组的杂色组织。选民必须是某一公会的会员,因此,1282年在中产阶级革命中被褫夺公民权的贵族也加入公会,以重新取得选举权。22个公会之下还有72个没有选举权的组织;以下还有数以千计按日计酬的工人,无权组织起来,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再下一层——也可以说是上一层,因为他们受到主人的照顾——是奴隶。大公会的会员在政治上形成“肥民”(popolo grasso),其余人口构成“小民”(popolo minuto)。佛罗伦萨的政治史像现代国家一样,先是商业阶级战胜了古老的地主贵族(1293年),然后是工人阶级起而争取政治权利。
1345年,西图·布兰第尼(Cinto Brandini)和其余9人因为组织羊毛业的贫苦工人而被处死,大批外国工人输入佛罗伦萨,以瓦解这些组织。1368年,“小民”企图革命,旋被敉平。10年后,一群羊毛梳理工叛变,为工人阶级带来短暂、混乱的控制权。那些羊毛梳理工在一位赤足工人米歇尔·兰多(Michele di Lando)领导下,拥入维奇奥宫(Palazzo Vecchio),解散领袖团,建立劳工极权政体(1378年)。他们废止“禁结社会”,使低层组织有了权利,准许工薪阶层延期还债12年,降低利率以减轻负债人的重担。大商人关闭店铺,说服地主断绝都市粮食的供应,以为报复。受挫的革命党分裂成两派——由技术工人组成的劳工贵族派,含有共产思想的左翼。最后保守派从乡下带来强壮的男人,对其加以武装,推翻了分裂的政府,恢复了商业阶级的权力(1382年)。
胜利的中产阶级更改组织,以巩固他们的胜利。城市领主与绅士构成的领袖团西贡诺里亚(Signoria)由8个领主或公会领袖组成,产生方式是将备选的名单放入袋中,抽签决定。他们轮流举出一位标准执法人为执行长。8位领袖中,4位来自大公会,而大公会在成年男子中其实只占极少数。人民顾问团也要求同样的比例。而所谓“人民”只包括21个公会的会员而已。群众议会(Consiglio del Comune)从公会会员中选出,职权有限,只能于会议中在领袖们表决提议之前表示肯定或否定。领袖们偶尔也在维奇奥宫塔上鸣钟示众,召集所有选民到西贡诺里亚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开会。这种大会通常选出一个改革会,在一定期间内赋予极高的权力,以后再行休会。
19世纪史学家都相信美第奇以前的佛罗伦萨是某种程度的民主政体,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实际上在那个财阀的天堂中,民主观念十分陌生。附属城市虽然有不少人才,并以他们的祖产为荣,在统治佛罗伦萨的领袖团中却没有席位。佛罗伦萨只有3200名男子可以参加选举,两个议会中,商业阶级的代表占着绝大多数。上层阶级相信文盲大众无法在国内危机和国外事务中作稳妥而安全的判断。佛罗伦萨人热爱自由,但是对于穷人而言,那是在佛罗伦萨主人命令下的自由;对于富人而言,那是他们统治城市和属地而不受帝国、教皇或封建势力阻碍的自由。
这个组织明显的缺点是任期短,组织本身经常改变。它的坏处是党争、阴谋、暴力、混乱、无能,共和国无法设计和执行长远的政策;相反,那正是威尼斯赖以稳定和强大的因素。相对的好处是冲突和辩论的选举气氛,使脉搏加快,使感官、心灵、机智敏锐,挑起想象力,使佛罗伦萨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成为世界上的文艺领袖。
“国家之父”科西莫
佛罗伦萨政治是富有家族与党派——里奇(Ricci)、阿必齐(Albizzi)、美第奇、里多非(Ridolfi)、帕兹(Pazzi)、比蒂、斯特罗奇、卢西莱(Rucellai)、瓦萨里(Valori)、卡波尼(Capponi)、索德里尼(Soderini)等——之间为控制政府而起冲突的政治。1381年至1434年,除了略有中断以外,阿必齐一直持有国家的主权,而且勇敢地保护富人,对抗穷人。
美第奇家族可以溯源到1201年,当时奇里西莫·美第奇(Chiarissimo de' Medici)是群众议会的会员。 科西莫的高祖父阿维拉多·美第奇(Averardo de' Medici)以大胆的商业和明智的掌理建立了家族的财富,在1314年被选为标准执法人。阿维拉多的侄孙萨尔韦斯特·美第奇(Salvestro de' Medici)是1378年的标准执法人,因为赞助贫民反叛而使美第奇家族大受欢迎。萨尔韦斯特的侄孙乔万尼·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是1421年的标准执法人,更因支持0.5%的收入年税(1427年)——虽然自己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受人民钟爱,原来税率本是人头基金的7%。享受过穷人人头税的富人现在发誓要对美第奇家族进行报复。
科西莫的高祖父阿维拉多·美第奇(Averardo de' Medici)以大胆的商业和明智的掌理建立了家族的财富,在1314年被选为标准执法人。阿维拉多的侄孙萨尔韦斯特·美第奇(Salvestro de' Medici)是1378年的标准执法人,因为赞助贫民反叛而使美第奇家族大受欢迎。萨尔韦斯特的侄孙乔万尼·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是1421年的标准执法人,更因支持0.5%的收入年税(1427年)——虽然自己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受人民钟爱,原来税率本是人头基金的7%。享受过穷人人头税的富人现在发誓要对美第奇家族进行报复。
乔万尼死于1428年,传给他的儿子科西莫很好的声誉及托斯卡纳区最大的财富——179221弗罗林。其时,科西莫年已经39岁,完全适合接掌商行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不仅有银行,还有广大农场的经营,丝、毛织品的制造,及远达俄国、西班牙、苏格兰、叙利亚、阿拉伯和基督教世界的各种贸易,科西莫一方面在佛罗伦萨建立教堂,一方面和土耳其苏丹贸易,交换昂贵礼物,他并不认为这是罪恶。这个商行专门从东方输入香料、杏仁、糖等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再和其他物品一起卖到20余个欧洲港口。
科西莫以平静的技巧掌理全部业务,还有余力从事政治。他是十人战争议会的一员,领导佛罗伦萨战胜卢卡,而且以银行家身份大量贷款给政府,支援战争。他受欢迎的程度激起了其他家庭的妒忌。1433年,里纳尔多·阿必齐(Rinaldo degli Albizzi)攻击他企图推翻共和,自任独裁者,劝服当时的标准执法人伯纳多·瓜达格尼(Bernardo Guadagni)下令逮捕科西莫。科西莫投降,被囚于维奇奥宫。里纳尔多带着他的武装顾问们控制了领袖团方型集会场的议会,处死的命令几乎就要下达。但是科西莫拿出1000杜卡特贿金给伯纳多,伯纳多突然变得十分慈悲,宣布将科西莫、他的儿子们和主要支持者放逐10年。科西莫在威尼斯住了10年,他的谦和与财富为他赢得不少朋友。不久威尼斯政府运用其影响力使科西莫获召返国。1434年选出的领袖团也偏向他,于是取消放逐的命令。科西莫凯旋回国,里纳尔多带着儿子们匆匆逃走。
议会任命一个改革会,并给它极高的权力。科西莫服务了短期的三任之后,毅然放弃所有的政治职位。他说:“被选任官职,对身体和灵魂都有害处。”他的敌人既已离开城市,他的朋友便轻易控制了政府。他并未干扰共和体制,只运用口才和金钱,使得他的党徒留任官职,直到他死为止。他对各大家族的贷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支持,送给教会的礼物使他得到热心的帮助,前所未有的慷慨公共福利使市民甘愿受他统治。佛罗伦萨人看出,共和政体并未保护他们免受财阀的欺凌——西姆皮的失败已在大众的记忆中烙下了一次教训。如果大家必须在偏向富人的阿必齐家族和偏向中等阶级与穷人的美第奇家族之间作出选择,实在没有犹疑的必要。一个久受财阀压迫、疲于党争的民族欢迎独裁,这可以从1434年的佛罗伦萨、1389年的佩鲁贾、1401年的博洛尼亚、1477年的锡耶纳、1347年和1422年的罗马得到明证。史学家吉尔瓦尼·维拉里说:“美第奇家族在自由的名义与民众的支持下,以达到其霸权。”
科西莫以精明的中庸之道运用权力,偶尔也用武力。当他的朋友怀疑巴达西奥(Baldaccio d'Anghiari)阴谋终止科西莫的权势,便将他从高窗推下,结束了他的性命。当时科西莫也没有表示异议。他的妙语之一是“国家并不能用念珠来治理”。他以浮动的本金征款代替固定的所得税。有人指责这项调整是存心庇护朋友,打击仇人。在科西莫统治期的前20年,这项征款共计487.5万弗罗林,拒绝付款的人即时被捕下狱。很多贵族离开城市,重过中世纪贵族的乡村生活。科西莫镇定地接受他们的离去,宣称几米红布就可以造就新的贵族。
人民微笑赞许,因为他们知道这笔征款将用于佛罗伦萨的行政与装饰,科西莫自己也献出40万弗罗林从事公共事务和私人慈善,相当于他留给继承人数目的两倍。他努力不懈地工作到75岁,精心安排自己的财产和国家的事务。英王爱德华四世向他大量借款,科西莫不计以往爱德华三世的背信,慨然应允,英王便以钱币和政治的支持报答他。博洛尼亚主教托马索·帕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基金耗竭向他求助,科西莫慨然供应。托马索日后即位为教皇尼古拉五世,科西莫便得到了所有教会财产的管理权。为了避免多种活动纠缠不清,他起得很早,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家居时便修剪树木,照顾藤草。他衣着简单,饮食节制,而且(和女奴生下一个私生子之后)过着安静、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应邀到他家做客的人意外地发现,他朴实的私人餐食和招待外国使节以示礼义、和平的盛宴,真有天壤之别。他极富人情味,温和、体谅,沉默寡言,却以机智闻名。他对穷人很慷慨,常替贫苦的朋友缴税,常匿名行善。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蓬托尔莫(Pontormo)、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曾为我们描下他的形象:中等身材、橄榄脸色、渐稀的灰发、尖长的鼻子及严肃慈和的表情,显示出精明的智慧与平静的力量。
他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和平组织。他在一连串毁灭性的冲突中得到权力,深感进行的或酝酿中的战争都会阻碍贸易的进行。米兰的威斯孔蒂政权因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孔蒂的死亡而崩溃。威尼斯扬言要吞并这个公国,并完全控制北意大利直达佛罗伦萨门口。科西莫送钱给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巩固了他在米兰的地位,阻止了威尼斯的入侵。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组织联盟对抗佛罗伦萨,科西莫收回两地人民的贷款,迫使政府谈和。后来米兰和佛罗伦萨联合对抗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双方势力太平衡了,没有一方敢轻启战端。这种平衡政策由科西莫首创,洛伦佐(Lorenzo de Medici)继续奉行,使1450年至1492年的意大利享有和平与秩序,使城市富足,使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得到财政上的支持。
科西莫对文学、学术、哲学、艺术的关心不下于对财富和权力的关注,这是意大利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他是受过良好教育、有高雅品位的人;他精通拉丁文,略通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他志趣宽广,能够同时欣赏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虔诚和绘画,弗拉·菲利皮诺·利比(Fra Filippo Lippi)动人的粗鄙,吉贝尔蒂(Ghiberti)浮雕的古典风格,多纳泰洛(Donatello)雕刻的大胆创意,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Filippo Brunellesco)的宏伟教堂,米开罗佐(Michelozzo)建筑的节制力量,盖米斯都·布雷托(Gemistus Pletho)的异教柏拉图主义,彼科和马斯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神秘柏拉图主义,里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精练,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博学的庸俗,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de'Niccoli)的卖弄知识。这些人都领受过他的慷慨。他将阿基洛普洛斯(Joannes Argyropoulos)带到佛罗伦萨教导年轻人古希腊语言和文学,他自己向菲奇诺学习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达12年之久。他花费大部分财产收集古典文稿,所以他船上最昂贵的货品往往是希腊或亚历山大城运来的书稿。尼科利因为买古典书籍而破产,科西莫便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了一个无限制的户头,一直到尼科利死为止。他雇了45个抄写员,在热心的书商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领导下,誊写那些无法买到的书稿。这些“珍贵的小东西”都放在圣马可修道院、费舍尔(Fiesole)寺院或他自己图书馆的房间中。尼科利去世的时候(1437年),留下800本书稿,价值6000弗罗林,还有不少债务,指定16个受托人决定藏书的处理方式,科西莫自愿代偿债务,要求支配藏书。协议达成,科西莫将这些藏书分存圣马可图书馆和他自己的图书馆中。这些书都免费开放给教师和学生使用。佛罗伦萨史学家瓦奇(Varchi)以爱国者的夸张语气说道:
希腊文学没有完全被遗忘,没有造成人类的一大损失,拉丁文学能复苏是人们的一大福利——整个意大利,而且是整个的世界都要完全感谢美第奇家族的高度智慧和友善。
当然再生的伟大工作是由12世纪和13世纪的翻译家、阿拉伯注译家和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开始的。由科西莫之前的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莱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继续;又有与他无关的尼科利、波焦、弗朗西斯科·斐勒佛(Francesco Filelfo)、那不勒斯仁主阿方索和百余位科西莫同代人士接棒,甚至被他放逐的对手帕拉·斯特罗奇(Palla Strozzi),也有功劳。但是,我们若不只以“国家之父科西莫”来判断,也注意他的后代——“尊贵的”的洛伦佐、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赞助学问和艺术方面,美第奇家族的确是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族。
人文主义者
美第奇时代,人文主义者占据了意大利的心灵,使它从宗教转向哲学,从天堂转向地上,也向讶异的一代泄露了异教的思想和艺术的宝藏。这些为学术疯狂的人士,早至阿廖斯托开始就已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名称,因为他们称呼古典文化的研究为“人文学科”——不是更富人情味,而是更人性化的学问。现在人类研究的适当题材是“人”,是他潜在的力量和身体的美,是他感官和感情的欢乐、痛苦,是他理性的脆弱尊严,是丰富、完美地显露这些题材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这就是人文主义。
现存的大部分拉丁古籍和不少希腊杰作都已为中古学者所知悉,13世纪更有人熟知了大部分的异教哲学家。但是那个世纪几乎完全忽略了希腊诗,很多现在受重视的宝藏当时在寺院或教堂的图书馆中无人理会。彼特拉克和他的继承人就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中发现了“遗失”的古典作品,他称这些作品为“被野蛮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薄伽丘参观蒙特卡西诺,诧异地发现不少珍本在尘土中面临腐朽,有些被删改成祷文或护符。波焦趁着参加康士坦斯会议之便,参观圣高尔(St. Gall)的瑞士寺院,发现昆体良的《学校论》(Institutiones)躺在污秽的地窖中。当他重拾这些书卷的时候,不免觉得这位古大师正伸手求援,希望脱离“野蛮人”的魔掌。因为有文化良知的意大利人就像古希腊和罗马人一般,正是用这个名字称呼阿尔卑斯山彼侧的强大征服者。其中只有波焦由严冬的寒雪中铲除障碍,从坟堆中救出卢克莱修、克伦姆莱(Columella)、弗仑蒂努斯(Frontinus)、维特鲁维亚、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德尔图良、普劳图斯(Plautus)、圣·彼得罗纽斯(San Petronius)、马西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等人的作品和西塞罗的几篇主要演讲。萨卢塔蒂在韦尔切利掘出西塞罗的信件《论家庭》(Ad Familiares)(1389年);兰德安尼(Gherardo Landriani)在洛迪城的古籍中发现西塞罗谈修辞学的论文(1422年);特拉弗沙利(Traversari)在帕多瓦拯救柯尼里·那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免于湮灭(1434年);塔西佗的作品《阿格里科拉传》(Agricola)、《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和《历史》(Dialogi),在德国被发现(1455年);塔西佗的另一作品《编年史》(Annales)前六册以及小普林尼的信件全稿都在科维(Corvey)寺院被发现(1508年),成为利奥十世的重要财产。
土耳其人占据君士坦丁堡的前半世纪中,12位人文主义者在希腊读书或旅行;其中乔万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带了238本书稿回意大利,包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弗朗西斯科·斐勒佛从君士坦丁堡(1427年)救出希罗多德、修昔底斯、波里比阿(Polybius)、狄摩西尼(Demosthenes)、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和亚里士多德的教本,及7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这些文学探险家带着他们的发现回意大利的时候,简直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受欢迎,王子和教士们纷纷解囊,以分享这些战利品。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很多拜占庭学者曾经提过的,据说是藏在该城图书馆的珍贵名作都因而陷落,但是也有数以千计的书册被抢救出来,大部分流到意大利。目前意大利仍拥有最好的希腊古典书稿。从彼特拉克到塔索(Bernardo Tasso)的3个世纪中,很多人热衷于收集稿本。尼科利在这种追寻中所花的钱远超过他的所有财产;安德罗洛随时准备牺牲他的家庭、妻子和生命以增加藏书;波焦只有花钱在书本上才不心疼。
编辑革命也随之发生。复得的书稿在学术战役中被研究、比较、收集、解释,而参加这次战役的人士从那不勒斯的洛伦佐·瓦拉到伦敦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无所不包。由于这些工作需要希腊文的知识,意大利——然后是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处召请希腊文教师。奥里斯帕和斐勒佛曾亲自到希腊学习。当克里索罗拉(Manuel Chrysoloras)以拜占庭使节身份赴意(1397年)以后,佛罗伦萨大学说服他担任教职,教授希腊语言和文学。波焦、帕拉·斯特罗奇、卡洛·马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和詹诺佐·曼尼提(Giannozzo Manetti)都是他的学生。莱纳尔多·布鲁尼本来学习法律,现在也弃法从文,在克里索罗拉的魔力之下学习希腊文。“我非常热心地向他学习,”他说,“所以连晚上做梦也充满白天向他学来的知识。”现在谁能想象希腊文法曾一度像奇遇记和浪漫诗一般迷人呢?
1439年,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佛罗伦萨会议上相遇,他们在语言上所交换的课程远比他们的神学谈判更有成果。当时盖米斯都·布雷托的著名演讲结束了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哲学上的领导地位,却将柏拉图提升到近乎神明的地位。会议解散之后,以尼西亚主教身份前来的贝萨里翁(Joannes Bessarion)继续留在意大利,用部分时间教授希腊文。其他城市也感染了这种狂热:贝萨里翁将它带到罗马;西多罗斯·加扎(Theodorus Gaza)在曼图亚、费拉拉和罗马等地教授希腊文;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在佩鲁贾、帕多瓦、佛罗伦萨和米兰(1492—1511年)等地;阿基洛普洛斯在帕多瓦、佛罗伦萨和罗马。这些人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来到意大利,所以该城失陷与希腊文从拜占庭移向意大利没有太大的关系。但1356年以后,土耳其逐渐包围君士坦丁堡,与希腊学者的西行不无关系。康·拉斯卡里斯(Constantine Lascaris)是在这个东方都城崩溃后逃出的,他在米兰、那不勒斯和墨西拿(Messina)教授希腊文。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所印行的第一部希腊文作品就是他的希腊文法。
有了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弟子在意大利热心活动,不久希腊文学和哲学名作就已被彻底、精确、完全地译成拉丁文,成果远甚于12世纪和13世纪。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翻译了斯特拉博和普卢塔克的部分作品;特拉弗沙利译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著作;瓦拉译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的作品和《伊利亚特》史诗;尼可罗·佩罗蒂(Niccolo Perotti)译了波里比阿的作品;菲奇诺译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Plotinus)的著作。柏拉图尤其使人文主义者大为惊喜。他们景仰他文体的流畅优美,认为《对话录》中生动而现代化的戏剧,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戏剧名家更胜一筹。他们羡慕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可以自由讨论最重大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他们在柏拉图身上——以往被普罗提诺所掩盖——发现一种神秘哲学,使他们重获了他们不再信仰却始终热爱的基督教。佛罗伦萨的科西莫被盖米斯都·布雷托的口才和他的门徒的热心感动,建立了(1445年)一个柏拉图学园,专门研究柏拉图,并且大量拨款给菲奇诺,使其以半生时光从事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和说明。经院哲学统治了西方400年,现在终于失去了哲学上的主要地位;对话和散文取代经院辩论成为哲学说明的主要方式,柏拉图的怡人精神就像兴奋酵母一般,深入新兴的欧洲思想体系中。
然而,当意大利一天天恢复古典传统时,人文主义者对希腊的崇拜却被他们对古罗马文艺的自负所超越。他们使拉丁文苏醒成活文学的媒介;他们将姓名拉丁化;将基督教礼拜和日常生活的名词罗马化;上帝变成Juppiter,天佑变成fatum,圣人变成divi,修女变成vestales,主教变成pontifex maximus。他们模仿西塞罗的散文文体,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体;而斐勒佛、瓦拉和波利希安等人的文章文雅得近乎古典。所以,文艺复兴逐渐从希腊文转回拉丁文,从雅典转回罗马。15世纪逐渐远去,西塞罗、奥维德和塞涅卡的时代似乎再生了。风格重于实质,形式重于内容,黄金时代的演说又在王子和腐儒的大厅中响起。若是人文主义者用意大利文那该是明智之举,但他们轻视戏剧化和经典化的演说,认为那是堕落的拉丁文,也痛心但丁选用方言创作他的伟大作品。结果,人文主义者失却了文学活泼的来源,人民也将这些人的作品留给贵族欣赏,宁愿阅读弗兰科·萨凯蒂(Franco Sacchetti)和玛泰奥·班狄洛(Matteo Bandello)的愉快故事,或者由法文翻译、改写的爱情战争传奇。不过,这种对死语言和“不朽”文学的迷恋帮助意大利学者恢复了建筑、雕刻和高尚的音乐,立下了情趣和语调的规范,使方言达到文学标准,为艺术定下目标和准则。史学方面,人文主义者结束了中世纪编年史——杂乱无章、不加评注——的传统,详审并协调资料,将事实依照简明的秩序编列,混合传记与历史,将过去生动化并使之富于人情味,洞察事件的前因、过程和结果,研究历史法则和教训,使他们的叙述富有哲学意义。
人文运动遍及意大利,但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担任教皇之前,它的领导人几乎全是佛罗伦萨的公民或毕业生。1375年成为领袖团执行秘书的萨卢塔蒂可以说是从彼特拉克、薄伽丘到科西莫之间的桥梁,他熟知这三个人,也热爱他们。他起草的公文是古典拉丁文的典范,是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官吏争相模仿的样本。米兰的吉安加里亚佐·威斯孔蒂曾说,萨卢塔蒂的杰出文体对他的伤害远甚于雇佣兵军队。尼科利的拉丁文体与他的书稿收集一样有名;布鲁尼称他为“拉丁语的监察官”,他也像其他作家一样,在作品出版前送请尼科利修改。尼科利家中充满古典名著、雕像、碑铭、花瓶、钱币和珍宝。他不愿结婚,唯恐分散他对书本的注意。他只有一个情妇,是从他兄弟身边抢来的。他把图书馆开放给所有喜欢研究的人使用,鼓励佛罗伦萨青年放弃奢华的生活,从事文学的研究。他看见一个富家青年终日闲荡,便问他:“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青年坦白答道:“享乐。”“但是你青春逝去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这个青年领会其意,终于拜师门下,接受尼科利的教导。
莱纳尔多·布鲁尼曾任四位教皇的秘书,当时(1427—1444年)正是佛罗伦萨领袖团的秘书。他将几段柏拉图的《对话录》译成拉丁文,文笔绝佳,使柏拉图的华丽文体第一次呈现在意大利人面前;他写了一部拉丁文的《佛罗伦萨史》,共和国因而免除了他和他子女的税金;他的演说才能堪比伯里克利。他去世的时候,领袖团的领袖们颁令用古礼公开祭他,将他安葬于克罗齐教堂,将《佛罗伦萨史》安放在他胸口。伯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为他设计了高贵而华丽的坟墓。
卡洛·马苏皮尼像布鲁尼一样生于阿雷佐,又继承他担任领袖团的秘书,他脑中记着半数的希腊、罗马名作,在他就任佛罗伦萨大学文学教授职位的演说中,几乎没有一个古作家不曾被他引述过。他太崇拜异教的古典文学,几乎因此遗弃基督教,但他担任过罗马教皇的秘书。有人说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但他也被葬于圣十字教堂,詹诺佐·曼尼提为其葬礼发表演讲,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Desiderio da Settignano)为他设计华丽的坟墓。为这个无神论者做祭文的曼尼提是一个既虔诚又博学的人。9年之间,他很少离开房子和花园,整天研究古典文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也学习希伯来文。他曾被派往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热那亚担任大使,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以他的修养、大度和廉正为政府赢得珍贵的友谊。
除了萨卢塔蒂以外,这些人士都是科西莫的城市住宅或乡村别墅的常客,在他当权期间领导着学术运动。科西莫的另一位朋友在招待学术界方面几乎与他不分轩轾。同志会教派(Camaldulite order)的领导人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住在佛罗伦萨附近圣玛利亚寺院的一间小室中。他精通希腊文,为自己热爱古典作品而深感不安。他在作品中尽量避免引用古典名作,却在拉丁文体中自然显出了他所受的影响,文中口语的纯净简直惊动了所有著名的罗马教皇。科西莫不仅知道如何协调财政,也知道如何协调古典名作和基督教文明,很喜欢拜访特拉韦萨里。尼科利、布鲁尼及其他许多学者使他的小室成为文学界的聚会所。
最活跃、最烦人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是波焦。他生于阿雷佐贫民家庭(1380年),在佛罗伦萨跟随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以抄写书稿维持生活,与萨卢塔蒂交友,而且在24岁被任为罗马宗教法庭的秘书。后来的50年中他一直为罗马教廷服务,但不曾担任一官半职,只穿着教士服装。教廷尊崇他的精力和学问,派遣他担任十几次任务。他屡次逃开本职,往寻古典书稿;他的教会秘书身份使他轻易进入圣高尔、朗格里斯(Langres)、温加腾(Weingarten)和雷查奴(Reichenau)等地守卫最严或最不受注意的图书馆;他的战利品十分丰富,被布鲁尼及其他人文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收获。回到罗马以后,他为马丁五世写下多篇生动的教会信条辩护文,然后,在私人集会中与其他教廷雇员共同讥笑天主教的规条。他以不雅却轻快的拉丁文写成对话和信件,讽刺教职人员的罪恶,自己却照犯不误。红衣主教圣安杰洛责备他有孩子,认为穿教士服装的人不宜如此,又责备他有情妇,认为连俗人都不可这样过分,波焦以一贯的无礼态度答道:“我有孩子,这是适合俗人的;我有情妇,那正是教职人员的古老风格。”他在55岁的时候遗弃了为他生过14个孩子的情妇,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孩。同时他还收集古钱币、碑铭和雕像,以学者的精简文体描述古罗马遗下的纪念碑,几乎建立了现代考古学。他伴随教皇尤金四世(Eugenius Ⅳ)参加佛罗伦萨会议,与斐勒佛争吵,用最粗鄙、下流、热烈的措辞对骂,控告他盗窃、支持无神论和淫乱。在罗马他又愉快地为人文主义者尼古拉五世教皇工作。他17岁就写出著名的《幽默书》(Liber Facetiarum),集故事、讽刺和脏话之大成。洛伦佐·瓦拉参加秘书工作时,波焦在新的《讽骂集》(Invectivae)中攻击他,控他盗窃、伪造文书、叛国、支持异端邪说、酗酒和不道德。瓦拉提出反击,讥讽波焦的文法,引述他文书和口语的错误,说他是老朽的傻瓜。除了受害人本身,没有人重视这些文学上的互殴。两方骂文同是拉丁文章的佳篇,波焦确实在其中一篇中显示出古典拉丁文可以深切表达最摩登的思想和最隐私的事情的能力。他非常熟悉广博粗鄙的艺术,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说“全世界都怕他”。他的笔,就像后来的阿里汀(Aretine)一样,成为勒索的工具。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王未能承认他将色诺芬的《语义学大全》(Cyropaedia)译为拉丁文的能力,这位愤怒的人文主义者便暗示说,一支好笔可以刺杀任何国王。阿方索赶忙送上500杜卡特以封住他的口舌。享受了70年的本能和冲动之后,波焦写了一篇论文《悲惨的人类处境》(“De Miseriis Humanae Conditionis”),认定生命苦多于乐,并且像梭伦一般推断说:“最幸运的是没有出生的人。”他72岁返回佛罗伦萨,被任命为领袖团的秘书,最后被选成领袖团的一员。他写了一本古体的佛罗伦萨历史,以示感激,书中包含政治、战争和虚构的谈话。最后终于在79岁逝世(1450年),使其他人文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他也葬于圣十字教堂,多纳泰洛为他塑的雕像立在大教堂正面,在1560年的某次变迁中被误认为十二使徒之一而改立在教堂里面。
基督教在神学和伦理方面显然都已失去约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力量。也有几位,如特拉韦萨里、布鲁尼、佛罗伦萨的詹诺佐·曼尼提、曼图亚城的维托里诺·德费尔特(Vittorino da Feltre)、费拉拉城的瓜里诺、罗马的弗拉维·比昂多(Flavio Biondo)等人依然忠于信仰。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历时千年,在文学、哲学、艺术方面达到高峰,和犹太教、基督教完全无关的希腊文化是他们信仰上的致命打击,他们不再相信保罗神学及“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的教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成为他们心中未受封的圣人,希腊哲学家的王朝似乎优于希腊和拉丁神父,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散文使红衣主教都要为《新约》的希腊文和圣哲罗姆的拉丁译文惭愧。罗马帝国的光荣似乎比基督徒避入寺院小室中高贵得多。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或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自由思想和行为使许多人文主义者羡慕不已,使他们心中的卑屈、来世和节欲法典大大动摇。他们疑惑自己为什么要使身体、心智和灵魂臣属于教士的规则,而教士本身现在却已转向尘世享乐。对这些人文主义者而言,君士坦丁大帝和但丁之间的10个世纪已成为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一种但丁式的迷失。圣母和圣徒的可爱传说已在他们记忆中褪色,让位给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贺拉斯性别不明的抒情诗。现在大教堂似乎已显得很野蛮,其中的巨大雕像对于见过、触过阿波罗像的人已失去一切吸引力。
所以,人文主义者已完全把基督教当作适合大众想象和道德的神话,而不是解放后的心灵所应认真接受的题材。他们在公开的宣告中支持它,承认已存的正统,奋力使基督教教条和希腊哲学合而为一。这项努力终于失败。他们毫无疑惧地接受理性最高的裁判,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如《新约》一样尊崇。他们就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诡辩学派一般,直接或间接、自愿或不自愿地破坏他们听众的宗教信心。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真正的信条,很多人以感官而非禁欲的观点来接受异教的伦理。他们承认的唯一不朽是伟大事迹的记录。他们将以自己的笔,而不是上帝,来达成不朽,使人注定永远的光荣或耻辱。科西莫以后的一代会同意和艺术家分享这种神奇的力量,而艺术家正是雕刻、绘画赞助者肖像,建筑高贵大厦以纪念捐助者的人。赞助者希望达成这种俗世不朽的心理正是文艺复兴的巨大推力。
人文主义者的影响是整整一个世纪中西欧知识生活的主要成分。他们教给作家更锐利的结构感和形式感,也教给他们修辞的技巧、语言的矫饰、神话的咒语、古句的盲目崇拜及不顾含义只求得语言正确、文体优美的精神。他们迷恋拉丁文,使意大利诗赋和散文的发展延迟了一个世纪之久(1400—1500年)。他们从神学中解放科学,却崇拜过去,重视博学甚于客观的观察和创见的思想,使科学又蒙阻碍。奇怪的是,他们在大学中的影响最小。在意大利的文学都太古老,在博洛尼亚、帕多瓦、比萨、皮亚琴察、帕维亚、那不勒斯、锡耶纳、阿雷佐、卢卡等地,法律、医学、神学和文艺——包括语言、文学、修辞、哲学——的教授都局限在中古的传统中,不容许重新强调古典文化,他们至多让人文主义者教教修辞学而已。“文学复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和罗马赞助的专门学校。人文主义者在那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口述他们所要讨论的古典教材,再一步步以拉丁文评论教材的文法、修辞、地理、自传和文学等;他们的学生记下口述的教材,也在书页空白的地方记下大部分的评论;就这样,古典作品和评论的抄本被复制起来,传遍世界。科西莫的时代因此成为学术而不是创造性文学的时代。文法、辞典编纂法、考古学、修辞学和古典名作的批评校订是当时文学上的光荣。现代学识的形式、组织和实质都已建立,希腊罗马遗产进入现代心灵的桥梁已建立起来。
自从诡辩派的时代以来,学者从未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有过如此崇高的地位。人文主义者成为元老院、领袖团、公爵、教皇的秘书和顾问,以古典颂词报答他们的恩宠,以有毒的警句回报他们的冷落。他们刺激了那些吸收民族文化遗产以得到智慧和价值的个人,也改变了绅士的理想。正当法国、德国、西班牙企图征服意大利时,他们凭借威望和口才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彼侧的欧洲。接二连三的国家吸收了新文化,从中古转向现代文明。发现美洲的那一世纪正是希腊、罗马文明被重新发现的世纪,而文学、哲学的转变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比对地球的迂迴探险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因为使人免于教条束缚,使他爱生命甚于来生,使欧洲心灵自由的,是人文主义,而不是航海家。
受人文主义影响的艺术得以延续,因为它是诉诸知识而不是诉诸感官。艺术的主要赞助者仍是教堂,艺术的主要目的仍是把基督教故事传给不识字的人民或装饰上帝的房屋。圣母和圣婴,受难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先知、使徒,圣父和圣徒仍是雕刻、绘画,甚至次要艺术的必要题材。然而,人文主义者渐渐教给意大利人更世俗的美感;对健康人体——男性或女性裸体——的坦白崇拜传播在受教育的阶级之间;文艺复兴文学对生命的再肯定,对中世纪来世思想的反抗已给予艺术一种秘密的现世依靠;而洛伦佐时代或后世的画家们,更以意大利爱神维纳斯为圣母的蓝本,以意大利太阳神阿波罗为圣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的蓝本,将异教动机带入基督教艺术中。16世纪——当世俗的王子和教士们争相支持艺术家的时候——维纳斯、迈那斯公主阿里亚德妮(Ariadne)、被阿波罗迷恋的少女达芙妮(Daphne)、月神狄安娜、缪斯和美乐女神(Graces)向圣母的独尊地位挑战,然而谦和的圣母玛利亚仍能继续维持她完美的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结束为止。
建筑:布鲁尼里斯哥的时代
“发明这种恶劣的哥特建筑的人该死!”安东尼奥·费拉里(Antonio Filarete)在1450年说,“只有野蛮民族才会把它带到意大利。”那些玻璃墙简直不适合意大利阳光;那些飞扬的拱壁——虽然曾在巴黎圣母院被锤炼成美丽的架子,就像喷泉在流动中僵住了一般——对南方而言似乎是建筑者留下的丑恶绞台,结构上缺乏自足的稳定感。尖拱门、高圆顶的哥特形式显示人们渴望将精神从劳苦的土地转向慰藉的天空。但是富裕且追求舒适的人民现在已希望美化生活,不想逃避或诽谤它。地上就是天堂,他们自己就是神仙。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基本上并不是对哥特建筑的反抗,因为哥特形式从未征服过意大利。每一种形式和影响都表现出14世纪和15世纪经验的片段:伦巴底—罗马式的重廊柱和圆拱门,希腊式地基的交叉,拜占庭的三角穹隆和圆顶,模仿伊斯兰教尖塔的端庄钟楼,令人想起伊斯兰教或古典回廊的托斯卡纳细廊柱,英国和德国的加梁天花板,哥特式的拱门、圆拱和窗饰,罗马建筑正面的和谐壮丽,尤其旁设甬道的教堂圣厅,其单纯有力更具有重大影响——当人文主义者将建筑眼光转向罗马废墟的时候,这些成分在意大利完全融合起来。当时从中古浓雾中升起的罗马法庭列柱,在意大利人眼中似乎比威尼斯的拜占庭怪物、沙特尔的端庄壮丽、博韦的脆弱大胆或亚眠拱门的神秘力量美丽得多。再建旋形美观、底座安定、柱头雕花悦目、额缘冷静安稳的廊柱——这个目标,由于已埋葬的过去活文化的发现,已成为布鲁尼里斯哥、阿尔贝蒂、米开罗佐、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的梦想和热望。
“说起菲利普·布鲁尼里斯哥,”爱国的瓦萨里写道,“在建筑术堕落了几个世纪之后,他可以说是上天派来创建新形式的人。”他就像很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一样,是金匠出身。他后来成为雕刻家,曾一度和多纳泰洛成为友善的对手。他和多纳泰洛、吉贝尔蒂竞争雕刻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他一看见吉贝尔蒂的草图,便宣布它们比自己的优异,于是和多纳泰洛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罗马研究透视和设计。他对那儿的古代和中古建筑深深着迷,度量了很多大建筑物的每个部分,尤其醉心于万神殿142英尺宽的圆顶,他还想为佛罗伦萨城未完成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加上这样的圆顶。他及时回返佛罗伦萨,参加建筑师和工程师会议,商讨大教堂八角席位的加顶问题,那个席位横跨138.5英尺,工程浩大。布鲁尼里斯哥建议用圆顶,但是这么大的圆顶会影响墙壁,实非外面的拱壁和里面的梁柱所能支持,这项大压力对于与会的人似乎是很大的障碍。全世界都知道布鲁尼里斯哥放蛋的故事:他向其他艺术家挑战,看谁能把蛋直立。在其他人都失败之后,他将蛋钝的、空的一端压在桌上,终于成功。这些人争辩说,他们也可以同样做到。他答道,等他为教堂盖好圆顶以后,他们也会这样说的。他接受了这项工作。14年中(1420—1434年)他断断续续地进行这项工作,克服上千种困难,冒险将圆顶立起,高出支持的墙壁顶端133英尺。最后圆顶终于完成了,而且十分稳固。整个城市都称赞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建筑。一个世纪以后,米开朗基罗计划建筑圣彼得教堂圆顶,有人告诉他,他有机会胜过布鲁尼里斯哥,他答道:“我会建一个姐妹圆顶,比他的大,却不可能比他的美。”在四周盟国的围绕下,这个威风多彩的圆顶卓然而立。红色屋顶的佛罗伦萨全貌,就像托斯卡纳山脚的玫瑰花坛一般。
布鲁尼里斯哥的观念来自万神殿,他却依照哥特式尖拱门的线条来弯曲圆顶,使圆顶和佛罗伦萨教堂的托斯卡纳哥特形式优美地协调起来。但是在从头设计的建筑物中,他的古典革命更为明显、更为完全。1419年,他开始为科西莫的父亲建立圣洛伦佐教堂,只完成了圣器收藏室,但是他采取本堂形式、列柱、柱顶线盘,罗马式拱门作为计划中的主体。在克罗齐寺院中,他为帕兹家族建了一个漂亮的小教堂,再度令人想起万神殿的圆顶和柱廊。在同一寺院中,他也设计了直角的正门——有凸槽的柱子、镂花的柱头、雕刻的额缘和弧形窗的镶画——成为文艺复兴时代十万屋门的典型。他以古典线条开始建筑圣灵(Santo Spirito)教堂,但是在工程进行中,他逝世了(1446年)。这位建筑家的尸体静静躺在他所建的圆顶之下。佛罗伦萨人,上自科西莫,下至曾在该地工作的工人,都来哀悼天才的夭亡。“他生前是一个好基督徒,”瓦萨里说,“给世界留下美德的芬芳……从古希腊、罗马以至于今,没有人比他更难得、更杰出。”
布鲁尼里斯哥在建筑的狂热中为科西莫设计了一座宫殿,非常广大,非常华丽,这位温和的独裁者害怕别人的忌妒,竟不让它成形。相反,他召请米开罗佐为他及他的家族和办公室建立了现在仍存的美第奇宫,没有装饰的厚石墙显示出社会的紊乱、家族的宿仇、日复一日的暴力和叛乱,给佛罗伦萨政治更增浓烈的气氛。巨大的铁门开向朋友和外交官,艺术家和诗人,也通向一座设有多纳泰洛雕像作品的宫廷,通向柔美的房间,通向一个正面由贝诺佐·戈佐利设计的富丽堂皇的小教堂。美第奇家族在该地住到1538年,中间曾被放逐。当然他们也常常离开那些阴郁的墙壁,到加里奇(Careggi)和卡发吉诺(Cafaggiolo)城外或费舍尔山坡的科西莫别墅享受阳光。科西莫、洛伦佐、他们的朋友及受监护人就在那些乡村静处逃开政治,躲入诗词、哲学和艺术之中,祖孙也曾到加里奇城避开死神的约会。科西莫偶尔瞥见坟墓,便拨下相当的款项以建立费舍尔寺院,并扩建圣马可古修院。米开罗佐在该处设计了优雅的回廊、一间尼科利藏书馆和一间小室。科西莫偶尔也离开朋友,到那间小室深思、祈祷一整天。
米开罗佐是他最喜爱的建筑师,也是忠实的朋友,曾在放逐期间陪伴他,又随他回国。不久,领袖团交给米开罗佐一项困难的工作,要他支持维奇奥宫免于塌倒。他恢复阿塔努西亚(Santissima Annunziata)教堂,为它做了一个可爱的神龛,又用“施洗者”约翰的雕像加以装饰,显示出极大的雕刻才华。他为科西莫之子彼罗(Piero)在圣米尼托(San Miniato)山侧教堂建了一间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圣堂。他结合自己和多纳泰洛的技巧,在普拉托大教堂的本堂设计并刻出了迷人的“环带讲坛”。
同时,商人、贵族正在建立傲人的市政厅和宫殿。1376年,领袖团授命本茨·西翁(Benci di Cione)和西蒙·塔伦提(Simone di Francesco Talenti)二人在维奇奥宫对面建立一个柱廊,以作为政府演说的讲台。它在16世纪开始出名,被称为朗奇柱廊,由科西莫公爵一世驻扎的日耳曼枪骑兵而得名。佛罗伦萨最富丽的私人宫殿是由凡西里(Luca Fancelli)根据19年前布鲁尼里斯哥的设计为银行家卢卡·比蒂(Luca Pitti)建立的(1459年)。卢卡·比蒂几乎和科西莫同样富有,却不如他贤明谦和。他和科西莫竞求权力,也因科西莫引发出尖锐的诤言:
你向无限奋斗,我向有限。你在空中架起梯子,我架在地上……很自然,很公平地我希望我家的光荣和名誉超过你家。让我们像两只狗一般,见面时互相轻蔑、龇牙咧嘴,然后各走各的路。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
卢卡·比蒂继续谋划,科西莫死后他阴谋取代彼罗·美第奇的权力。他犯了文艺复兴时代公认的唯一罪恶——失败。他被驱逐、毁灭,他的宫殿也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中,达百年之久。
雕刻
·吉贝尔蒂
古典形式的模仿在雕刻方面比建筑更为彻底。罗马废墟的观察、研究及某些罗马杰作的偶然发现使意大利雕刻家发出好胜的狂喜。当现存于柏琪斯画廊(Borghese Gallery)的爱神像——她漠然的背部温和地转向观者——在圣西尔索(San Celso)的葡萄园中被发现时,吉贝尔蒂形容道:“没有任何语言足以描写其中的学问和艺术,或者公平地批判它的杰出形式。”他说,这类作品的完美使眼睛不敢正视,只能用手抚摸大理石的表面和线条来加以欣赏。随着这些发掘的遗迹逐渐增多,逐渐熟悉,意大利心灵渐渐习惯了艺术中的裸体。解剖学的研究在艺术家艺苑和医学大厅中一样普遍。不久艺术家便毫无恐惧,不受指责地使用裸体模特。雕刻受了这样的刺激,结束了屈居建筑的附属地位,从石头或灰泥镶画转向立体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像。
但是,在科西莫时代的佛罗伦萨,雕刻最初的、最著名的胜利却是镶画。大教堂前面的丑陋洗礼堂必须加上临时的修饰,才能挽回颜面。托里提(Iacopo Torriti)曾装饰讲坛,塔菲(Andrea Tafi)装饰圆顶,都是使用群集的嵌画;安德烈·皮萨诺曾为南方正堂铸了两面青铜的大门;1401年,佛罗伦萨领袖团又与木商工会联合,筹了一大笔款项准备为洗礼堂北面装饰一副青铜门,以说服神祇停止瘟疫。竞赛公开举行,所有艺术家都被邀提出设计。最成功的——布鲁尼里斯哥、奎尔恰(Iacopo della Quercia)、吉贝尔蒂和其他几位——接受款项,被授命铸造一个青铜样品镶板,展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情景。一年后,完成的镶板被送到34位裁判面前——包括雕刻家、画家和金匠。大家一致同意吉贝尔蒂的最佳。这个25岁的青年便开始了他第一副著名的青铜门的铸造工作。
只有仔细研究过这个北面大门的人才能了解其设计和铸造为何要花费21年的光阴。基于友谊,多纳泰洛、米开罗佐都来慷慨地帮助吉贝尔蒂,还有其他一大群助手。全佛罗伦萨人都期望并确信这是艺术史上最好的。吉贝尔蒂将这副门分成28片镶板。20片叙述基督的生活,4片描绘使徒,4片表现教会的博士们。当这些镶板被设计、批评、再设计,铸造并装在门上的时候,捐献者不仅不吝惜已经花去的2.2万弗罗林,还聘请吉贝尔蒂为洗礼堂东面做一副对应的门(1425年)。吉贝尔蒂在这次历时27年的创作过程中,有不少已成名或将成名的艺术家作为助手:布鲁尼里斯哥、安东尼奥·费拉里、鲍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安东尼奥·波莱奥罗(Antonio Pollaiuolo)和其他的人。在这段时期,他的工作室培养了十几位天才。因为第一副门表现了《新约》,所以,现在吉贝尔蒂用10片镶板呈现出《旧约》的情景,从人类的创造到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王应有尽有。在边上他又用近乎完整的镶画和极为可爱的装饰——动物和花——构成20幅画面。在此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完全融合:第一片镶板上有关亚当的创造、夏娃的诱惑和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等中古题材是以古典的布帏波纹和大胆丰满的裸体来处理,而夏娃从亚当肉体中生出的意境也可媲美爱神从海上升起的希腊镶画。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行动的背景中,风景几乎完全合乎透视学原理,描绘也很仔细,与当时最好的图画并无二致。有人抱怨这幅雕刻太注重绘画,超出古典镶画的传统。学理上的确如此,但效果很生动、很壮丽。一般公认第二次雕刻的门比第一次好:米开朗基罗认为它“好得足以装饰天堂的入口”;瓦萨里一定只想到镶画,他宣称“这幅雕刻的每一细节都很完美,无论在古人或今人之中,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杰作”。佛罗伦萨人非常满意,他们将吉贝尔蒂选为领袖团的一员,并给他很多财产以安度晚年。
·多纳泰洛
瓦萨里认为多纳泰洛也是入选试铸洗礼堂门板的艺术家之一,但是多纳泰洛当时只有16岁。他的朋友和后代给他的爱称为“贝托·巴蒂”。他只花一点时间在吉贝尔蒂画室学艺,很快就发挥了自己的天才,从吉贝尔蒂镶画的女性优雅转向立体的雄壮雕像。他改革雕刻并不采纳古典的方法和目标,而是毫不妥协地忠于自然,表现自己原有个性和形式的粗鲁力量。他是一个独立的灵魂,像他雕刻的《大卫》(David)一样强韧,《圣乔治》(St. George)一样大胆。
他的天才发展并不像吉贝尔蒂一般迅速,却达到更大的范围和高度。一旦天才成熟,他便极为多产,直到佛罗伦萨充满他的雕像作品,阿尔卑斯山彼侧也回荡着他的盛名。他22岁时为圣米凯莱教堂雕刻圣彼得像,与吉贝尔蒂分庭抗礼;27岁又为那栋大厦加上健壮、单纯而真诚的圣马可,超过了吉贝尔蒂。米开朗基罗说:“由这样一个直爽的人传播福音,想拒绝接受是不可能的。”多纳泰洛23岁受聘为教堂雕刻《大卫》,那是他所雕刻的许多《大卫》中的第一座。他对这个题材始终有兴趣。他最好的作品也许就是科西莫订制的青铜《大卫》。它雕刻于1430年,立在美第奇宫的庭院里,现在放在巴吉诺。这是立体的裸体雕像在文艺复兴史上第一次大方的展露:身躯平滑,年轻的肉体肌理结实,脸孔侧面也许太希腊了,盔甲更是希腊化过度。在这一瞬间多纳泰洛把写实主义推开一旁,充分沉湎在想象之中,几乎堪比米开朗基罗为未来的希伯来王所刻的那尊更著名的雕像。
他的“施洗者”约翰却不如此成功,那个严厉的题材与他的现世精神相去太远;巴吉诺所存的两幅约翰雕像显得荒谬,毫无生命。有一幅石制的儿童头像比这两副好得多,命名为“年轻的圣约翰”,实在没有太大的道理。在同类作品《圣乔治》中,他把基督教理想和希腊艺术的节制线条联合起来:一副稳定、自信的体型,一个成熟、强壮的身体,一个哥特式的显示出古典布拉诺第(Buonarotti)的布鲁特斯精神的椭圆头形。他为佛罗伦萨大教堂正堂造了两座有力的人像——《耶利米》(Jeremiah)和《哈巴谷》(Habbakuk)。后者光秃秃的,被多纳泰洛称为“大南瓜”。在朗奇柱廊,多纳泰洛受科西莫之托所雕刻的青铜《朱蒂丝》(Judith)仍然向《何洛芬斯》(Holofernes)舞动着他的剑:而这位喝了药酒的将军在被斩前睡得很安宁,他被设计得很好,也铸得很好;但是那位年轻的除暴者完全被布帏的波纹掩盖了光辉,她对即将来临的事了无挂虑,平静得不合时宜。
在罗马的简短旅行中(1432年),多纳泰洛为古老的圣彼得教堂设计了一个古典的大理石圣龛。也许他在罗马研究过帝国时代遗下的胸像,他最先发展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人像雕刻。他在人像方面最伟大的杰作是他为政治家乌扎诺所雕刻的陶土胸像。他用不恭维、表现真人的写实主义来娱乐自己、表现自己。多纳泰洛重新发现一项古老的真理,艺术不必永远追求美,但是要选择并表露有意义的形式。很多高贵的人不惜牺牲凿刀的真实性,有时因此而失败。一位热那亚商人不满意多纳泰洛眼中的自己,和他讨价还价。事情闹到科西莫那儿,他裁定多纳泰洛索价还嫌太低呢。商人抱怨说,这个艺术家只为这件作品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索价达到每天半个弗罗林,认为多纳泰洛不过是个艺术家,这价格未免太高了。多纳泰洛把胸像击得粉碎,说道,这种人只配在买豆子的时候讨价还价。
意大利城市比较欣赏他,而且竞求为他服务。锡耶纳、罗马和威尼斯都曾一度诱他前往,但是在帕多瓦城他铸造了他的代表作。他在圣安东尼教堂为伟大的圣方济各灵骨上的祭龛刻了一个大理石幕,上面放着构想柔和的活动镶画和青铜的十字架。在教堂前面的外廊里,他立了(1453年)近代第一座重要的骑马雕像。这无疑受了罗马奥勒留骑像的激励,但是面孔和气氛却完全是文艺复兴式的,不是理想化的哲人国王,而是可以看出当代性格的活人,无惧的、无情的、有力的——威尼斯将军加塔梅拉塔(Gattamelata)。那匹焦躁、口吐白沫的马和他的脚配起来未免嫌大了些,而那些鸽子(与瓦萨里无关)每天都在这位征服者的光头上拉屎,但他的姿态骄傲而强壮,仿佛马基雅维利所渴望的一切美点都在多纳泰洛铸像中借着融熔未硬的青铜传递下来。帕多瓦城惊奇地、荣幸地注视这位幸得不朽的英雄,给予艺术家1650金杜卡特以酬谢他六年的辛劳,并要求他在该城定居。他古怪地反对说:“帕多瓦所有人都称赞他,他的艺术在这里不会有进步;佛罗伦萨所有人都互相批评,为了艺术他必须返回佛罗伦萨。”
事实上他返回佛罗伦萨是因为科西莫需要他,他也喜爱科西莫。科西莫是一个懂得艺术的人,非常支持他的创作。他们之间相契极深,因此多纳泰洛“将科西莫最微小的意向也加以神圣化”。在多纳泰洛建议下,科西莫收集了古雕像、石棺、拱环、廊柱和柱头,放在美第奇花园中,供年轻的艺术家学习。多纳泰洛和米开罗佐共同为科西莫在洗礼堂中立下一座逃亡者约翰二十三世的坟墓。他也为科西莫最喜爱的圣洛伦佐教堂刻了两个讲坛,饰以基督受难的青铜雕刻。日后萨沃纳罗拉和其余的人就是从这两个讲坛向以后的美第奇家族射箭的。他为神龛铸了一个可爱的《圣劳伦斯》(St. Lawrence)陶像,为圣器收藏室设计了两副铜门,并为科西莫的父母设计了简单而美丽的石棺。其他工作在他看来简直像小孩子的游戏:为圣十字教堂雕了一块精美的《天使报喜》(The Annunciation);为大教堂雕了唱歌的男孩——胖嘟嘟的男孩们狂野地唱着颂歌;一幅《青年》(Young Man)胸像,是健康青年的化身(现存万国艺术博物馆);一幅《圣西西里娅》(Santa Cecilia,可能由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所雕),其美堪称为基督教的颂赞;一幅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青铜浮雕,写实详尽,十分有力;在圣十字教堂雕了另一幅十字架图,用木头刻成憔悴、孤单的身影,虽然被布鲁尼里斯哥批评为“像钉上十字架的农夫”,仍是描写此景最感人的代表作。
赞助人和艺术家一起老了,科西莫对这位雕刻家照顾得十分周到,使多纳泰洛很少想到金钱的问题。瓦萨里说,他将钱放在一个篮子里,挂在工作室的天花板上,并吩咐他的助手和朋友们依照需要取用,不必征求他的意见。当科西莫临死的时候(1464年),他要他的儿子彼罗照顾多纳泰洛。彼罗给予这位老艺术家一栋乡间的房子,但多纳泰洛不久就回到佛罗伦萨,他喜欢自己所习惯的工作室甚于乡下的阳光和昆虫。他过着简单、满足的生活,活到八十高龄。佛罗伦萨所有艺术家——几乎所有人民——都参加他的葬礼。他如愿葬于圣洛伦佐教堂的地下圣堂中,和科西莫的坟墓比邻。
他曾大大增进了雕刻艺术,偶尔也过分注重姿态或设计,缺乏吉贝尔蒂铜门的完整形式。但是,他的错误是由于他决心表达的不是美,而是生命,不仅是强壮而健康的身体,而且是复杂的性格或心灵状态。他发展了雕刻人像,使它从宗教延伸到世俗的范畴,也给予他的题材空前的多变性、个性和力量。他曾克服上百种技术上的困难,创造了文艺复兴时代遗留至今的第一座骑马雕像。只有一个雕刻家能达到更高的巅峰,而且还是继承了多纳泰洛所学、所做、所思才能达到。多纳泰洛的学生贝托尔德(Bertoldo)正是米开朗基罗的老师。
·罗比亚
当我们读到瓦萨里的传记时,我们心目中有关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的画面显示出文艺复兴雕刻是由很多双受精神引导的手共同合作,师徒日日相传、代代相续的事业。从这些工作室中产生次要的雕刻家,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不太响亮的名字,然而却各有所长地尽心将易逝的美化成永恒的形式。兰尼·迪·本科继承了一笔财产,本有足够的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爱上了雕刻和多纳泰洛,便在他门下忠心为徒,直到自己成立工作室为止。他为圣米凯莱一地的鞋匠工会刻了一幅《圣菲利普》(St. Philip)像,为大教堂刻了手持福音书的《圣路加》(St. Luke)坐像,满怀信心地面对着开始萌发怀疑精神的复兴的意大利。
在另一间工作室中,伯纳多·罗塞利诺和安东尼奥·罗塞利诺兄弟联合他们在建筑和雕刻方面的技巧。伯纳多为莱纳尔多·布鲁尼在圣十字教堂设计了一座古典坟墓,然后,在尼古拉五世即位时到了罗马,献身于教皇的建筑革命。伯纳多在34岁时(1461年)在佛罗伦萨圣米尼托为葡萄牙主教杰姆(Don Jayme)立了一座大理石坟墓,达到事业的巅峰。这是古典形式的全胜,只有天使的翅膀、主教的法衣和象征他童贞的皇冠例外。美国现存两幅安东尼奥的作品——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的《耶稣儿时》(The Christ Child)大理石胸像,国家艺术馆的《年轻的施洗者约翰》(The Young St. John the Baptist)。在维多利亚博物馆中有一幅圣米尼托医生乔万尼有力的头像——脸上布满青筋和思虑的皱纹——难道其他地方还可以找到比这更高贵的写实胸像?
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从邻近乡村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名字就是由村庄名字而来的。他参加多纳泰洛工作团,发现这位大师的工作缺乏足够的耐心。他以文雅、单纯和优美使自己的作品成名。他为卡洛·马苏皮尼造的坟墓不能媲美伯纳多·罗塞利诺为布鲁尼造的,但是他为圣洛伦佐教堂设计的神龛使见过的人都非常喜欢,而他附带的人像和镶画更令他声名远播。他的《玛丽埃塔·斯特罗齐》胸像(Marietta Strozzi)现存纽约的摩根图书馆和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他死时年仅36岁,如果他像他的老师一样活到80岁,成就该多大呢?
卢卡·罗比亚活到82岁,而且善用了他的年华。他使土陶作品几乎提升到主要艺术的地位,他的声名比多纳泰洛传得更远。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博物馆不展出他柔和的圣母像,那是漆上蓝白两色的土制品。他像文艺复兴的许多艺术家一样,是以金匠开始的,在那个小世界中学得设计的精艺,转而学习雕刻镶画,为乔托刻了五个大理石墙板。也许大教堂的教会委员并没有告诉罗比亚这些镶画是优于乔托的,但他们很快命他用一块描述歌唱中的唱诗班男童、女童的镶画装饰风琴房。两年后(1433年),多纳泰洛雕刻了一幅同样的作品。现在这两幅镶画正在大教堂作品室中对面而立,两者都有力地传达了童年的饱满生动。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儿童是艺术中不错的题材。1446年,教会委员聘他为大教堂圣器室的铜门雕制镶画。这些镶画无法和吉贝尔蒂的作品相比,但是它们曾在帕兹的阴谋中救了洛伦佐·美第奇的生命。现在整个佛罗伦萨都称赞罗比亚为大师了。
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遵循雕刻艺术的传统方法。然而,他同时也做泥土实验,希望这种容易处理的材料能够做得和大理石一样美。他将泥土铸成设计好的形式,加上不同化学品的釉,再放入特殊构造的火炉中烘烤。教会委员对实验结果非常满意,便任命他在大教堂圣器室门上铸立有关耶稣复活和升天的土陶雕像(1443—1446年)。这些凹版像,虽是黑白的,因为材料新颖、涂漆和设计的精练而大为轰动。科西莫和他的儿子彼罗也为美第奇宫殿和彼罗的圣米尼托礼拜堂订制同样的雕像,在这些作品中罗比亚在白色主色之外又加上蓝色。订约纷至沓来,使他迅速地、轻便地完工。他用一幅《圣母加冕》(Coronation of the Virgin)陶像美化了奥尼桑提教堂的正门,用温柔、优美的《圣母与圣婴》(Madonna and child)美化巴迪亚正门,图中的天使使我们几乎和天堂的永恒合而为一。他为皮斯托亚城的圣乔万尼教堂设计了一幅很大的《圣母访问》陶像(Visitation),其中伊丽莎白的老年形象和玛利亚的年轻、无邪、羞怯成为很鲜明的对比。罗比亚开创了艺术的新领域,也建立了一个罗比亚王朝,一直繁荣到15世纪末为止。
绘画
·马萨乔
在意大利,14世纪,绘画高于雕刻;15世纪,雕刻高于绘画;16世纪,绘画又居于领导地位。也许14世纪的乔托、15世纪的多纳泰洛和16世纪的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人的天才在这个转变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天才是时代精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成因。也许在乔托时代,古典雕刻的发现和启示并不像它们对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一样,发生很大的刺激和指导作用。但是那种刺激在16世纪达到巅峰,为什么没有使伊库甫·圣索维诺(Iacopo Sansovinos)、切利尼(Cellinis)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刻位居当时的画家之上?为什么米开朗基罗本来是雕刻家,却一步步闯入绘画的领域?
是因为文艺复兴艺术还有比雕刻更广、更深的工作和需要?艺术,在贤明、富有的赞助人的支持下,希望占据整个描述和装饰的领域。用雕像达到这个目标要费太多时间、劳力和金钱,使人不敢问津。在一个匆忙而繁荣的时代,绘画可以更轻易地表达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双重范围。哪一个雕刻家能像乔托一样迅速、杰出地描绘圣方济各的生活?而且,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思想仍是中古式的,甚至被解放的少数也依恋古神学的回声和记忆,回想它的希望、恐惧和神秘观点,它的热诚、温和与弥漫的精灵音响。这些就像希腊、罗马雕刻所表达的美和理想一样,已在意大利艺术中找到出口和形式。以绘画表达如果不比雕刻更忠实、更微妙,至少也方便得多。雕刻长久地、热爱地研究人体,因此灵魂的表现并不擅长,虽然哥特式雕刻家偶尔也做精灵的石像。文艺复兴艺术必须同时描绘身体和灵魂、面孔和情感,它必须十分敏感,足以表达所有虔诚、挚爱、热情、苦难、怀疑论、感觉论、自负和权力的全部范围和气氛,还要使人感动。只有努力的天才才能用大理石、青铜或泥土达到这样的成就。当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尝试的时候,他们必须将方法、透视学和绘画的色调差异带入雕刻之中,并为生动的表达而牺牲黄金时代希腊艺术所要求的理想形式和沉着平静。最后一点,画家使用吸引注意的色彩,或叙述大家喜爱的故事,使人们更容易了解。教会发现绘画比冰冷的大理石雕刻或端庄的青铜铸像更容易感人、更亲切地触动人们的心灵。随着文艺复兴的进行,艺术拓宽了范围和目标,雕刻降为背景,绘画的地位提高了。以往雕刻是希腊人最高的艺术表达方式,如今绘画领域加宽了,形式变化了,技巧改进了,已成为至高的、有特性的艺术,成为文艺复兴的面孔和灵魂。
这段时期绘画仍处在摸索与不成熟阶段,鲍罗·乌切洛研究透视学,后来简直没有其他东西使他感兴趣。弗拉·安杰利科在生活和艺术方面都是中古理想的实现。只有在马萨乔的画中才可感觉到即将征服波提切利、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新精神。
某些次要的天才曾转变了艺术的技巧和传统,乔托教过加多·加第(Gaddo Gaddi),加多再教塔第奥·加第,塔第奥又教安哥洛·加第(Agnolo Gaddi),而安哥洛在1380年仍用乔托形式的壁画装饰克罗齐教堂。安哥洛·加第的学生西尼尼(Cennino Cennini)将当时绘画、构图、嵌饰、颜料、油彩、上光等画家工作所积存的知识汇成《艺术之书》(Libro dell' arte)。第一页写道:“这是《艺术之书》的开始,用以表示对上帝和圣母的尊敬,也对所有圣人们……还有乔托、塔第奥·加第和安哥洛·加第示敬。”艺术成为一种宗教。安哥洛·加第最伟大的学生洛伦佐·摩纳科(Lorenzo Monaco)是一个同志会僧侣。在华丽的祭坛画《圣母的加冕》中——洛伦佐为他那“属于天使”的寺院所画(1413年),洋溢着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活力,面孔个别化了,颜色灿烂而强烈。但是在三联画上并没有透视学,后面的形象比前景中的还要高。就像从舞台上向下望见的观众头颅一般。谁能让意大利画家领会到透视学的奥秘呢?
布鲁尼里斯哥、吉贝尔蒂、多纳泰洛曾接近它。乌切洛几乎为这个问题贡献一生。他每夜都在沉思,使他太太极为愤怒。“透视学是多么迷人的东西!”他告诉她,“啊!如果我能让你了解其中的快乐多好!”对于乌切洛而言,最美的莫过于图画上平行田畦的稳定接近和远景混合。他在一位佛罗伦萨数学家安东尼奥·曼尼提(Antonio Manetti)的协助下,决心确立透视法则。他研究如何正确表达圆顶的后倾弧度,物体进入前景时的粗劣扩大,曲形廊柱的特殊变形,等等。最后他感到自己已将这种神秘化成规则,由这些规则,一个维度可传达出三维度的幻觉,绘画可以显出空间和深度。这对于乌切洛而言似乎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以自己的画证明他的原理,并且用壁画装饰圣诺维拉教堂的回廊。他的画在当时引起轰动,却经不起时间的磨蚀。他仍存的作品是大教堂墙上约翰·霍克伍德的画像(1436年),这位骄傲的贵人曾一度从攻击转而保护佛罗伦萨,现在正加入学者和圣人的行列。
安东尼奥·韦内齐亚诺(Antonio Veneziano)是乔托的门徒,斯塔尼亚(Gherardo Stamina)是韦内齐亚诺的学生,斯塔尔尼亚传授马索里诺(Masolino da Panicale),马索里诺又教马萨乔。马索里诺和马萨乔也研究他们自己的透视学。马索里诺是最初画裸体的意大利人之一。马萨乔最先应用透视学原理得到成功,使当代人大开眼界,也开创了绘画的新纪元。
他的真名是乔万尼(Tommaso Guidi di San Giovanni)。马萨乔是他的绰号,意思是“大汤姆”,正如马索里诺意思是“小汤姆”一般。意大利人喜欢为人取这种有鉴别性的名字。他很小就开始拿画笔,非常热爱绘画,对其他东西都不在意——他的衣服、他的外表、他的收入、他的债务。他曾和吉贝尔蒂一起工作,也许曾在那所学校中学到了解剖的精确性,那是他作品的特征之一。他研究马索里诺在圣玛利亚教堂的布兰卡奇(Brancacci)礼拜堂所画的壁画,也特别高兴注意到其中的透视和远缩试验。在巴迪亚寺院教堂的一根柱石上,他用从下往上看的远缩法画了布列塔尼的圣伊沃(St. Ivo)像,观者都不肯相信圣人会有这样的大脚。在圣诺维拉教堂的《三位一体》壁画上,他画了一个筒状拱环,渐缩的透视非常完美,使眼睛似乎看到画上的天花板正沉入教堂的墙壁中。
使他成为三代之师的划时代的杰作,是他继承马索里诺为布兰卡奇礼拜堂所画的有关圣彼得生平的壁画(1423年)。这个纳税的小故事由这位有新观念、真实线条的青年艺术家描绘出来:基督显得坚决高贵,彼得愤怒庄严,税吏带着罗马运动家的柔软骨架,每一个使徒的面貌,衣服和姿势都不同。建筑物和背景的山丘证明了初兴的透视学。而马萨乔自己,对着镜子摆姿态,也将自己画成群众中一个带胡须的使徒。当他绘制这一系列图画的时候,人们正用游行仪式供奉礼拜堂。马萨乔以敏锐的记忆眼光观察仪式,然后在回廊的壁画中描绘出来,布鲁尼里斯哥、多纳泰洛、马索里诺、乔万尼·美第奇和教堂负责人布兰卡奇都曾参加供奉,现在发现他们都在画里。
1425年,马萨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放下他未完成的工作,去了罗马。我们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只能猜测他也许遭到意外或病亡了。布兰卡奇那些壁画虽然未完成,却立刻被公认为绘画上的一大进步。在那些大胆的裸体、优雅的衣褶、惊人的透视学、写实的远缩法和精确的解剖细节中,在光影的微妙层次深度中,大家都感到一种新的起程,那就是瓦萨里所谓的“现代”形式。凡是佛罗伦萨行程范围可及内有野心的画家都来研究这一系列图画:包括安德烈亚、利比、卡斯塔吉诺、韦罗基奥、吉兰达约、佩鲁吉诺、彼罗·弗朗切斯卡、达·芬奇、巴托罗米奥修道士、安德烈亚·萨尔托、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没有一个已死去的人有过这么多显赫的学生。自乔托以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曾经不自觉地有过这样大的影响力。达·芬奇说:“马萨乔以完美的作品显示,凡是不以自然——至高的女主人——为向导的人,都会在徒劳的苦工里耗尽生命。”
·弗拉·安杰利科
在这些刺激的新奇事物中,弗拉·安杰利科静静地走着他自己的中古路线。他生在一个托斯卡纳村庄,本名彼得罗,年轻时就来到佛罗伦萨学画,可能是向洛伦佐·摩纳科学习的。他的天才成熟极快,而他也有希望在世俗领域建立一定的地位,但对和平的热爱、对拯救的渴望使他加入了多米尼克教团。他在各城见习修行,改名为弗拉·乔万尼,然后定居在费舍尔的圣多米尼克修院(1418年)。他在快乐、默默无名的状态下画书稿插图,为教堂和宗教团体画图。1436年,圣多米尼克的教士们转入圣马可新修院,那是由科西莫出钱、任命米开罗佐所建的。以后的9年中,乔万尼在寺院教堂、僧会礼堂、宿舍、餐厅、招待所、廊柱和小室等处的墙上画了50多幅壁画。同时他以十分谦和、十分诚挚的态度修行,修士伙伴们便称呼他为安杰利科弟兄(Angelic Brother)、弗拉·安杰利科。没有人看见过他生气,也没有人能激怒他。凯皮斯(Thomas Kempis)发现他完全“模仿基督”,只有一个微小的差错:在《最后的审判》中,这位天使般的僧侣竟忍不住将几个圣方济各教派修士放入地狱。
对于弗拉·乔万尼而言,绘画是宗教的习题,也是美学上的解脱与喜悦。他绘画的格调很像他的祈祷,而他一定先祈祷才作画。他远离了生命中的严酷竞争,觉得生命是神圣补偿和爱的颂歌。他的题材永远是宗教——圣母和基督的生活、天堂中受保佑的人、圣人的生活、僧侣团的团长们,等等。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创造美,不如说是激励虔诚。在僧会礼堂中,他画了一张副主教认为应该常存教士心中的图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一张强有力的绘图,显示出他对裸体的研究和包容一切的基督教本质,在十字架的底部,与圣多米尼克一起的是敌对教团的建立者——圣奥古斯丁、圣本笃、圣伯纳德、圣方济各、古伯托(John Gualberto)、同志会的阿尔伯特。在接待旅人的接待所入口天窗里,安吉利科描绘了有关基督化身香客的故事,因此每一个香客都应该被当作基督化身来招待。招待所内部如今聚集了不少安吉利科为各教堂和公会所画的题材:麻布公会的《圣母像》(Madonna of the Linaioli),其中天使唱诗班的团员都有女性化的柔软外形和天真孩童的微笑面孔;一幅《基督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美而柔和,可媲美文艺复兴艺术中描述同一场面的成千作品中任何一幅;一幅《最后的审判》,有一点儿太对称了,而且充满了可怖、不讨人喜欢的幻想,仿佛原谅是人道的,憎恨却是神圣的。在通向小室的楼梯顶部立着安吉利科的杰作《圣召》:一个非常优雅的天使已经对未来的耶稣之母表示敬意,而玛利亚正谦逊地、怀疑地鞠躬,用手画“十”字。在近50间小室中,这个有爱心的教士在他的教士学生的协助下,抽出时间来为每一间画一张壁画,使人回忆起一些激励的福音场面——《基督变容》、《使徒的共融》、《抹大拉的玛利亚以香膏涂基督的脚》等。在科西莫修行的双间小室中,安吉利科画了一幅《耶稣钉上十字架图》,还有《众王的崇拜》,其中众王都穿着富丽的东方服饰,也许就像这位艺术家在佛罗伦萨会议上所见的一般。在他自己的小室中,他画了《圣母的加冕》,那是他曾一再画过的最喜爱的题材。沃夫兹画廊有一幅,佛罗伦萨有一幅,卢浮宫有一幅,最好的是安杰利科为圣马可修道院所画的,其中基督和玛利亚是艺术史上最美好的形体之一。
这些虔敬作品的声名为乔万尼带来数以千计的订单。他对那些慕名而来的人说,他们必须先求得副主教的同意。有了副主教的同意,他不会拒绝他们。尼古拉五世召请他去罗马,他便离开佛罗伦萨的小室,前去为教皇布置礼堂,他选用的情景是有关圣斯蒂芬和圣劳伦斯的生平,这些画至今仍是梵蒂冈最愉悦的画面之一。尼古拉十分仰慕这位画家,建议他做佛罗伦萨大主教,安杰利科借故推辞,推荐他最敬爱的副主教。尼古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弗拉·安托尼诺即使在大主教长袍之下也仍是一个圣人。
除了艾尔·格里科(El Greco),没有人会像安杰利科一样创造如此统一、如此独特的风格,即使生手也能认出他的手笔。恢复乔托风格的单纯线条和形式;狭隘却清幽的颜色组合——金色、朱红、猩红、蓝、绿——反映出光辉的精神和快乐的信仰;形体也许太简单了,几乎没有解剖观念;面孔很美、很温和,但是苍白得不像活人,僧侣、天使、圣人都相似得近乎单调,就像天堂中的花朵一般;一切都加上温柔奉献的理想精神,气氛和思想的纯洁使人想起中古最好的时刻,不再被文艺复兴所掳。这是中古精神在艺术上的最后呼声。
弗拉·乔万尼在罗马工作了一年,一度曾在奥维托住过,曾在费舍尔的多米尼克修院当过3年的副主教;又被召回罗马,68岁那年死于该地。也许是洛伦佐·瓦拉的古典笔调写出了他的墓志铭:
基督!但愿你将赞美归于我,不因我是你所称呼的另一个人,而是因我曾将一切利益奉献于你。
有的事业是在世上,有的在天上。伊城的花将我若望举起。
基督,不要向你最忠心的信徒,我,称赞我是另一个阿佩莱斯,称赞我已贡献了一切吧;因为有些作品是为尘世,有些是为天堂。我弗拉·乔万尼,是佛罗伦萨城邦的托斯卡纳市民。
·利比
艺术从温和的弗拉·安杰利科,经过热情的马萨乔,然后到了一个喜欢生命甚于来世永生的艺术家手中。弗拉·菲利皮诺·利比,屠夫托马索·利比之子,生于佛罗伦萨同志会修院后面的穷巷里。他两岁便成了孤儿,由一个婶母勉强抚养,到了8岁婶母便把他送入同志会教团,摆脱了他。他不喜欢读指定的书,却在书页边缘上画满了漫画。副主教注意到那些画的不凡,让他学马萨乔在同志会教堂所画的壁画。不久这个少年便在同一教堂里画自己的壁画了。那些画现已不存,但是瓦萨里认为不次于马萨乔的作品。他在26岁(1432年)离开寺院,仍旧自称为“教士”(Fra),却活在“世界”里,而且以他的艺术为生。瓦萨里说了一段已被传统所接受的故事——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其真实性:
利比据说非常好色,当他看见一个中意的女人,便愿意献出一切财产以占有她。如果不能成功,便画她的画像以平息爱火。这种欲望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只要有这样的心情存在,他就不再注意他的工作。因此,有一次科西莫雇用他时,把他关在房中,以免外出浪费时间。这样过了两天,他又被色情和原始的欲望所征服,用剪刀剪下床单,从窗户攀下房外,花费很多天的时间尽情玩乐。科西莫找不到他,特别来一次搜寻,最后利比又自行回来工作。从此以后,科西莫让他自由来去,后悔把他关起来……因为,他说:“天才是天上的形体,不是捆扎的驴子。”……后来他努力以情感的束缚绊住利比,因此得到他更情愿的服务。
1439年,利比教士在写给彼罗·美第奇的信中形容自己是佛罗伦萨最穷的教士,有6个侄女与他同住,供养不易,而且她们都急于出嫁。他的作品销路甚佳,但是收入显然不敷侄女们的愿望。他的道德还不至于声名狼藉,因为他还曾经受聘为许多女修院作画。在普拉托的圣玛格丽特(Santa Margherita)修院中,他爱上了卢克雷齐娅·布蒂(Lucrezia Buti),也许是一个修女,也许是修女的监护人。他说服女院长让卢克雷齐娅·布蒂做圣母的模特。不久他们就私奔了。虽然她的父亲责备她,她还是和这位艺术家一起,做他的情妇和模特,让他画出许多圣母像,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成名的小利比。普拉托教堂的监护们并没有为这件事而反对他,1456年,他们聘请他在唱诗班席位上画壁画,描述“施洗者”圣约翰和圣斯蒂芬的生平。这些壁画现在已大大损坏,当时被公认为杰作,构图完美,色彩丰富,充满戏剧性——一端以莎乐美(Salome)的舞蹈,一端以石掷斯蒂芬达到高潮。利比生性好动,觉得这件工作太沉闷,曾两度逃离。1461年,科西莫说服庇护二世(Pius Ⅱ),让这位艺术家解除僧侣誓言。利比似乎觉得自己也脱离了对卢克雷齐娅的忠心——她现在已不能做圣母的模特了。普拉托的监护们想尽一切办法劝他回去完成壁画。最后,距开始动笔10年之后,他才在科西莫的私生子卡洛·美第奇——现任使徒书记的劝诱下将壁画加以完成。在斯蒂芬葬礼的一幕中,利比竭力去实现的是——建筑背景的透视错觉,环绕尸体而各有特性的形体,科西莫私生子为死者宣读礼文时的强壮体型和平静圆满的面孔,等等。
虽然他在性行为方面很不规矩,可能也正因为他对女人可爱的温柔很敏感,利比最好的作品全是圣母像。它们缺乏安杰利科圣母像中的非俗世精神,但是却表达了深度的柔软人体美和不尽的温柔。在利比教士的画中,圣父一家变成了一个意大利家庭,被家庭偶发事件所包围,而圣母玛利亚的肉体美更预报了异教文艺复兴的来临。除了女性魅力之外,利比在他的圣母像中又加上轻灵的优雅,这种特色后来传给了他的徒弟波提切利。
1466年,斯波莱托城邀请他在教堂东面半圆室内再度描绘圣母的故事。他谨慎地工作,热情冷静下来,但是力量也随着热情消逝,他再也无法重现普拉托壁画的杰出成就了。他在这次工作中死去(1469年),瓦萨里认为是被他所诱惑的一个女子的亲戚毒死的。这一点不太可能,因为他被葬于斯波莱托大教堂中。而且几年以后,他的儿子还应洛伦佐·美第奇之聘为他的父亲建立了富丽的大理石墓。
每一个创造美的人都值得纪念,但是我们这里只能匆匆跳过多米尼克·韦内齐亚诺(Domenico Veneziano)和谋杀他的嫌犯卡斯塔吉诺。多米尼克从佩鲁贾(1439年)应召到圣玛利亚教堂画壁画,他的助手是一位来自伯戈城(Borgo San Sepolcro)的有为青年彼罗·弗朗切斯卡。他在这些作品中——现已失散——第一次做了佛罗伦萨油画实验。他只留给我们一张杰作——《妇人画像》(Portrait of a Woman,现存柏林):上梳的头发,慧黠的双眼,突出的鼻子和丰满的胸。根据瓦萨里的记载,多米尼克把这个新技巧教给了当时也在圣玛利亚教堂作壁画的卡斯塔吉诺,也许竞争破坏了他们的友谊,而卡斯塔吉诺又是一个冷酷、冲动的人。瓦萨里叙述了他谋杀多米尼克的经过,但是其他记录显示多米尼克比卡斯塔吉诺多活了4年。卡斯塔吉诺以克罗齐教堂的基督受难图闻名,其中的透视技巧连同行都大感惊奇。在佛罗伦萨的圣阿波罗寺院中藏有他虚构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乌波提(Farinata degli Uberti)画像,还有虚张声势的《皮博·斯帕纳像》和《最后的晚餐》(1450年)。《最后的晚餐》似乎画得很差,毫无生命力,但是可能对达·芬奇多多少少提供了一两个概念。
其他
若要生动体会科西莫时代的佛罗伦萨艺术生命,我们不能只想到上面匆匆提过的主要天才。我们必须走入艺术的旁街和小巷,参观上百的店铺和工作室,其中有陶匠塑土、绘彩,玻璃匠将玻璃吹成、切成脆弱可爱的形状,金属匠将贵重金属或宝石雕成珠宝和勋章、印玺和钱币等。我们也许可以看见嘈杂中专心的工匠正把铁、铜或青铜锤成武器、甲胄、容器、用具和工具。我们必须观察橱柜工人设计、雕刻、镶嵌或磨饰木材;雕刻者在金属上刻图案;还有其他工人凿烟囱片,装饰皮革,刻象牙或制造细致的纺织品以使肉体更迷人,或用以装饰家庭。我们必须进入修院,看看耐心的僧侣装饰书稿,沉静的修女缝制含有历史故事的花毡。我们尤其必须想象一代人,进步得足以了解美,明智得足以将荣誉、食粮和刺激给予那些潜心创造的人。
金属雕刻是佛罗伦萨的一项发明。其大师古登堡(Gutenberg)和科西莫死于同一年。菲尼圭拉(Tommaos Finiguerra)是一个黑金镶嵌工人——他在金属或木头上刻铸图案,再用黑色的银铅合金填入凹洞中。传说有一天一张飘落的纸片或布片落在镶好的金属表面,拿起来以后发现上面印着花纹,这个故事不免予人后见之明的感觉。反正菲尼圭拉和其他工匠都精心地在纸上印出图案,以判断刻出的效果。一位佛罗伦萨金匠保迪尼(Baccio Baldini,约1450年)显然是最先从刻好的金属表面印制图案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保存和放大艺术家的作品。波提切利、曼特尼亚和其他画家都曾供给他画稿。10年后,莱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发展出新的雕刻技术,以便将佛罗伦萨绘画传遍世界。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位轻视古典的人,他是当时最具体的综合工匠。除了政治之外,阿尔贝蒂经历过该世纪生活的每一面。他生于威尼斯,是佛罗伦萨的一个被放逐家庭的后代:科西莫复辟时回返佛罗伦萨,爱上了那儿的艺术、音乐、文学和哲学团体。佛罗伦萨也把他当作巨人般的完人。他英俊、强壮,体力过人,双脚被捆时还能跃过一个直立的人的头顶;能在大教堂中掷出钱币,达到圆顶;喜欢驯野马、爬山自娱;也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有名的风琴家,迷人的演讲家,有力的雄辩家,一个机灵、清醒的聪明人。他是一个优雅有礼的绅士,对谁都很慷慨,只有对女人例外。他常以不愉快的固执态度和近乎做作的愤怒讽刺女人。他不太在乎金钱,将财产委托朋友代管,也和他们分享收入。“人可以做一切事,如果他们有意去做的话。”他说。的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要艺术家很少不精通数种艺术的。像半世纪后的达·芬奇一样,阿尔贝蒂是十余种行业的大师,或者至少是娴熟的老手——数学、机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戏剧、哲学、市政法和宗教法,等等。这些题材他几乎都撰文讨论过,其中一篇绘画论文还影响了彼罗·弗朗切斯卡。也许达·芬奇也曾受其影响。他还加上两篇讨论女人和爱情艺术的文章及一篇著名的《谈家庭照顾》。每画完一张图画,他会叫进一群小孩,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小孩不懂,他就认为是一大失败。他是首先发现可以用照相暗箱的人。他还是一位建筑家,曾逐城建立罗马式教堂正面或礼拜堂。根据瓦萨里的记载,他在罗马参加尼古拉五世“翻转首都”的建筑计划。在里米尼他将圣方济各教堂几乎改建成异教的庙宇。在佛罗伦萨,他为圣诺维拉教堂立了大理石前部,在圣潘克拉齐(San Pancrazio)教堂中为卢西莱家族建立了礼拜堂,还有设计简单、稳定的两座宫殿。在曼图亚城他用因科罗纳塔(Incoronata)礼拜堂装饰大教堂,又以罗马凯旋门式的正面装点圣安德烈亚教堂。
他写过一篇喜剧《费罗都斯》(Philodoxus),其中的拉丁口语太流畅了,因此他谎称是新发现的古典作品以愚弄世人,竟没有人怀疑他;而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身为学者,竟也将它当作罗马古典作品来印行。他用闲谈对话的方式写论文,使用的意大利文非常平易单纯,连忙碌的商人都乐于拜读。他的宗教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基督教,但是他听见大教堂唱诗又总会怀有虔诚的礼拜之心。他极富远见,预先忧虑基督教信仰的衰颓会使世界陷于行为和思想的混乱。他热爱佛罗伦萨四周的乡村,尽可能隐入那些地方,而且使对话录主角提基里诺(Teogenio)说出如下的话语:
我可以悠闲地在这儿欣赏已逝名人的社会。当我要和圣人、政治家、大诗人谈话时,我只得转向书架,我的友伴比你宫中的一大群客人和谄媚者要好得多。
科西莫同意他的看法,老年时最爱在他的别墅、他的朋友、他的艺术收藏和他的书本中找寻慰藉。科西莫患了严重的风湿,晚年将外部的事务交给卢卡·比蒂处理,此人滥用机会增加他的财富。科西莫的遗产并未因无数慈善行为而减少,他曾古怪地抱怨上帝永远先他一步,以利息还报他的慈善。他在乡村的邸宅中接受柏拉图门徒菲奇诺的教导,研究柏拉图。科西莫垂死时,菲奇诺答应给他死后生命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不是基督权威。朋友、敌人同样都为他的死亡而悲哀(1464年),惧怕政府陷于混乱。几乎全城的人都追送他的遗体到坟墓去,那是他授命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为他在圣洛伦佐教堂所预建的。
圭恰尔迪尼等爱国者被后来美第奇家族的行为所激怒,把他当作布鲁特斯眼中的恺撒(布鲁特斯刺杀恺撒),马基雅维利却尊崇他有如尊崇恺撒一般。科西莫推翻了共和国,但是他所阻止的自由是富人以党派混乱统治国家的自由。虽然也偶有残酷的记录,他的统治大体上却是佛罗伦萨史上最温和、最平静、最有秩序的时期。另一段好时期则属于他精心训练的孙儿统治时代。很少有王子如此贤明慷慨,如此真诚地重视人类的进步。“我负欠柏拉图许多,”菲奇诺说,“但是对科西莫亦然。他使我了解德行,正如柏拉图使我了解概念一般。”在他手下,人文运动开花了;在他手下,多纳泰洛、安杰利科和利比等天才受到了慷慨的资助;在他手下,久被亚里士多德掩盖了光辉的柏拉图恢复了人文主义主流的地位。科西莫死后一年,当时间有机会冲淡他的光荣、显露他的缺点时,佛罗伦萨会议表决在他的墓上刻铸最高贵的头衔:国家之父。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文艺复兴因他而抬头,在他的孙儿领导下达到最纯粹杰出的巅峰,在他的重孙手下征服了罗马。在这样的王朝下,也许很多罪恶都被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