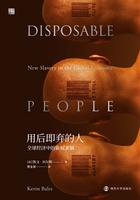
百万饿虎亿万雁
谁是现代奴隶持有人?答案可能是任何人和所有人:任何人,即有一定资本可以投资的人。那些看起来拥有被奴役妓女的人——皮条客、鸨母、妓院管理人员——事实上通常只是雇员。作为雇佣劳力,皮条客及其助手提供了控制女性的残暴,和尽可能的商业剥削。尽管他们只是雇员,但皮条客很会为自己谋福利。他们经常住在妓院里,拿固定工资并以其他诡计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卖给客人的食物和饮料价格飞涨,皮条客将价差所得纳入囊中。更有利可图的是,控制性交易价格。虽然每个女性都有个基本价,皮条客会打量一下顾客,然后据此提出相符的价格。在这种方式下,一个客人支付的价格可能是正常价格的两倍或三倍,所有多得的部分都会到皮条客那里。皮条客串通会计员,有条不紊地欺骗妓女,有意地减少划到账上用于抵债的数目。如果他们精于管理,八面玲珑,数十倍于他们基本工资的所得,对皮条客来说唾手可得。对于一个主要技能是暴力和威胁的前农民来说,这是笔不小的收入,但相较于那些掮客和真正的奴隶持有者的所得,这点钱不值一提。
在村子里买卖女孩的掮客和中介,他们只是短期的奴隶持有者。他们的生意部分是招募中介,部分是贩运公司,部分是公共关系,部分是绑架团伙。他们旨在低买高卖,同时从村子里源源不断地招募女孩。掮客里面男女都有,数量几乎相等,并且通常来自他们进行招募的地区。一些本地人会参与女孩的交易,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警察、政府官员甚至学校老师。公众信任的地位是购买年轻女孩的绝佳起点。不用管他们工作的性质,他们仍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作为工作提供者和支付给父母的大量现金的源头,他们在社区中非常有名。许多女性掮客自己曾经被贩卖,做了多年妓女,如今人近中年,靠着给妓院提供女孩谋生。这些女性是性产业行走的广告。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收入,她们西式的服装以及迷人和精细的生活,为她们买下的女孩指出了一个玫瑰色的经济的未来。但是在妓院,她们经过这么多年还能生存下来可能只是例外——更多年轻的女性回到村里,然后死于艾滋病——但是父母们倾向于乐观。不管这些商人是本地人或中介,他们都将拉皮条的生意和其他经济追求结合。一个归来的妓女可能会和家庭生活在一起,照顾父母,拥有一两块稻田,同时另一边做着买卖女孩的事情。与皮条客一样,她们的生意很好,通常从每个女孩身上两三个星期之内就能挣到双倍的钱,但相较于长期的奴隶持有者,她们的利润仍然少之又少。
真正的奴隶主常常是中产阶级商人。他们无缝衔接进社区,并且不会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承受社会歧视。如果有的话,他们会被羡慕为成功的、多元经营的资本家。妓院所有权通常只是奴隶持有者许多生意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妓院老板可能会与有组织犯罪有某种联系,但是有组织的犯罪常常也会与警察和政府中的大部分有关。实际上,现代奴隶持有者的工作最好不要再被视为脱离常轨的犯罪,而是冷漠无情的资本主义的完美例证。拥有一个奴役年轻女性的妓院仅仅是一桩生意。投资者会说他们是在创造工作机会和财富。他们的行为毫不虚伪,因为他们遵循一项重要的社会规则:做任何事情的最好理由是挣很多钱。当然,生活在中产阶级邻里之间,奴隶持有者不会对外显示关于他的工作的任何迹象。他的邻居们将只知道他是个商人,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为此而尊重他。过于接近地探究他人的私事在泰国文化中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不要多管闲事”(yaa suck)在泰语中是最有力的反驳。因此,奴隶持有者获得了剥削、虐待年轻女孩的所有福利,却不会有任何社会反响。
事实上,奴隶持有者可能是合伙企业、公司或社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投资涌入泰国,大量资本的迁移被称为“飞雁”(11)。强势的日元在全国导向购买和建造,当电子公司建造电视机制造厂时,其他投资者发现投资性产业的所得会更多。步日本后尘,“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在性产业中发现了大量机会。(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也被证明是最旺盛的进口泰国被奴役女孩的市场,稍后会讨论。)“飞雁”和“小龙”有资源买通当地罪犯、警察、管理人员,也有建立商业性产业所需的资本。随着性产业的爆发,泰国本地人也会投资妓院;由于缺少资本,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更贫穷的工人阶级为销售对象。
尽管年轻的妓女经常与警察打交道,但她们可能从未见过事实上拥有她们的人。当今泰国奴隶持有者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正是一个坚持“一臂之距”原则的资本主义的典型。妓院老板,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跟妓女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更有可能,有些合伙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奴隶持有人,他们单纯以为只是雇用了商业的性劳力。高额的回报承诺是投资朋友的新企业的一剂强心针,多数泰国人会投资朋友或亲戚的生意,而非投入股票证券市场。多元化投资在泰国还是个新事物,但发展迅速。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很快在全泰国被新商人模仿。通过观察发达国家,他们发现投资者将钱投入股市共同基金,因为其回报高于其他形式——至于这个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是开矿的还是制造刑具的,则无关紧要。以不知情为借口所需要的距离并不大,只需一小步便足以隔绝投资者和他的良心。
无论他们是单个泰国人、合伙人或外国投资者,奴隶持有者有诸多共同点,他们展示了今天新奴隶主的特征。他们和奴隶之间不再有民族或种族差异(日本投资者除外)。他们也无须用种族背景去合理化持有奴隶的行为,也不会牵涉奴隶继承的问题,或想到奴隶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奴隶一点都不感兴趣,唯一关心的是他们的投资底线。如果他们不是奴隶持有者,他们将会把钱投到其他生意中,但他们缺少这样做的动力,因为妓院远比股市更牢固、坚挺。在泰国,为经济做贡献是一种强大的道德论述,而这些奴隶持有者为他们的贡献而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提供就业机会,甚至是将深陷农村贫穷中的债务女孩拉出泥潭。道德问题从来都不重要,因为奴隶持有者从来不会想到他们妓院里的那些女性,不会关心她们从哪里来或者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为了理解今天的奴隶制,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它于其中运行的经济环境。尽管经济在增长,但以西方标准来看,泰国人均收入仍然低得可怜。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农村人口仍处在贫困中。如果一个农村家庭有房子和稻田,他们每个月依靠不到500泰铢(20美元)就能生存。这样的绝对贫困意味着,每天吃着带虫子的米饭(蟋蟀、蛆虫被大范围食用)、野菜和能捉到的任何鱼类。这个水平只有在农村能勉强维持生存,低于此意味着饥饿、卖房卖地。对于多数泰国人来说,每月收入2500—4500泰铢(100—180美元)是常态。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穷人变得更加贫穷,并且更多的工作被蒸发掉:在城市,房租占了工资的一大半,物价水平持续攀升。这个收入水平只会贫困但不会挨饿,因为政府政策人为地压制米价(导致农民的贫困)。大米每千克20泰铢(75美分),而一个四口之家每天能吃1千克米。处于贫困工资水平的泰国人,他们或许仅能吃饱,除此之外什么都干不了。无论是在城市、乡镇或农村,要想谋活路,就意味着每周要工作6—7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疾病或受伤能够迅速让这个生活标准直线下降。没有福利或健康保障体系,紧缩的财政状况没有给储蓄留一点空间。对这些家庭来说,卖女儿得到的20000—50000泰铢象征了一年的收入。数目如此庞大,充满诱惑,这使得父母们对性奴隶的现实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