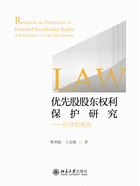
第一节 优先股制度概况
一、优先股的内涵与特征
公司融资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股份发行、负债以及利润留存。利润留存属于内部融资,而股份发行和负债则属于外部融资范畴,需要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在变动不居的市场条件下,只有适应公司需求并能够满足投资人偏好的资本动作方能实现投融资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股东异质化”1的现实状况下,为满足不同投融资主体的偏好,融资过程有可能偏离标准操作,发行一些条件或条款与标准条款有差异的股份,或者构造出一些与股权资本特点相类似的债权,又或者设计出一些兼具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特征的融资工具——混合金融工具,即优先股。
普通股股东权利是投票权和财产性权利的统一体。其中,投票权是依据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股东集体投票的方式对公司重大决策进行投票表决以及选举董事会成员的权利;财产性权利也称“经济权利”,包括两部分:在公司正常运营时获得经营收益分配(分红)的请求权,以及在公司清算时获得剩余财产的权利。2 普通股的这两类权利可以拆细并通过契约重新安排,形成与普通股的权利、风险承担有别的优先股(类别)股,也有学者称之为“特别股”。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柯芳枝教授所下的定义很有代表性:“股份得分为特别股与普通股,而特别股本身,并不止一种,得以章程规定其种类……所谓特别股,系指该股份表彰之股东权所具之盈余分派请求权、剩余财产分派请求权或表决权等权利内容异于普通股而言。此处所谓异于,乃指优于(或先于)或劣于(或后于)而言。”3比如,优先股股东通常享有优先分红权:“优先股为持有者提供了类似债券的固定收益及持续收入流( constant payment stream) ,同时也为发行人提供了类似于普通股的定期支付灵活性。”4此外,作为混合证券的优先股还因此被描述为介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之间的夹层融资,5它结合了股权与债权的特征——首先是一种股权权益,同时通过合同附加了经济利益和优先性权利,从而具有债权色彩:
第一,优先股的优先性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的,是在某些经济利益上的优先——通常为获取分红及清算方面的优先。优先分红权保障优先股股东在发行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获得“上行” ( upside)保护,分享公司发展的红利;优先清算权旨在提供“下行” ( downside)保障,在公司陷入困境时也能保障优先股股东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剩余财产分配,同时也避免普通股控制下的董事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截留分红并恶意通过公司清算而将原本属于优先股的收益转移给普通股的可能性。因此,优先分红权与优先清算权基本都是同时并存于优先股中。
第二,优先股权能有多种形式,可以根据优先股股东与发行人公司之间的合同进行多种组合,即权利具有复合性。例如,美国公众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大多为累积分红型不可转换优先股,而封闭公司(私募投资参与的创业企业)发行的优先股则多为非累积分红型可转换优先股。6 不同的权利设置体现了投资人不同的需求。在创业企业中,投资人,尤其是“风险投资者” ( venture capitalist) ,更多着眼于在未来与普通股股东一起分享企业快速发展的收益,同时又要在企业创业初期处于高风险阶段时尽量控制风险,因此倾向于采用可转换优先股作为投资工具,保留在企业发展良好并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时转换为普通股的可能性。
第三,优先性权利的获得意味着优先股其他某些权利的让渡。优先股获得了经济利益上的优先,作为对价,则需要让渡股权中的公司日常经营和控制权(投票权)。优先分红权使优先股具有固定收益特性。7 由于固定收益,公司经营事项的决策权对优先股股东来说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作为一种权利平衡设计,优先股股东需要让渡其表决权。在公司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优先股股东不具有投票选举公司董事等表决权利。不过,在某些触发事件发生时,如公司持续一段时间未能支付分红,则会出现表决权恢复问题,优先股股东获得股东大会表决权或者选举一定数量董事席位的权利,以弥补其因经济性权利未获实现而导致的利益失衡,同时也促使发行人公司及其高管层扭转偏离正常分红安排的状况。
第四,优先性权利设定的合同性。优先股股东的优先性权利来自融资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特别规定,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谈判在合同中预设保护权利实现的条款。公司法作为开放式的普遍适用的条款文本,8提供了一套标准形式的合同,以普通股为样本进行股东权利义务的设定,体现交易中最普遍且通常最容易达成的协议条款。同时,公司自治原则允许对这些条款进行变更,而设置优先股股东权利的合同,就是在变更通常条款的前提下列出那些被变更的条款。优先性权利内容首先体现在优先股融资文件中,其后会被纳入公司章程,因此章程是优先股合同最主要的载体形式。风险投资合同本质上就是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签订的以风险投资家提供资本、参与公司治理、实现投资回报为内容的系列合同。
我国《公司法》中没有使用“优先股”的概念,但是其第126条对股份发行的规定中着重强调“同种类”股份应具有相同的权利,第131条还授权国务院对公司发行其他种类股票作出规定,9《公司法》本身已经预留了公司发行区别于普通股的其他类型股票的空间。在实践中,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普通股票发行时,大多会特别表明和强调其发行的是“普通股”股票。依据《公司法》的授权, 2013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2014年3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启动优先股试点实践,由此开启了优先股制度在中国的适用之路。
二、优先股法律性质辨析
优先股并不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设计。通说认为,优先股与公司制度是结伴而生的,最早出现于欧洲。据考证,16世纪的英国就有了优先股,而此时公司制度才刚刚萌芽。10 只是在公司制度发展早期,由于整个商品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市场发达程度所限,大多公司只发行普通股,优先股的社会影响非常有限。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11随着工业化进展和生产力提高,在铁路、运河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动下,优先股开始发挥出强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优势,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学术界也早已认可优先股作为一类股份类别的存在。股东权利包含三种权利维度:经济性权利、参与性权利和处分性权利。优先股主要体现为经济优先性权利,因此可视为股权的经济性权利差异化配置主要样态之一。12 柯芳枝教授对股份进行的首要分类就是“优先股、普通股、劣后股与混合股”,认为优先股是以普通股为基准,就公司盈余或剩余财产之分派优先于普通股之股份。13 刘俊海教授认为,股份可以分为普通股与特别股,特别股以权利内容之不同可以分为优先股、劣后股和混合股,优先股是指与普通股相比,在分取股利或剩余财产方面(不包括表决权等共益权)享有优先性权利的股份。14 冯果教授认为,股份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系根据股东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风险大小不同而区分;普通股是指股东权利平等而无差别待遇的股份,优先股则指对公司享有比普通股优先内容或优先性权利的股份,属于特别股的一种,系以普通股为基准而划分。15
从财产的视角来看,公司被视为“财产的集合”,发挥着类似集装箱的作用。将不同性质和种类的财产投入公司,不论是采用股权投资、银行借贷还是其他合同方式,最终均输出以股份(股票)和债权(债券)为表现形式的新财产,对应公司的“资本” ( equity)和“债务” ( debt) 。这就是“资本化” ( capitalization)的过程,16原财产所有权人成为拥有股权的股东或者拥有债权的债权人。股权和债权两种形式在历史上的演变比较频繁,还出现了各种衍生形式,包括在不同时期对是否属于所有权凭证、是否具有固定收益属性的争论等等。但总体而言,股权,尤其是最为典型的普通股,与债权构成公司融资的两种基本工具形式,是公司财务架构中的两座堡垒,是公司融资的典型甚至绝对模式,其他融资手段都要与普通股或债权进行类比描述。17 优先股被认为是这两种基本形式的混合体,有些功能类似于债权,有些功能类似于普通股,或者两者兼备(如图1-1所示)。

图1-1 资本市场的基本结构18
基于优先股的灵活性,不同的优先股拥有不同的特征,或倾向于普通股,或倾向于债权。但是,在一些表征基本特性的特征方面,仍然可以对优先股与普通股、债权等邻近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分。总体而言,优先股与普通股、债权的异同在于:在经济效果上,优先股类似于债权,收益与风险的波动不大,且具有固定收益特征;在法律上,优先股更类似于普通股,优先股股东不得依据合同起诉请求返还投资本金或者未付的分红,而且与债权不同,优先股与公司的合同可由公司单方面变更。19 下面通过列表方式对优先股与普通股、债权的异同进行详细对比。
表1-1 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较

表1-2 优先股与债权的比较

(续表)

由上可见,在某些经济要素上,优先股类似于债权。譬如,优先股股东对公司资产具有固定收益索取权,同时还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定期支付,其中优先分红权类似于债权利息,优先清算权的约定类似于债权人本金返还请求权,且两种请求权都有限额限制,支付金额的上限乃通过合同预先约定。
但是,在法律性质角度,优先股又呈现出强烈的股权性质。最典型的体现是在应对风险方面,优先股与债权具有不同的抗风险能力。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都在寻找保护其在公司资产上的请求权免受公司和普通股股东剥夺的途径,但是可用的方法差异很大。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违约时加速实现债权,这会对普通股股东和管理层造成很大的压力,是债权工具“锋利性”的主要体现。相比之下,优先股股东可依赖的救济则相对偏弱。优先股股东可以利用优先股合同中的约定进行自我保护,但是没有请求加速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权利——对优先股的分红属公司管理层自由决策范畴,管理层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对优先股进行分红,而且即使公司或管理层违反了优先股合同条款的约定,优先股股东通常也无权请求返还本金,只能寻求合同约定的其他救济方式。优先股股东利用回赎权谋求退出投资是一种方式,但是回赎权也不能随意行使,其决策权掌握在公司手中,而且受到不能因回赎损害债权人利益等强制性规则的约束。理论上,优先股股东可以获得对董事会的控制权。但是,实践中除了一些创业企业外,董事会多由普通股股东控制。因此,优先股股东在对抗风险方面的能力明显弱于债权人,体现出作为公司“内部人”的品格。
此外,在对公司剩余财产分配的请求权方面,优先股与债权也有明显差异。优先股虽可以约定优先清算,但其优先性仅仅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的。换言之,在分配公司剩余财产时,优先股股东的受偿顺位在债权人之后,不能超越债权人。这是优先股股权性质的另一个典型体现。
市场经济属于权利性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例如,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具有风险厌恶倾向,对冲基金需要通过对冲投资获得套保收益,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基金希望在前期保本的同时保留后期分享企业高速发展红利的机会,企业创始人在获得高额融资的同时需要保留对企业的控制等,这些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丰富图景。对这些需求的不断满足促进了融资市场的发达,而后者又是公司制度变迁并不断丰富的内在动力。传统理论对股权与债权进行泾渭划分,试图区分出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对于公司资产负债比、公司价值、破产界限的确定以及公司收入及业绩的衡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公司融资角度而言,股权与债权都是融资工具。而随着融资实践的发展以及投融资双方需求的多样化,融资工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演化方式。各种可转换证券(包括可转换债与可转换股票)及衍生证券的出现,逐渐消融了股权的法定属性与债权的约定属性。债券的格式化和标准化,以及股票的财产性和合约性,使得基于传统的物权与债权来区别股权与债权融资模式显得较为“笨拙”。20 在公司融资工具的选择中,公司自治所带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优势被充分发挥。投融资双方不再拘泥于传统股权与债权的界限,而是针对各方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条款设定,为优先股的创设提供了可能性。由此反映出的一个重要趋势——股票、债券或者债权都是融资的不同途径和手段而已,其产生的动因在于满足融资需求、契合不同的经济目的,其区别在于风险、收益和成本的不同,至于法律性质上的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21 更可取的姿态是,立足于公司融资的语境,从公司治理架构的角度讨论公司控股股东及管理层对公司不同参与人的义务。
事实上,西方公司法律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放弃了对普通股与优先股差别的过度强调。以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为例,该法有关公司股份设置的规定为:“每个公司都可以发行一种或多种类别的股票……每一类别股票的任何或全部数量都可以拥有完整投票权、受限投票权或无投票权,这种包含资格条件、限制和制约要求的指定性、优先性、相对性、参与性、选择性或其他特殊权利安排应在公司注册证书及其修正案,或董事会依据注册证书明确授权而作出的股票发行方案决议中予以明确。”22由此可见,美国相关公司法已不再为优先股设置标签,而更加注重股份设置的灵活性,强调公司章程的授权性,授权公司依据现实需求设置具有不同权利内容的股票类别和系列,打破概念或称谓上的局限,提供权利配置的必要张力,促进投融资需求的结合。23 与之相对应,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大多不会强调从概念或定性的角度区分各种不同的融资工具,而是更多地考察董事、高管人员的信义义务指向、代理成本抑制以及公司各种参与人的正确激励方向等。
三、优先股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 股东异质化现实驱动差异化股东权利设置
自从美国学者阿道夫·A. 伯利( Adolf A. Berle)和加德纳·C. 米恩斯( Gardiner C. Means) 1933 年在其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 (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中提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以来,公司的独立人格及集中管理就成为现代公司五大核心特征中的两项重要内容,而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的公司治理结构就自然衍生出股东同质化假设。这种假设理论认为,在公司治理层面,所有股东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在公司治理中被视为“恒定的参数”24,其利益、目的和能力都是一致的。即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其投资于公司的目的都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这种目标与公司利益目标是一致的,且每个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参与度和理解能力都是一致的,属于同质化的群体。同样,基于这种假设,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被认为是公司治理中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股东之间的立场与诉求差异、利益冲突以及股东之间的摩擦成本、协商成本等往往被忽略。
但是,随着公司实践内容的丰富以及对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股东之间事实上存在多维的利益分歧,以资本多数决为基础的“股东民主”实际上可能演化为控制股东权利的“多数暴政”。25 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矛盾,以及短期股东与长期股东之间的矛盾(追求短期持股将促使公司追求高风险投资,损害长期股东的利益)等多种矛盾形式的存在表明,如果继续忽略股东差异性的存在,将会导致对某些股东利益的压迫与侵蚀。事实上,股东之间除了持股数量的差异外,对公司的利益期待、诉求、关切度、风险偏好、发展策略都可能持有不同见解,在权利行使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和程度,包括谈判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和对冲基金等专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专业投资者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以及对管理层的影响程度上都远超普通个人投资者,其利益诉求也与个人投资者、其他投资人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甚至是直接的冲突。这些差异和冲突都表明,公司股东内部并不是一个利益诉求完全重合的“大同”团体,股东异质化才是鲜活的现实。
在公司融资层面,股东异质化的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创业企业为例,因为高风险与高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创业企业融资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创始人拥有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对企业运营具有实质影响力,同时其自身也极其珍视对企业的控制权,希望由自己主导企业发展,牢牢把控这种控制权,将创意转化为产品来实现其市场效益。但是,他们又必须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方可将其创意转化成生产力。而风险投资人正是看中这种创意及创始人的个人专业技术能力才会作出投资决策,他们希望将创始人牢牢锁定在创业企业中,但同时,他们也面临信息不对称风险,担忧创始人及管理层在运营中脱离控制而增加资金风险,却又不想放弃企业未来的良好预期及必要时对企业的控制权,希望保留灵活退出渠道。在此类企业中,创始人与风险投资人对企业的期待有差异,投资各方对企业未来的期待与成熟期企业股东的期待自然也不同,导致难以利用已有普通股制度框架充分表达各方利益诉求。此时,就需要足够灵活的权利义务设计和权力配置,以契合创业企业在初创期的典型特征及需求。
(二) 公司合同理论为优先股设置提供了空间
关于股权的性质,存在各种传统民法理论,包括所有权说、债权说、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独立民事权利说等。这些理论对股权描述的侧重点虽不同,但都是从外观上一般性地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性权利及非财产性权利内容,26而对股权内容中各种权利的内在本质来源并没有过多阐述。不过,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公司合同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参与方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合同关系,各参与方,包括股东之间、股东与董事及其他管理人员之间,通过合同设定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合同即公司章程。27 公司之所以需要章程,是因为章程具有明确的公示性,并由此产生了更强的约束力,这是章程与普通合同的主要差异。28 因为公司的公共性强于合伙等形式,从而对利益攸关者的约束力不同。合同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方不具有效力。章程则具有公示性,因此某些对其他利益攸关者具有影响的事项,需要进行登记以增强其公示效力。
从公司合同角度出发,对公司法的作用会得出另外一种理解:公司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而公司法则被视为标准合同条款,作为标准合同文本,其中包含一系列强制性法律规则与默认规则。默认规则模仿了各合同参与方在交易中最普遍且通常最容易达成的协议条款,由各方主体自愿选择全部或部分采纳,其作用是提供一套标准形式的合同。默认规则留给参与方“选出” ( opt-out)规则的权利,允许偏离合同法条款,只要求各参与方就其合同中偏离默认规则的方面作出约定。29 这种方式在降低各方交易谈判成本的同时,还能够通过促使各方“围绕默认规则进行谈判”,鼓励信息披露并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弊端。这也是公司自治原则的基础。强制性规则则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合约失效”基础之上,避免因为这些强制性条款的缺失导致某些主体权益因信息弱势而被剥削,或者使第三方利益受到不利影响,又或者因为集体行动问题导致合同效率降低或产生不公平的结果等。例如,有关董事对公司的义务就属于强制性规则范畴,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变更。
正是基于这种公司合同理论及公司自治原则,公司各股东及投资人之间可以灵活约定其所持股权的不同权利和优先性权利内容。不论从自益权与共益权进行分类,还是从财产性权利与非财产性权利进行分类,股权内容设计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架构都属于公司默认规则及公司自治范畴,给股东将各项子权利分割并重新组合保留了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优先股制度可以“将对财产收益权或表决控制权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容纳到同一公司中”30。实际上,优先股股东是通过放弃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控制权换取经济收益上的优先性权利。当然,与债权人可以要求额外担保类似,优先股股东如果想谋求更好的“待遇”,也可以通过合同协商争取对公司某项重大事项的控制。这体现了公司制度的创新以及权利分配的平衡。总之,优先股制度的设置有利于公司实现理想化和个性化的治理架构,有利于公司依据融资实践与现实需求调整内部制度设计,促进公司内部的权利平衡,实现股东实质平等,增强公司制度的活力。
1 汪青松、赵万一:《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变革——以股东“同质化”假定到“异质化”现实的演进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2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272页。
3 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4 William W. Bratton, Corporate Finance: Cases and Materials, 7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12, p. 607.
5 参见〔英〕艾利斯·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6 See William A. Klein & John C. Coffee, Jr. ,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Leg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10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8, p. 305; Ronald J. Gilson& David M. Schize, Understanding Venture Capital Structure: A Tax Explanation for 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6, No. 3, 2003, p. 879.
7 优先股的固定收益是指其收益不随公司盈利状况发生变化,但是与债券不同,如果公司没有盈利,则优先股的固定收益并非必须支付。
8 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 (中译本第二版),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9《公司法》第126条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第131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
10 参见曹立:《权利的平衡:优先股与公司制度创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11 See George Heberton Evans, Jr. , The Early History of Preferred Stoc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9, No. 1, 1929, pp. 43-44.
12 参见汪青松:《股份公司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的域外借鉴与制度建构》,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
13 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14 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页。
15 参见冯果:《公司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16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17 See William A. Klein & John C. Coffee, Jr. ,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Leg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10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8, p. 305.
18 See Frank J. Fabozzi & Franco Modigliani, Capit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2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Inc. , 1996, p. 12.
19 由于优先股股东权利条款嵌在公司章程中,因此公司可以依据公司章程修订规则对优先股股东权利条款进行变更,这也是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所面临的风险之一。详见后文论述。
20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21 同上书,第286页。
22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ion Law, Section 151(a).此外,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在“授权的股票”一节也规定:“(a) 公司章程必须规定授权公司发行的股票的类别、同一类别中股票的系列以及每一类别和每一系列股票的数量。如果公司被授权发行一种以上类别或者系列的股票,公司章程必须对每一类别或者系列规定不同的名称,在发行一个类别或者系列的股票前必须对该类别或者系列股票的条件作出相应规定,包括优先权、权利和限制。除非在本节允许的可变范围内,某一类别或者某一系列的所有股票必须与该类别或者系列的其他股票具有相同的规定,包括优先权、权利和限制。”转引自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23 See Richard A. Booth, Stockholders, Stakeholders, and Bagholders ( or How Investor Diversification Affects Fiduciary Duty), The Business Lawyer, Vol. 53, No. 2, 1998, p. 478.
24 冯果:《股东异质化视角下的双层股权结构》,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
25 参见汪青松、赵万一:《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变革——以股东“同质化”假定到“异质化”现实的演进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26 参见刘俊海:《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27 参见〔美〕莱纳·克拉克曼、亨利·汉斯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2版),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1页。
28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29 See Yair Listokin, What Do Corporate Default Rules and Menus Do?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 6, No. 2, 2009, pp. 279-280.
30 朱慈蕴、沈朝晖:《类别股与中国公司法的演进》,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9期。